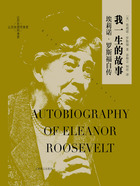
第四章
婚姻之初
在我们婚礼举行前的两周里,每个人都忙疯了。我的几位伴娘来帮我写信,向赠送结婚礼物的人表示感谢,当然签的是我的名字。然而有一天,我们惊恐地发现,伊莎贝拉·塞尔姆斯在写完“富兰克林和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礼物”之类的话后,居然签上了她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我的!
伴娘们的服装是奶油色塔夫绸的连衣裙,头上带有三根装饰羽毛,身后披着薄纱。富兰克林有众多男傧相,拉斯罗普·布朗是主伴郎。我自己的礼服则是长袖的,厚重的硬质缎面,领口饰有绢丝薄纱。豪尔外祖母的连衣裙上镶着一层布鲁塞尔玫瑰蕾丝,我的头纱也是同款蕾丝材质,从头上一直飘落到长长的裙裾之上。
伴娘们佩带的三根羽毛令人联想起罗斯福家族的纹章,而富兰克林为伴郎们设计的领带饰针上,也有三根用钻石制作的小羽毛。他还为我设计了一款金表,用钻石镶嵌着我名字的首字母,用来佩戴的别针上也有三根羽毛,这块表我至今还戴着,虽然款式如今已经过时了。
婆婆送给我一根像“狗项圈”那样的短款珍珠项链,带着它的感觉有些难以形容。我手里还捧着一大束山谷里采摘的百合花。
婚礼的日期对于我们豪尔家族的人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那一天是我母亲的生日。3月17日到来了。泰迪伯父从华盛顿抵达纽约,他检阅游行队伍之后就来到苏茜表姐的宅邸,富兰克林和我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
由于游行队伍堵塞了街道,许多参加婚礼的宾客被堵在路上。第五大道不能走,警察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泰迪伯父,也很难有人从麦迪逊大街通过。有几位客人直到仪式结束之后才抵达,气恼不已!
婚礼仪式由格罗顿公学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主持。苏茜表姐的客厅和她母亲的房子是相通的,因此我们有两间宽敞的大厅。我们实际上是在拉德洛夫人的房子里举行了婚礼,和去年普茜结婚时一样,房子里的壁炉前也放置着一个圣坛。
仪式结束后,我们转过身接受来自家族成员和朋友们的祝福。与此同时,泰迪伯父去了书房,那里有茶歇供应。我们的至亲们真心诚意地祝我们幸福,不过绝大多数宾客都对能够亲眼见到总统本人,亲耳听到总统讲话更感兴趣——有一小会儿,我们这对年轻的新人竟然被丢在一旁无人理会!总统所在的那间屋子里挤满了人,随着他的谈笑风生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我记得,当时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而且富兰克林似乎也不介意。我们只是跟随人群,和其他人一起听总统讲话。后来,我们召集了伴郎伴娘们一起切婚礼蛋糕,我觉得泰迪伯父应该也参加了这个仪式。之后我们便上楼更衣。到了下午“大人物”就回去了。
我们在传统的大米浴(1)中离开。我的一位老朋友鲍勃·弗格森,由于发烧卧床不起,没能参加婚礼。他曾经是泰迪伯父“莽骑兵”的成员,经历了美西战争后,就不时地发作,因此我们在乘火车回海德公园之前,先去看望了他。我们在海德公园度过了第一个蜜月。其实并没有两个蜜月的习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丈夫必须完成他在法学院的学业。
婚礼后的那个春天,富兰克林继续习修他的法律,我们则在纽约西福蒂斯一家酒店的一间小套房里,安顿好了我们的第一个家。
十分幸运的是,我的第一份家务非常简单。我给弟弟豪尔也准备了一个小房间,这样他就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复活节假期,而他的到来似乎令整个公寓都变得满满当当。在最初的几周里,我作为家庭主妇的职责实际上主要是修修补补,这个我还是能做的。但是我对于如何安排一日三餐却知之甚少,出国留学前曾经在蒂沃里学到的一点儿东西也全都忘光了。
当我婆婆去海德公园度夏的时候,我们搬进了她的房子,因此,我在作为家庭主妇方面的无知得以继续隐藏。
法学院一放暑假,我们就出国了——我是怀着怎样忐忑的心情登上了船啊!当你晕船晕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新婚燕尔的丈夫在一旁关切地注视着你,偏偏他又是个将航海视为乐趣的人,想想都觉得可怕!还好,航行途中风平浪静,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玩了很多次皮克牌游戏,而我总是输。当时的我还不够明智,不知道如果想要和富兰克林打牌的话,必须做好很少赢的准备。我说他是牌运好,他说这完全是靠技巧!
蜜月里,我们做了我一直以来都渴望做的事。我们首先去了伦敦,然而却惊讶地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被贴上了泰迪伯父的标签,布朗酒店为我们安排了皇家套房,客厅太大了,我连东西放哪儿了都找不着。我们只好解释说,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这样的奢侈消费,但也无济于事。在伦敦的前几天我们就住在这间皇家套房里。
我的丈夫热爱这座城市,而我也比以前更加喜欢它了,因为在他四处寻找书籍和画作的过程中,我们探寻到这座城市许多不为人知却新奇有趣的角落,顺带还买了不少衣服。不过,最令我感到兴奋的还是横渡英吉利海峡。
在巴黎,我们在充满异国情调的餐厅用餐,尝试每家餐馆的特色菜品,不管口味如何。我们在塞纳河畔漫步,逛遍了所有的旧货摊位。我买了些衣服和画册,而富兰克林每到一处都在买书,买书。
他精通法语,所以在巴黎他负责讨价还价,不过等到了意大利就换成了我,我的意大利语说得比他好。但是,仅仅过了几天之后,他再准备讨价还价的时候,就不再带着我了,因为他说我不在旁边他能做得更好,这个男人无论说什么我都会接受并且深信不疑。他凭借自己那点儿可怜的意大利语,大部分来自他在学校里学习的拉丁语,居然也能怡然自得。
我们去了米兰,然后在7月份的时候去了威尼斯,并在那里度过了美国国庆日。为我们划船的船夫很讨人喜欢,看上去像是个绿林好汉,我们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运河上徜徉。船夫和我的沟通很顺畅,有时候,我们的行程较长时,会有一个朋友来帮他,这时候威尼斯方言就会满天飞,他不得不给他的朋友充当翻译。
我们在那些教堂里流连忘返,直到我丈夫不想再看为止。我们沐浴在阳光里,坐在广场周围的小桌旁,回忆着威尼斯的历史,他始终兴致勃勃。
我们乘坐贡多拉去了穆拉诺,参观了玻璃吹制的过程,并订购了一套印有罗斯福家族羽毛标志的玻璃器皿,还有几个威尼斯彩色玻璃制成的海豚装饰品,这些东西我现在仍然保留着。
我们从威尼斯向北穿越多洛米蒂山,乘坐的是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笨重马车。科尔蒂纳一带的风景十分优美,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天。我丈夫和一位迷人的凯蒂·甘迪小姐一起爬的山。她比他年长几岁,并且他和她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她能爬山,而我不能,虽然我没说过一个字,但是嫉妒的心情无以言表。当我们重新出发,从山中离开时,我内心里暗自欢呼雀跃。不过我似乎应该补充一句,后来甘迪小姐成了我的挚友。
我们还去了奥格斯堡和乌尔姆,两座古老的德国城市,在那儿我们设法探访了更多蕴含历史价值的画作。然后我们驱车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圣莫里兹,蒂茜阿姨和她的家人就住在这里。
事实上,开车就意味着我们没法带那么多行李,我只带了一件简单的晚礼服,还是以前穿过的。当我们抵达皇宫酒店时,发现为我们预留了一间套房,价格却令人咂舌。因为只住几天,荷包尚能承受,所以我们决定住下来。但是我们忘了在这样的酒店中要准备多少套衣服,很快就发现,我们的衣服只适合在一个地方用餐,一个观看湖景的阳台,而这里的食物似乎比其他地方要贵许多。当我们再度启程,驶离瑞士,取道斯特拉斯堡和南锡返回时,简直如释重负。
一路上,富兰克林拍了许多照片,有一些是在山顶公路上拍下的,我们四周别无他物,只有白雪皑皑的群峰。我们一回到家,他立刻就去查找这些照片拍摄的准确地点。他具有照相机式的非凡记忆力,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回到巴黎,我收拾整理衣物,因为富兰克林的一些表亲也在那里,还有他的朵拉阿姨(福布斯夫人),我们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她带我们去了许多地方,她的寓所是我们最温暖的家,也是整个家族的人在巴黎的活动中心。
在英国,我们拜访了福尔贾姆夫妇,于我而言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他们有一处美丽的庄园,位于英格兰一个叫做“杜克雷斯”的地方,许多名门望族都在那里拥有大片庄园。
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蔚为壮观的橡树就在这附近,我们参观了一座城堡,城堡里有一条小铁轨,从厨房要穿过无数个走廊才通到管家的储藏室。有一间专门放置盘子的房间,更像是银匠的仓库,而不是私人宅邸的储藏室。藏书室才真的令人着迷。穿过一段走廊,然后踏上几节楼梯,便进入一个长长的房间。房间尽头的壁炉里,几根木头燃烧着。房间的两边堆满了书,中间摆放着桌子、椅子和地图,所有的一切都让阅读或学习变得轻松愉快。
在这个庞大的家庭中,却只有一间浴室。我们住在有壁炉的舒适房间里,早晨锡制的浴盆放在炉火前,旁边是盛满热水的罐子。食物非常丰盛,但都是典型的英国菜。晚餐很正式,却没有宾主介绍,这令我感到很是意外。我们是这栋房子里的客人,他们认为这就足够了。
晚饭后要打我一点儿都不擅长的桥牌,令我备受煎熬,而且还要赌钱,又令我的恐惧增加了几分。我信奉的原则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虽然被丈夫带着,但并不能减轻我良心上的折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陷阱里的困兽,既出不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在我们离开美国之后不久,伊莎贝拉·塞尔姆斯的妈妈发来电报,伊莎贝拉准备嫁给鲍勃·弗格森。他们在苏格兰度蜜月,看望他的家人。他们邀请我们去他母亲家,以便我们能够见上一面。他们的老宅子在苏格兰北部,一个离诺瓦尔不远的小型温泉疗养胜地。在那里,人们把家族的首领称为“诺瓦尔”,现任的诺瓦尔爵士多年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其他头衔,因为他认为“诺瓦尔”比王室加封给他的任何名号都要高贵。
老弗格森夫人所住的寡居别屋,对我来说是个惊喜,那里风景优美,山坡上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我和弗格森一家非常熟悉,他们和我们家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友谊。
富兰克林总是“和赫克托耳在荒野上游荡”,一天晚上,在参观了许多佃农小屋,忙活了一整天之后,沉睡中的我被邻床传来的犀利叫声惊醒。弗格森夫人睡眠很浅,我不想影响到她,连忙“嘘”了一声。我发现我的丈夫总是做噩梦。在轮船上的时候,他会梦游,从船舱走出去,所幸他在睡眠状态下很是温顺,会在我的劝说下乖乖回到床上。
这一次,他直直地指着天花板,怒气冲冲地问我:“你没看到房梁在旋转吗?”我向他保证没有这回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服他没有下床叫醒其他人。
第二天早晨,当配有薄片面包和黄油的早茶送进来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的梦。他说是的,而且记得当时对我很恼火,因为我坚持留在横梁可能会掉下来的地方。
在那里的时候,有人要我召集一场义卖活动。这对于任何年轻的英国女孩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十分确定,在公众场合我是一个字儿也喊不出来的。最后,富兰克林被撺掇着给佃农们做了一场演讲,结果被我们嘲笑了许多年,因为他告诉那些苏格兰农夫们,蔬菜应该在牛奶里煮——这可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奢侈!
从那儿我们又去了弗格森夫人的哥哥家里,罗纳德·弗格森爵士,他是家族的掌门人,和妻子赫克伦住在他们的另一所房子里,位于福斯湾的雷斯,就在爱丁堡对面。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遍布着苍翠茂盛的森林和风姿秀美的杜鹃花。我丈夫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科学的林业管理使这些森林变得富有经济价值,年年都能带来收入。
房子里四处悬挂着的油画令我深深着迷,就连通向我们房间的那一小段后楼梯的墙上也有。最令我激动的是,我们去吃晚饭的时候,在墙上发现了雷伯恩画的诸多弗格森家族祖先肖像。我看到的第一幅画《穿开襟衬衫的男孩》,是我自孩提时代就熟知的,只不过那时看到的是复制品,从来不曾想过能在朋友家里看到原作。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晚宴上看到身着短裙的苏格兰男子。荒野上的赫克托耳就穿着这样的短裙,但是直到这次之前,我还没有机会一睹它们的真容。
有一天下午喝茶的时候,我和海伦夫人单独在一起,她突然问了一个令我崩溃的问题:“请告诉我,亲爱的,你如何解释你们国家和州政府之间的差别?对于我们来说,这很令人费解。”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不同需要解释。我知道我们有州政府,是因为泰迪伯父曾经做过纽约州的州长。幸运的是,罗纳德爵士和我的丈夫在那一刻出现了,我可以让富兰克林回答她的问题。他圆满完成了任务,我暗自发誓,一旦安全返回美国,就要去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政府。
我们必须回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开学典礼,所以我们的假期,或者说蜜月,已经结束了。我婆婆在离她家不到三个街区的地方为我们租了一套房子,在东36街125号。她已经将房间布置好,并且也为我们找好了仆人。在回来的最初几天里,我们会和她住在一起,直到我们的房子装修完成。
我开始成为一个完全依赖他人的人——不需要买票,不需要做计划,一切都有人替我做好决定。与我以前的生活相比,这无疑是令人愉悦的,我对此欣然接受。
被迫与许多人接触,我那种害羞的感觉正在逐渐消失。虽然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折磨,但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
莫德或是普茜曾经告诉我,如果我在谈话中卡住了,应该从字母表开始找话题。“A-Apple,你喜欢苹果吗,史密斯先生?B-Bears,你怕熊吗,琼斯先生?C-Cats,你对猫有同样的感觉吗?杰里费什太太,即使你看不到它们,它们也会让你毛骨悚然吗?”诸如此类,为了打发时间而没话找话真是令人绝望。作为年轻女性,我认为我更适合传统的、安静的年轻人社交模式。
(1) 大米浴(a shower of rice),是西方婚礼的一种习俗。在婚礼中客人们要向新郎和新娘身上抛洒大米,旨在祝福新婚夫妇子孙满堂、人丁兴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