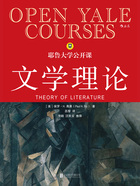
前言
本书里的章节在出版过程中经历了极为不寻常的变化,尽管收录本书的丛书系列可能让它看起来不是这样。没错,我在2009年春季学期开设的26讲的耶鲁大学公开课“文学300”录了像,当你开车上班或者去跑步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录音听。当人们认为转写成书稿也许也会有吸引力之后,这些讲座最后变成了文字形式的这本书。这些讲座都是我根据一页左右的潦草笔记即兴讲的。录音带被送到圣地亚哥,在那里,一台机器写下了它认为自己听到的东西。这份稿子又被送到纽黑文的一个人的手里,她又做了她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我接手的起点。我本应该完成我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做的这项工作,但那时缺乏动力,我只是花时间浏览了文稿,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尽管我意识到这份记录稿经过多次转手,已经变得像一个笑话或者一堆闲言碎语。
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让它保持那个样子,因为这些本来就是转写稿,而不是重写,尽管它们的准确度只达到了电视上为有听力障碍的人提供的即时字幕的水平,但是不会有人说这份稿子经过了有意而为的改动。但是,它们现在变成了一本书:诚然,既有数字版本也有印刷版本,但仍是一本书。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收到并接管这份转录稿后,做了一些润色修改。然后我收到了这些讲座的压缩文件包,进一步的编辑工作已经启动,我也开始工作。这时,我不断想起我为学生布置的(在本书第13章中加以讨论)一篇非常有名、以难读著称的论文的开头几段,那就是雅克·拉康的《无意识中文字的能动性》。他说,他这篇文章是一个研讨会发言的文字稿(écrit,收录在一卷《著作选集》【Écrit】中)。他觉得,如果他想完全传达他对语言在无意识中扮演的角色想要表达的看法,保留那个场合的口语形态很重要。同时(尽管拉康没有这么说),对任何曾经当过听众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即兴讲话中传达的信息或许对那个场合来说是足够的,但听众对其记录下来的方式的接收,与一个读者在更为休闲的状态下关注文字版本时接收信息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这本书是为读者准备的,所以我修改了讲座中在我看来需要进一步详细阐释的地方,同时希望全程保留一种现场听讲座的感觉。我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散文化”的即兴演讲者,所以当你遇到一个长句子时,请不要认为它在讲课时是短一些的。
没有我的助手斯蒂芬·埃斯波西托不可或缺的全面帮助,我不可能集中精力处理我已经描述过的那些意外的挑战。斯蒂芬是给这些讲座进行录像时的助教之一,也是一位冉冉升起的重要的比较文学学者和理论家。我欣然地接受他对这些章节做最后一遍的通读和修改,当我把稿子递给在波士顿的他时,每一份稿子的标题都是“修改稿,X号”。他撰写了书目文章《阐释的种类》,以及每一个话题的进阶阅读书目,这篇文章在全书的最后。他还提供了我们认为必要的参考文献(尽可能少),以及附录中的文章段落。我在一些课上打印并散发了这些段落或者上传到了网上,以便学生讨论。
尽管引用我布置的复印材料是一个挑战,估计至少会引起我们大体上希望避免的烦恼,但是引用我们的主要教科书还是容易的。我强烈建议我们的读者考虑购买这本优秀的书。这本书以其明智、丰富的选文(选文覆盖了整个批评史)和通情达理的导读在这个领域独树一帜。这就是大卫·里克特(David Richter)编纂的《批评传统:经典文本和当代趋势》(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3rd ed.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7)。本书所有方括号里的引文页码都是该书第三版的页码。
本书的头两章是导论,给出了许多大家通常可能期望在前言中看到的申辩、免责声明和自夸,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多说我接下来对这个广阔学科的巡视包括哪些内容。但我意识到,我的课程大纲中没有包括一些近来很有影响的人物和思想,尽管你可以零星地找到对这些潮流的间接提及和预测。比如“伦理转向”,如我指出的,也包括晚期的德里达,但是我没有讨论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或者诸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还有一个潮流发端于英国,以西蒙·贾维斯(Simon Jarvis)、凯斯顿·萨瑟兰(Keston Sutherland)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本表面做出了才华横溢的解读。他们采用的微读法(micro-reading)是由蒲龄恩(J. H. Prynne)开创的,刚刚通过他们大有前途的学生们传到美国海岸。
文学社会学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但是我对约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的讨论(并在那个语境下提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并没有结合对其他重要著作的讨论,比如社会语言学家迈克尔·西尔费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的著作。皮尔士的符号学影响了西尔费斯坦思想的形成;比如纳普和迈克尔斯的新实用主义观点(本书有所讨论),如今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知识和品位在社会和文化中的流通,但必须说明的是,这更多的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为模型,而非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后者与作为索绪尔传统的竞争者兴起的皮尔士传统中的社会标志符号(socially indexical sign)相似,我们的讲座对这场竞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皮尔士传统的概述还没有著作出版,我希望很快会出现。读者可以在本书第25章的开头找到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讲解。
最近,福柯(本书有所讨论)和葛兰西(只顺便提了一下)以外的知识流通理论将学者们引入了相互关联的一些领域:系统理论(尤其是尼克拉斯·卢曼的)、媒介史、再媒介化、媒介理论(这个领域的经典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著作),以及这些领域中更专门的书籍史(如彼得·斯塔利布拉斯和大卫·卡斯坦的著作)。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需要另一门课、另一本书来介绍。
确认我在学术上受到了哪些人的恩惠—我是说我受到的个人恩惠,因为这里写下的这些名字大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被列入了书目文章之中—是极其巨大的挑战。我在这里只能列出其中一部分人名,这些年来他们的教导和对话塑造了我对这门学科的理解,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点:Jeffrey Alexander, Johannes Anderegg, Marshall Brown, Margaret Ferguson, Stanley Fish, Hans Frei, Harris Friedberg, Paul Grimstad, John Guillory, Benjamin Harshav, Geoffrey Hartman, John Hollander, Margaret Homans, Helmut Illbruck, Carol Jacobs, Barbara Johnson, Jeremy Kessler, Eric Lindstrom, Alfred MacAdam, David Marshall, Irving Massey, Rainer Nägele, Ana Nersessian, Edward Nersessian, Cyril O’Regan, Brigitte Peucker, Anthony Reed, Joseph Roach, Charles Sabel, Naomi Schor, David Simpson, Peter Stallybrass, Garrett Stewart, Henry Sussman, Steve Tedeschi, Michael Warner和Henry Weinfield。在这些课题上教育别人(并且允许别人接受教育)是一件如此重要但又精细的工作。与以往类似的场合相比,我现在的痛苦尤甚,尽管我已经列了一个似乎相当长的致谢名单,我无疑还是遗漏了许多值得在这里提到的人名。我只能希望他们能够因为未被提及而免于受责松一口气。从我20世纪80年代开设这门课程开始(当保罗·德·曼的学生把他们的优势和热诚带入我们的进程时),有很多助教帮助过我,我在本书题词中对它们表达了谢意。对于一直以来给予我建议和鼓励的人,除了斯蒂芬·埃斯波西托,我还要感谢耶鲁大学公开课的创始人和不知疲倦的支持者E. E. Kleiner以及耶鲁大学出版社的Laura Davulis, Christina Tucker, Sonia Shannon, Ann-Marie Imbornoni和Aldo Cupo。我也要感谢韦斯特切斯特图书集团的Wendy Muto和Brian Desmond,以及我的文字编辑Julie Palmer-Hoff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