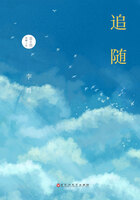
第3章 老舅(2)
老舅叫陈宏,是个“能人”。不仅是家里公认的,也是村里公认的。强健的身躯,坚韧的意志,朴实的个性,这些陕北农民最值得自豪的优秀品质,在老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学时代的老舅,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老舅所在的学校离家有十几里山路,虽然有自行车,但陕北高原上山路崎岖,沟壑纵横,一路上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半数时候只能扛着车子前行,可谓翻山越岭。即便这样,初中三年,每天来回二十几里,早晨很早就披星戴月地出发了,晚上放学,再披星戴月地回家,老舅却从来没有抱怨过。
寒冷的冬夜里,一个高瘦的黑影扛着自行车在漆黑的陕北高原的沟壑里忽隐忽现,没有树,没有河流,一切都是灰黑色,没有生机,没有色彩,只有嘴里呼出的热气在月光下分外明亮,仿佛成了这片晦暗大地上唯一的一抹亮色。
老舅初中毕业后,就坚决辍学了。个中原因有很多,当然,有为家庭减轻负担的考虑,毕竟,老舅的家庭较为贫寒,五女一男,女眷众多,男丁稀少,劳动力严重短缺,生产队的工分欠了一年又一年,以至于老舅打小就有一种紧迫感与危机感。另一方面,老舅的辍学也是主动的、有意识的。
与其说老舅没有太大的志向,倒不如说老舅务实且自信。老舅坚信,凭借自己的勤劳就足以立足社会。于是,在姥姥和姥爷坚决的反对声中,老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业后就果断辍学了。辍学以后,老舅到砖厂里打工,工作没几年,便攒够了结婚的彩礼。20世纪80年代的婚姻,有了足够的彩礼就可以娶一个很不错的媳妇了。有了几年的积攒,加上姥姥和姥爷的贴补,老舅在村里盖起了第一栋红砖房,当时村里大部分人都还住在土窑洞里呢。老舅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村里的后生们纷纷效仿老舅,盖起了红砖房。
老舅娶了一个同样高瘦且强壮的媳妇,两人颇有夫妻相。在很多人看来,老舅和舅妈是天生一对,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两人同岁,性格差异却很大,老舅仁厚,舅妈脾气大,有些斤斤计较。人们说老舅是“妻管严”,其实舅妈在很多方面都是尊重丈夫的,可以说是给足了老舅面子。两口子很少吵架,只是近来因为儿子的事,生出颇多意见。尤其是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的事,让舅妈也忧心忡忡。就夫妻关系而言,老舅和舅妈之间几乎没出过大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老舅的忍让。可到了四十五岁这一年,老舅似乎在很多方面都不愿忍让了。
老舅没什么宏大的志向,但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照顾好家人,始终是老舅最为看重的责任。
老舅有一个原则,就是努力让自己处在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处的位置,与潮流趋势共进退,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感。时代在变化,农民进城已经成了大趋势,留在村里就意味着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意味着不进,不进则退,就免不了沦落到社会的边角旮旯,家人也跟着遭罪。
这样的危机意识早就在老舅的脑袋里萌芽了。
就在村子里的年轻人还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着祖先的劳作时,老舅便扔下锄头,大胆地行动了。
老舅抛下了老家才住了五六年的崭新的红砖房,进城租房住了。老舅也不在砖厂干重体力活了,做起了配送工作,专门负责4S专卖店的汽车零部件配送。彼时的配送工作不同于现在红火的互联网外送模式,没有平台抽成,老舅只为汽车厂商服务,收益也更为可观。面对姥姥、姥爷的不理解和不支持,老舅的内心没有动摇。
老舅和舅妈目标一致,夫唱妇随,两人省吃俭用,处处精打细算,在他们四十周岁那年,买下了老城区的一栋二层独院。
没多久,紧靠着老城区,打造一座“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号角突然吹响了,各种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工建设,一座座高楼大厦崛地而起,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进小城。过了三年,房价开始上涨,他们的房子升值了一倍,又过了短短两年,房子估价飙升到三倍以上。老舅从小习惯了为生计担忧,面对突如其来的美事,心里总免不了有些疑虑。
想不通,便不再多想。老舅把院里的小房和正房一楼租出去,让舅妈做起了包租婆,自己则照旧忙活配送工作。
房租的收入让老舅的收入翻了近一倍。老舅感叹道,这哪是买了一套房子啊,简直是买了一个无形的劳动力嘛!
有人告诉老舅,这是吃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所致。老舅只知道吃苦,未曾想过要吃时代的“红利”,更不明白时代的“红利”为何物。对老舅来说,踏实肯干、从点滴做起、不怨天尤人,这是生活的基本要求,无关其他。所以,老舅对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取得的成绩,始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有时候回想起来,似乎一切出乎意料,但仔细想想,又步步都在情理之中。
积极进取,然后随遇而安,这是老舅的生存哲学。
即便是买了房子,老舅依旧勤勤恳恳。需要的时候,加班加点工作也毫无怨言。有时候深夜下班,老舅舍不得在外面买吃的,便提前叫舅妈热好饭菜,回来吃。有时到了数九的寒冬,晚上八九点钟下班回到家,刚端起碗筷,主管的配送电话打来,老舅顾不得吃饭,立马扔下碗筷,一边吞咽着烫嘴的饭菜,一边起身,绑上厚厚的护腿和袖套,戴上头盔,骑上摩托车,平稳地穿过朦胧的夜色。在配件市场上,没人比老舅干得更久,没有人比老舅更可靠、更值得信赖。不管什么时候,老舅都以工作为主,甚至参加亲戚的婚礼,老舅也不喝酒,配送电话一到,撂下碗筷,随时出发。忙碌工作之余,老舅还默不作声地拿到了汽车驾驶证。
深知勤劳的价值,这是老舅立足的根本,也是他心里踏实的稳定器。可最近,老舅的心理越来越不踏实了。
起初只是儿子将工作不顺的怨气抛给自己,现在就连舅妈也将一切恼事归罪于自己。老舅仿佛成了一个出气筒,一天疲惫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家还要小心观察老婆、儿子的脸色,这和老舅一直以来的追求背道而驰。
心情不好的时候,老舅只能无奈地抽烟。面对与儿子的矛盾,老舅无可奈何,却并不过分担忧。老舅心里清楚,儿子长大了,迟早要有自己的生活。父子间的矛盾,随着儿子逐步建立自己的生活,自然会得到解决。老舅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去干涉儿子,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默默照顾儿子。那个至今让老舅的右手隐隐作痛的巴掌,只是过渡期的一段小插曲,不会吞噬父子之间的感情。
真正让老舅苦恼的是夫妻关系的恶化,且没有一丝改善的迹象。
这里存在一个硬件问题。作为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的利器,老舅和舅妈的性生活出了问题。
在老舅四十五岁的这一年,老舅和舅妈的性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在老舅的记忆中,近半年时间,夫妻之间只有过三次性生活,只有第一次还算和谐。
那天是正月初四,恰逢春节长假,儿子去了奶奶家,家里来了亲戚,老舅很有兴致,便喝了些酒。送走了亲戚后,两人一起收拾了家庭聚会留下的一片狼藉。舅妈看上去似乎也是难得的好心情。儿子不在家,只剩夫妻二人,两人一下子感觉像是刑满释放的囚徒,平日里压抑的气氛消失了,不必再有什么顾虑,整个房子都是他们的。老舅借着酒劲,显出了全然不同的另一面,一家之主的威严和姿态一扫而光,变得亲切火热起来。
中年夫妻的性生活是直率而熟练的,老舅和舅妈也不例外。有十多年没有在卧室以外的地方做爱的老舅和舅妈,突然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的时候。在客厅的沙发上,半个多小时之后,伴随着舅妈的抓挠与尖叫声,老舅用最传统的姿势,在汗流浃背、脖颈通红的状态中不舍地释放了自己,也释放了舅妈被压抑许久的体验。这次难忘的性生活后,两人赤身躺在沙发上,相拥着笑了很久。这放松的笑好像也蕴含着某种预兆。笑声结束后,老舅的心里生出了一丝不安的念头。
此后的两次性生活都间隔了好几个月,且都是草草收场。第二次是后半夜,做着做着,舅妈一直盘算着昨天给住户拟定的取暖费是不是低了点,想着想着,便有些烦躁地说,没感觉,太累了。老舅只好尴尬收场。第三次,也是最近的一次,在两个月前,也是老舅扇了儿子一巴掌的半个月前,这次舅妈很有些兴致,但老舅刚刚进去就泄了,舅妈只是抱怨老舅没准备好就瞎撩拨她,老舅却隐隐地有些害怕。
那会儿,天刚黑,时间尚早,且还是老舅少有的假期,老舅一整天待在家里,可谓精力充沛。老舅却早泄了。直到入睡,也没能再次勃起,老舅越发觉得不正常。
往常可不这样的啊!
老舅是一个健壮的中年男人,虽然看着偏瘦,但都是结实而有活力的腱子肉。长期的劳动,让老舅养成了一副好的胃口,能吃能喝,不挑食,也练就了一副结实的身体。刚结婚那几年,一次,砖厂晚上八点多才出完砖,第二天是个难得的休假,老舅当晚十点钟就赶回了家。小两口已经两个星期没见面了,刚到家,舅妈把饭放回锅里,顾不上让老舅吃口热乎的饭就关上卧室门,小两口很快就裹在温暖的被窝里。夜里十点到家,半夜一点多,舅妈才从厨房拿出已经冷了的饭菜,看着老舅狼吞虎咽地吃着,小两口有说有笑地聊到半夜两点。这之前,三个小时里,两人先做了两次,老舅不想做了,耐不过舅妈的要求,又做了一次。三个小时三次,想想也觉得没什么。第二天早上六点钟,老舅就在晨勃中清醒了,小两口在被窝里一直腻到上午九点才起床,这期间,又做了两次。从晚上的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老舅扳了扳手指头,十一个小时,做了五次,还是在一整天的劳动之后,这确实有点分量了。可老舅依然精力旺盛,忙进忙出,没个停。
回忆越多,老舅便越发地心慌起来。虽然性生活里泄一次很正常,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泄过,但很快就能重振雄风。可这次泄了,却再也没法唤醒更多的热情了。
在这个漫长的、无法再次勃起的夜晚,老舅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做了前半生唯一的一个春梦。
这个春梦的情节大概是老舅的一个真实记忆。
那是老舅的中学时代。那时候的农村初中,生物课中的“两性生理课程”往往作为自学部分,被老师直接跳过,而“两性生理课程”又往往是整个生物课本的开篇第一章,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在那个纯真、奋发的年代,勤奋的学生们把课本的边缘空白都用来记笔记,唯独打开生物课本,会发现毫无铅尘、干净如新。老舅的生物课本也是如此。老舅和大多数学生们一样,对于“两性生理课程”充满好奇,可常规的课程挤满了老舅的学习时间,下午放学后,大量的时间又耗在了赶回家的路上。回家吃过饭,已将近后半夜,想要看会儿书,只好挑灯夜读。那时候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煤油金贵,半夜点煤油看书时常被姥姥骂。
“白天不好好学习,半夜了装什么样子!”姥姥这样一骂,老实听话的老舅就赶紧熄灭油灯。余下的就只有周末了,可家里的农活又占据了老舅全部的周末时光。在家几乎没时间拿起书本,老舅只好利用在学校的有限时间跟着老师们的课程计划亦步亦趋地学习。这样问题就来了。到了期末,老舅其他的课程都很熟悉、很优秀了,但一直想看的生理课程却抽不出时间看。
没有理论知识,自然无法指导实践。老舅有个女同桌,短发,平日里很活泼,近来却胖了许多,且胖得异常。老舅始终琢磨不透,平日里很熟悉的女生,近来胸前为何有些肿胀?老舅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变化,只能用“肿了”一词。在老舅看来,女同桌似乎得了病,老舅将此病命名为“胸前浮肿病”。
终于有一次,老舅耐不住满脑的疑问,低声地问女同桌,是不是病了。女同桌答道,她没病。
“那你怎么有肿块了?”老舅不敢指得太精确,便说,“你看你肚子上面。”
女同桌听后,笑翻了。
老舅意识到自己的描述不准确,干脆直接说:“不是肚子,是你的胸前,起了肿块了!”
女同桌终于听明白了,抱着肚子,笑得更厉害了。
老舅有点尴尬,短促地说了声:“算了!当我没问。”
女同桌突然不笑了,疑惑地看着老舅,问道:“你没看生物课本吗?”
老舅说,看了。
女同桌低声说:“生物课本第一章,生理课那部分!”
“没看。”老舅说,“我也很想看,只是没有时间。”
“你看了那章就知道了。”女同桌说。
“你怎么有时间看呢?”老舅好奇地问。
“我不像你,周末没你那么忙。”女同桌说,“我有时间,还可以做些功课。”
“女娃就是好。”老舅说,“没那么多农活,还可以看书。”
“都有肿块了,还好?”女同桌笑着反问老舅。
老舅一脸窘态。老舅确实没仔细研究过此病,不知其利害,更不知如何回答。
见老舅一脸认真的模样,女同桌忍不住又笑了。
“你还是要抽时间看看的。”女同桌突然郑重地对老舅说,“生物期末考试,要考这部分呢。”
“可我真的没有时间看啊!”老舅着急地说。
见老舅被自己逗得够呛,女同桌瞬间心软了,心里有了些愧疚。
女同桌自我反省了一会儿,随后凑过来,贴着老舅的耳朵,红着脸说:“我们不是一起回家嘛,我路上给你讲吧。”说完,匆匆瞄了老舅一眼,脸更红了。听了这话,老舅也有些害羞。
两人刻意躲闪着,一日无话。
老舅偶尔抬起头,从乌黑的齐刘海看过去,女同桌若隐若现的脸颊和修长的脖颈,一片通红,却那么纤细,那么自然,那么美。白净得不像陕北女娃的脸,微微偏过去的下巴和脸颊,棱角分明,在阳光下,通透,闪着光,好像雨后滴着水滴的青葡萄。
老舅有些疑惑,自己之前为何不曾发现这样的美?
在未来三十年的时光中,每当看到电视上出现的全国公认的大美女站在镁光灯下的倩影时,老舅就会想起这张侧脸,但所有那些大明星的脸都没有记忆里的这张侧脸迷人,这样直击他的灵魂。
总之,这是老舅生命中最难忘记的几个画面之一。
女同桌的建议,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学有所获,一举两得。反复权衡后,老舅便以“传纸条”的方式,欣然应许。老舅之所以能理所当然地接受女同桌的帮助,是因为他也没少帮女同桌的忙。
老舅和他的女同桌来自同一个乡,只是住在不同的村子里。两人就读的中学位于乡镇中心,两人放学后总是相伴着一起回家。老舅家的村子距离学校远,女同桌的家更近些,老舅回家的路正好途经女同桌所在的村子,因此,实际的情况就变成老舅每天护送女同桌回家。
女同桌也骑自行车,只是不太熟练,骑起来七拐八拐的。女同桌平日里大大咧咧,也不会爱护自行车,掉链子、爆胎成了家常便饭。女同桌的自行车出了问题,老舅也没法骑车了。老舅帮女同桌修了无数次自行车,也帮女同桌扛了无数次自行车。
因此,在这片历来荒凉又充满传奇的黄土地上,时常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在陕北高原黝黑的山路上,两个年轻的身影,披星戴月,翻山越岭,缓慢前行,讨论着人类几千年历史总结出的最原始的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些最本源的身体知识,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一样态度严谨,也像亚当与夏娃,在漆黑的夜晚,漫步在伊甸园中,彼此观察着、交流着,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思考着。女同桌在前面开路,老舅跟在后面,一人扛着两辆自行车,步伐沉重而坚实。女同桌不时回头看老舅,走到崎岖处,还伸手拉老舅一把。他们俩的身影在漆黑的陕北高原的沟壑里忽隐忽现,没有树,没有河流,一切都是灰黑色,没有生机,没有色彩,只有嘴里呼出的热气在月光下升腾,成了这片晦暗大地上唯一的亮色。
某一天的晚上,繁星布满天空,夜色格外迷人。两个人一边激烈地讨论着生理问题,一边吃力地爬上一座小山峁,老舅脚底下没踩稳,肩上的自行车晃动起来,瞬时失去重心,滑下了山坡。女同桌慌忙伸出手,舅舅一把握住。无奈舅舅身体重,顺势一拽,两个人一起跌下山坡,滑到山脚下,两辆自行车一辆压着一辆,两个人身体纠缠着,滚作一团。两人脸贴着脸,老舅的胸膛压在了女同桌的胸脯上。气氛出奇的安静,只听到山脚下的小河潺潺流动,在月光下,如水银泻地。
老舅摇了摇有些晕乎的头,看清女同桌的脸后,慌忙爬起来。女同桌也坐起身,轻轻拍打着身上的土。
猛然间有笑声传来。
“你笑什么?”老舅疑惑地看了看女同桌,问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女同桌一边笑,一边说,“男人的胡楂是硬的,书上说得对!”
老舅的脸涨成了紫色的芋头。女同桌说老舅是“男人”,老舅从来没被人用“男人”这个词形容过,所有的人都称呼老舅是个“男娃娃”“小后生”。老舅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算是个男人了,但是老舅知道女同桌是有点像女人了。女同桌是像她自己讲两性生理课程时说的那样,“发育”了。同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一直以为女同桌胸前的肿块是硬的,当他的胸膛压在女同桌讲给他的所谓“乳房”上时,终于从实践中检验出来了,那不是硬的,靠在上面软绵绵的,像是靠着棉花糖的感觉,女同桌讲得不假!
那天晚上,女同桌偷偷地亲了老舅。算不上吻,只是简单的嘴唇触碰。后来老舅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觉得那个吻是干干的,没一点水分,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老舅一辈子忘不了那个吻。
梦中女同桌的吻,吻醒了老舅。老舅的春梦就停留在这个吻上。
老舅略有不舍地睁开眼睛。这是连日来众多梦境中,唯一没有触发压力和恐惧的梦。老舅缓缓起身,点了一支烟,仔细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两支烟的工夫过去了,事实确凿无疑了。这不是梦,是现实,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记忆。
老舅想到了和女同桌的后续。彼时处在青春期的老舅,在外人面前是一个内向的、不爱说话的男娃,对男女关系也尚未开窍。第二天回到校园后,老舅发现女同桌看自己的眼神有了奇异的变化。女同桌变得不爱说话了,两人也不再打打闹闹了,对话也不再是之前那般连珠炮似的了。在学习问题面前,女同桌不再那么激烈地反驳老舅的观点,更有一种“你说怎样就怎样吧”的顺从态度。
女同桌主动示好,老舅却始终沉默应对。
老舅的沉默并不是克制的,而是自然的。老舅的心思都在家里的事情上,无暇投入青春期的浪漫时光。老舅更不会想到,三十年后自己还会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读初中的末尾,两个月后老舅便辍学了。此后,两人再也没见过面。老舅始终不能确定这算不算是自己的初恋。如果女同桌不算自己的初恋,那老婆是自己的初恋吗?老舅转头看了看轻声打鼾的舅妈,坚决地摇了摇头。老舅心想,总要有个初恋,那女同桌就算作是自己的初恋吧。
让老舅不解的是,自己为什么会在如此尴尬的夜晚做这样一个梦呢?
老舅又开始担心昨夜性生活的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