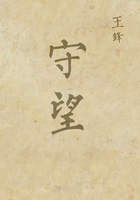
第1章 灰黄的灯光
外面的风呼啸而过,把院子里靠墙的简易铁皮房吹得哗哗作响,屋子里炉膛的火烧得正旺,那通红通红的火苗上下跳动着和屋子里热闹的气氛不谋而合。孩子们欢聚一堂,他们相互比画着手指脸上挂着笑意,时而举杯碰盏,时而谈天说地。至于他们说什么我已经听不大清楚,我只是自顾自地任由回忆的思绪把我无情地拖拽回去。
我坐在一张已经陪了我几十年的摇椅上,扶手上明显已经被包浆成了油亮的暗黄,它的摇动有一种随意而舒适的节奏感,这种缓慢而持续地摆动并不像令人眩晕的旋转,而能让人心情逐渐地平静下来,仿佛可以感受到时间流逝的缓慢。坐在摇椅上,随着节奏的变化,我的心情如同在一次轻松的时光旅行中,感受着岁月的温暖和安慰。
今年我已经68岁了,在这样的恍惚中我分不清我是唐四妮还是扈蕊,这两个名字贯穿了我的一生,在我的生命里不断地交叉纠缠,她们让我游走在人性的边缘,明白了善恶的区别和生命的脆弱。
我这一生是波折的一生,而这份波折中也造就了我的幸福,仔细回忆这应该都源于人性中那份时刻都提醒我的善,是这份信念默默地守护了我这么多年,渡我每一次化险为夷,这一切都要从我的出生说起。
1955年的春天的西北,有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叫雷桥,在雷桥二队,住着二十户人家,这里家家户户的房子连排挨着,大家的房子和院墙都用的是土坯,一家坐北向南的院子就是唐家,三间不大的土坯房在小院的中央处挨着。
外面黑夜如漆,最左边土坯房里搭着一个通铺大炕,炕上铺着一张席子,席子的边角已经有了年久破损的痕迹,一些地方用颜色不一的布头缝补着。炕角放着两张露着灰黑棉絮的棉被。
炕上放着这个房子里唯一的一样家具——一张小方桌,方桌上放着一盏油渍四溢的油灯,从油灯里发着幽幽暗暗灰黄的光。我的父亲唐一民还在响应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在田里忙着挣工分没有回来。
我的妈妈马茹娥,满脸通红伴随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滚落到了她穿的那件白色粗布褂子的衣领上,衣领看起来汗津津的,她已经怀胎足月,硕大的肚子疼到不行。
马茹娥不断的“哎哟,哎哟”呻吟着,两条麻花辫被炕上的席子扯出许多毛刺,满脸都是痛苦难耐的表情,一条黑灰色的裤子裤腰已经耷拉到了腹股沟以下,对襟衣服的下面两颗扣子也亮眼的敞开着。离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打着赤脚穿着半夹棉开裆裤的小姑娘,周身上下脏兮兮的,脸上也被鼻涕糊的乱七八糟,一把手放在嘴巴里不停的咂摸着,看起来她只有两岁多,这个时候她明显饿了,这个小姑娘就是唐三妮。
“大妮、二妮,妈妈要生了,快帮妈妈去叫隔壁的张姨,快去……”马茹娥在呻吟和疼痛的间隙对着两个女儿呼喊。两个女孩,老大是唐大妮年过六岁,丹凤眼,八字眉,瓜子脸,高鼻梁,扎着利落的两根马尾辫,马尾辫下面用的是两根红毛线,一身花棉袄和棉裤,膝盖已经磨得细薄如纸,能看见里面细白的棉花集结成坨,针脚的地方还露出了几根飘飞的棉絮,脚上趿着一双大拇指已经有破洞的枣红色单布鞋,四月的春季显然是有些冷的。
大妮的大模样像妈妈马茹娥,虽然不能说长得漂亮,但是身材纤细也算出落得大方。小一点的是唐二妮,刚满四岁,跟姐姐一样的发饰打扮,长了一双似乎能说话的双眼皮大眼睫毛弯弯,圆脸盘,小嘴巴。身着一套略显宽大的红色袄子夹棉裤子,很旧,屁股还有一些不大的破洞,这是唐大妮穿剩下她接替过来的,脚上的鞋大到连鞋跟都提不起,就那么如同拖鞋一样在她不断地移动中与地面摩擦发出闷响。
二妮个头矮小,看起来更灵动可爱。在马茹娥叫喊完以后,二妮麻溜地应了声“妈妈,好的,我跟姐姐这就去”。“妈……你忍忍啊!”大妮和二妮二人在奔跑中回应了马茹娥然后一前一后地掀开破旧的布门帘冲了出去。
隔壁的张家和唐家一直关系交好,两家常常相互帮衬,张家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他们也不再决定生了,因为第三个孩子终于生到了儿子,年龄跟唐家的三妮相差无几。
不一会,张姨就冲进了门,旁边一左一右是气喘吁吁的大妮二妮,“茹娥,你终于有盼头了,这次这肚子里的四胎怎么也是个儿子,你家后继有人啦!”“她张姨你来啦!借你吉言。我不行了,看样子是要生了,哎哟,哎哟……”马茹娥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应和着。
“我前几天就给平时常接生的郭婶子打好了招呼,你哪天肚子疼要生,只要去找她,不管几时她都会麻利来的,你候着再忍忍,我这就让土生的叔叔去叫,然后再去田里叫大妮她爸,你别怕昂,我在”张姨很热心地安慰。
待到接生的郭婶子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有大半个小时,马茹娥已经疼得死去活来,在炕上左右翻滚着。郭婶是远近闻名的接生产婆,个头不高,五十多岁,身材瘦小,近十年之内经由她手接生的孩子也已经数量非常多。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伴随着土改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社会也在倡议多生孩子提高国家人口数量。谁家要是生孩子,都要找郭婶。郭婶麻利地对着张姨说“她姨你给我烧两壶水”。“噯!好的,郭婶,她家大妮、二妮三妮都是你接生的,她家你比我熟。”隔壁张姨调侃着。
郭婶把炕上的三妮一把抱了下来,给了站在炕沿边看着妈妈显得焦躁不安的大妮,“大妮,抱着三妮,带着二妮先出去,我要给你妈接生弟弟”。大妮格外懂事地一把接过三妮回郭婶的话“嗯,奶!”在张姨的帮衬中,伴随着马茹娥不停的呻吟,和郭婶有节拍的呼喊促生中,郭婶用一把开水煮过,酒精消毒过的剪刀,“咔嚓”一下剪断了我和妈妈马茹娥的最后的连接,一声啼哭划破了深夜的天际。
这个哭出了响亮声音的孩子就是我,唐四妮,一个在妈妈肚子里被大家判定为男孩的女婴。给我擦洗了身上的血迹后,郭婶对着张姨失落地说“又是女娃娃。”旁边的张姨唉声叹气,躺在炕上半昏睡的妈妈马茹娥听到了“又是女娃娃”这句话,好似凉水泼身,俨然一副忘了刚生过孩子的样子,半起身,“郭婶,她张姨你们再看看。”“茹娥,没事,以后咱再生,”张姨不断地安慰着。郭婶拾掇东西也悻悻退去,张姨把我放在了妈妈身边,可妈妈连看都不想看我一眼,侧过身去,轻轻地开始啜泣。大妮抱着三妮,带着二妮进门后,扒着炕沿伸头看着,小声叫着“弟弟,弟弟。”马茹娥听到后,由啜泣改成了更难过的抽泣,她的整个后背都在颤抖着。对于她来说,家里又一次生男丁的希望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