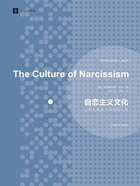
历史时间感的淡薄
随着20世纪将近尾声,人们日益坚信有很多事情也将随之结束。各种有关风暴的警报,不祥的预兆和关于灾祸的暗示搅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得安宁。这种“终结感”构成了20世纪文学的重要因素,并已广泛地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想象之中。纳粹党的大屠杀,核战争的威胁,自然资源的耗尽,证据确凿的有关生态危机的预测,不但印证了诗一般的预言,而且为这一噩梦、这一由先锋派艺术家首先表达出来的死的愿望注入了具体的历史内容。世界会告终于火还是告终于冰,是带着一声轰隆还是一声唏嘘,这一问题不再只使艺术家们感兴趣。正在迫近的灾难已成为人们日常关心的对象,而人们已变得如此习惯,以至于再也没人会费心思索该如何行事才有可能避免灾难。相反,人们忙于寻找生存、长寿、确保身体健康、心境安宁的良策。(4)
那些挖防空洞的人希望四周布满现代技术的最新产品以使自己幸免于难。乡村中的社群主义者们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竭力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从而不致因技术的摧毁而一同毁灭。一位访问过北卡罗来纳一个社群的人士写道:“似乎每人都在分享着即将面临最后审判日的感觉。”《全球书目》的编辑斯图亚特·伯兰特报告说:“介绍如何幸存的书最为畅销,它是我们发展最快的项目之一。”这两点反映出人们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的失望日益加深,甚至到了对这种变化理解不了的地步。这也说明了人们为何对当今盛行的心理意识、身体健康和个人“成长”如此热衷。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动乱,美国已完全退缩到彻头彻尾的自我关注中去了。因为没有指望能在任何实质性方面改善生活,人们就使自己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使自己在心理上达到自我完善: 意识自己的感情,吃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学习芭蕾舞或肚皮舞,沉浸于东方的智慧之中,慢跑,学习“与人相处”的良方,克服“对欢乐的恐惧”。这些追求本身并无害处,但它们一旦上升成了一个正式的项目,并被冠以真实和觉醒等美名,就意味着一种对政治的逃避和对新近逝去的往昔的摈弃。的确,美国人似乎希望不但忘却60年代、暴乱、新左派、高校学潮、越南、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执政,而且希望把整个历史、甚至在庆祝其诞生200周年时采用的极其客观冷静的形式所体现的历史,也统统忘却。伍迪·艾伦(5)1973年发行的电影《睡者》就准确地揭示了70年代人们的心理。电影恰如其分地模仿了未来派作家的科幻小说的形式,从很多方面表达了“政治途径解决不了问题”的思想,这一点艾伦也曾在另一处明白无误地宣布过。当有人问艾伦信什么时,他排除了政治、宗教和科学,并宣称:“我相信性和死亡——这两种体验一生只发生一次。”
当前的时尚是为眼前而活——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前辈或后代。我们第一次失去了历史延续感,失去了属于源于过去伸向未来的代代相连的整体的感觉。正是这种历史时间感的削弱——尤其是对后辈的任何关心已被融蚀——才使70年代的精神危机清楚地区别于与之具有表面相似性的早期追求千年盛世的宗教萌发。许多评论家抓住这一表面上的相似点以期理解当代的“文化革命”,而忽视了其不同于以往信仰危机的一些特点。几年前,莱斯利·费尔德勒宣告了一个“信仰的新时期”。更晚些时候,汤姆·沃尔夫把新自恋主义理解为“第三次大觉醒”,狂欢式的、令人心神荡漾的宗教感的爆发。吉姆·豪根(Jim Hougan)在他写的一本似乎既批评又赞颂当代腐败的书中把当前的人心动向比作中世纪衰落时的千年盛世主义(millenarianism)。他写道:“中世纪的焦虑与我们现代的焦虑无甚区别。”社会动乱造就了“追求千年盛世的宗派”,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6)
然而,豪根和沃尔夫无意间提供的证据却让那种把“觉醒运动”当作宗教运动的说法变得不再站得住脚。豪根提到生存一词已成了70年代人的“时髦口号”,而“集体自恋主义”也成了当前的主要倾向。既然“这个社会”已到了穷途末路,那么明智之举就是为眼前而生存,着眼于我们自己的“个人表现”,欣赏我们自己的腐败,培养一种“超验的自我中心”。这些态度在历史上并不能与向往千年盛世的思想联系在一起。16世纪的再洗礼派等待世界末日时并不是怀着超然的自我中心心理,而是带着一种对这个末日所势必带来的黄金时代的难以掩饰的渴望之情。再者,他们从未对过去漠不关心。古代流传甚广的关于“沉睡的君王”——一个将回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恢复失去了的黄金时代的领袖——的传统为当时的那场千年盛世运动提供了启迪。上莱茵河的革命家、《百章书》的匿名作者宣告说:“德国人曾把整个世界置于他们的手掌之中,他们今后还会这样,并将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去做。”他预言道: 复活了的腓特烈二世,即“末日之皇”,将重振德国原始宗教,把基督教的首都从罗马迁移到特里尔,废除私有制,并消灭贫富差异。
这些时常与全民族反抗外来占领者的事迹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曾在许多时候以很多形式,包括以基督教徒对末日审判的看法这种形式而十分盛行。其平均主义及伪托历史的内容显示: 过去时代里即使是最激进、最超凡脱俗的宗教也表达了社会平等的愿望和与更早先的世代之间所具有的连续感。这些价值观的消失正是70年代生存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彼得·马林写道:“在我们中间产生出的世界观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并把个人生存当作其唯一目的。”为了确切说出当代宗教的特殊之处,汤姆·沃尔夫说:“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生活时似乎从未想过他们只有一次生命可活。相反,他们似乎既过着其先辈的生活又过着其后代的生活……”这些评价似乎都一语中的,不过它们又使人们对他把新自恋主义说成第三次大觉醒的提法产生了怀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