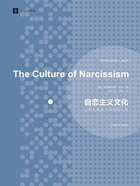
从政治到自我反思
精神治疗的世界观不仅已使宗教不再是美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它同时也威胁着作为意识形态的最后避难所的政治。官僚主义把集体的怨愤转变成了可由精神治疗处理的个人问题。60年代新左派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阐明了这一使政治斗争变得浅薄无意义的过程。然而到了70年代,原先的许多激进分子们自己也接受了精神治疗的意识。雷尼·戴维斯摈弃了激进派政治,跟随起一个叫吉的十几岁的印度教精神领袖来。雅皮士的前领袖埃培·霍夫曼则认为让自己振作起来比鼓动大众重要得多。他从前的盟友杰里·鲁宾也到了30岁这一令人心悸的年龄。他发现自己面临着恐惧和焦虑,于是从纽约搬到旧金山,用他那看来永不枯竭的收入贪婪地购买着西海岸的精神超级市场里的物品。鲁宾说:“从1971年到1975年的5年时间里,我直接体验了埃哈德讲座疗法格式塔治疗法、生物动力学、按摩法、散步、保健饮食法、太极拳、伊塞仑疗法、催眠术、现代舞、沉思法、西尔瓦意识控制法、阿里加疗法、针刺疗法、性疗法、赖希疗法、莫尔豪斯疗法——新意识方面的一门大杂烩式的课程。”
在他那本腼腆地取名为《在37岁成长起来》的回忆录中,鲁宾证实了他的精神治疗法的养生之道对健康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在忽视自己的身体达数年之后,他“允许自己变得健康”起来,并很快使体重减轻了30磅。保健食品、慢跑、瑜伽、蒸气浴以及按摩师和针疗医生都使他在37岁时还感觉到自己“像是才25岁”。精神方面的进步也一样令人充实,且毫无痛苦。他舍弃了保护自己的甲胄,性爱主义和“对爱的依赖”,并学会了“自爱,以使我不再需要靠别人来促成我的幸福”。他开始明白他的革命政治观掩藏了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这种教育使他对自己享有的名声及与其相适应的物质报酬感到不安。他似乎无需在精神方面做出任何艰苦的努力就相信,“享受金钱带来的生活乐趣是无可非议的”。
他学会让性爱“处于适当的地位”,享受它,却并不给它以“象征”的意义。在一系列精神医师的影响下,他向父母和自己内心那个道貌岸然的、惩罚性的“审判员”愤怒地宣战,最后终于学会了“宽恕”他的父母和自己的超我意识。他剪短头发、剃掉胡子,“对自己的形象颇为满意”。现在“我走进屋子,却没人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形象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我。我35了,可看上去却像23”。
鲁宾把他的“心路历程”视为70年代“觉悟运动”的一部分。然而这种“集体的自我反省”不管就个人而言还是就集体而言,都没带来多少真正的自我理解。自我觉悟仍陷于解放主义者们的陈腐术语中。鲁宾谈到了“我本质中的女性特征”,谈到了需要对同性恋持更容忍的态度,谈到了与他父母“和解”的需要,仿佛这些陈词滥调代表着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的对人类境况的非凡洞察。作为一个能熟练地玩弄流行术语的人、一个自己承认能“随心所欲左右宣传工具的人”、一个宣传家,他认为所有的观念、性格特点和文化模式都来源于宣传和“条件反射”。他深为自己的异性恋感到歉意,甚至写道:“男人不能使我激动起来,因为自孩提时起我就受到宣传的影响,因此认为同性恋是病态的。”在治疗过程中,他力图把“孩提时受到的反面教育”重新颠倒过来。他设法使自己确信集体规模的反条件反射过程能为社会和政治变革打下基础。于是他就在自己60年代的政治活动和他目前对自己的身体和“感觉”的关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梁。如许多前激进分子一样,他也只不过成功地把过去他有口无心地高呼过的政治口号换成了今天的精神治疗的口号而已。
鲁宾宣称“70年代的内心革命”起源于对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错误的一种领悟。那种激进主义曾错误地认为“个人成长这一问题可以等到‘革命成功以后’再考虑”,因此它既不思索个人生活的性质,也没触及文化问题。这一责难有一定道理。左派思想过多地成了人们躲避内心生活的恐惧的避难所。另一位前激进分子保尔·茨威格说他在50年代后期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能帮他“从个人生活那颓败的屋子和破碎的花瓶中……解脱出来”。只要政治运动还不可抗拒地吸引着那些企图用集体活动来淹没其个人生活的失败感的人——似乎参加集体活动能从某种程度上消除对个人生活的注意——那么政治运动就不大可能对社会危机、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作出多少贡献。
然而新左派(不同于老左派)的确在它昙花一现的60年代中期触及了这个问题。在那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仅是新左派——渐渐认识到,在今天这个程度上的个人危机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对现代社会作一透彻分析,就必须在解释其他问题的同时,也对为何个人成长和发展竟会变得如此艰难加以剖析: 为什么对成长与衰老的恐惧折磨着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已变得如此脆弱而不安全;为什么连“内心生活”也已无法成为我们逃避周围危险的避难所。60年代出现的一种综合了文化批评、政治报道和回忆录的新颖的文学形式体现了探讨这些问题的努力。它试图阐明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历史及个人体验之间的相互交叉关系。诸如诺曼·梅勒(10)的《夜之军》之类的书籍摒弃了新闻体裁式的客观写作传统,常常探索事物的内部,而不仅仅流于所谓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的一些记录。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无意掩饰自己的存在或观点,他们用小说证明写作活动本身如何成了一个小说题材。文化批评带上了个人和自传特点。虽然最糟糕时它会堕落成一种自我表现,但在它最出色的时候却向我们表明了: 要想理解文化就得把文化对批评家个人意识的形成起着何种作用也一并加以分析。政治动荡使政治成了人们每次讨论都少不了的题目,也使人们不可能无视文化与政治间的关系。60年代的政治动荡一旦有力地动摇了文化可以不受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影响而独立发展这一幻觉,它也就大大地削弱了上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使大众文化成了人们严肃讨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