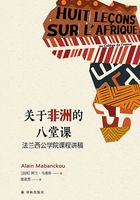
第1章 中文版导读 非洲法语文学的新视域
1921年,法国人将龚古尔文学奖颁发给加勒比地区的黑人作家勒内·马朗(René Maran,1887—1960)的小说《霸都亚纳:真正的黑人小说》(Batouala:Véritable Roman Nègre,1921),从此非洲法语文学正式进入了西方读者的视野。马朗生于巴西北部的法属圭亚那,并不算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年少时,马朗在法国西南部的城市波尔多接受法国教育,寒暑假常常去其父亲工作的非洲旅行。长大后,他在法属赤道非洲谋得了一个殖民地行政长官的职位。他以自己在非洲的经历写成的代表作《霸都亚纳》获奖后,在法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拥有神奇力量、情感经历丰富、战功显赫、狩猎能力出色的族长霸都亚纳。在对人物的生活、命运和生存环境的叙述中,作者展现了法国殖民统治下黑人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法国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罪行,尤其是西方文明对黑人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部“写真主义”小说,非洲黑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富有情感的、感性的而非理性思考的生命。由于在讲述非洲族长霸都亚纳的故事中,作者批判了法国殖民者在非洲的暴行,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具有独立意识的非洲精神,这部小说很快遭到了法国当局的封杀。
不难看出,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觉醒意识是非洲法语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在塞内加尔国父、诗人列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1906—2001)的眼里,马朗是“黑人性”(Négritude)运动的先驱,他的文学创作引发了人们对非洲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也许,正是因为马朗介于法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双重身份,法国才将龚古尔奖颁给了他。这既能显示法兰西帝国的包容,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情绪。存在主义作家萨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殖民统治者看来,这类具有抗争性的文学创作不过是殖民教化过程中一些无足轻重的牢骚而已,尽可让他们大喊大叫直至声嘶力竭,这样也许会使他们感到好受一点。再说,偶尔颁一次奖并不会动摇法兰西帝国在非洲的地位。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早先曾写过一部有关非洲风情的小说,但是,真正把黑人作为小说主要人物来塑造的并不是他,马朗才是当之无愧的鼻祖。在《霸都亚纳》这部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黑人,而且非洲元素十分浓郁。作者不仅采用了一种并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而且尝试了他以前并不擅长的小说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马朗并没有放弃非洲的文化传统,仍然保留了其民族特有的表达形式。为了忠于非洲的语言,他希望写出一个具有“非洲范式”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出黑人性的审美元素。但是,仅仅有审美元素还不够,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小说。确实,非洲小说的原创性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加以研究,尤其是其中口头文学的属性。
过去,在许多西方作家的笔下,有关非洲题材的作品侧重描绘的是秀丽的风光、野蛮无知的土著以及神秘且愚昧的社会习俗,文字里暗含的是欧洲文化以及白人种族的优越感。白人将自卑情结悄无声息地注入了黑人的灵魂深处。当然,这种刻板印象并不是造成非洲“失真”的唯一因素。20世纪30—40年代,桑戈尔、塞泽尔(Aimé Césaire,1913—2008)、达马斯(Léon Damas,1912—1978)、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等一批年轻学者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文学创作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黑人凝聚在一起。在他们的笔下,非洲不再是眼前现实的非洲,而更像一个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他们坚定地扛起反殖民主义大旗,发出了那个时代反殖民主义的最强音。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弱势群体和弱势种族的文学创作开始走出国门,逐渐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代表性的作家有塞泽尔、桑戈尔、达马斯、法农、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1928—2011)、莱伊(Camara Laye,1928—1980)、孔戴(Maryse Condé,1937—)、夏穆瓦佐(Patrick Chamoiseau,1953—)、玛利亚玛·芭(Mariama Bâ,1929—1981)等。
就文化身份而言,黑人性是一个颇具争议且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但是,这一概念带有浓厚的本质主义思想。在《黑人性:非洲文学的伦理》一文中,聂珍钊教授曾经指出,黑人性是非洲诗人从事诗歌创作伦理价值的内核。桑戈尔将黑人的情绪与希腊人的理性进行对比,在竭力颂扬非洲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同时,深入阐释了对“黑人性”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在《论塞泽尔的诗歌创作》一文中,李建英教授指出:“在非洲达姆鼓的节奏下,记忆再现,直抒胸臆,内心暗示,诡秘意象,似乎一切都缘于生命的原始律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桑戈尔出版了诗歌选集《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这部作品堪称黑人性运动的宣言书。在序言中,萨特形象地将黑人诗人比喻成“黑人俄耳甫斯”,这篇序言可以看成是萨特对殖民种族主义情景中黑人性的最本质的回答。有了这篇序言,黑人性的定义(主要在诗歌中)经过不断界定,获得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认可。非洲法语文学成了一种类别特殊、特色鲜明的文学。原始宗教、神话故事、巫术和祭典礼仪常常把读者带进一个神秘而奇幻的世界。在第一代黑人小说家的笔下,格言、歌曲、诗句,甚至在接受者与讲述者之间口口相传的箴言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非洲法语文学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鼓声和歌舞声常常为我们营造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为非洲法语文学平添一种活力四射的动态形象。
几内亚作家卡马拉·莱伊就是非洲法语文坛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代表作《黑孩子》的故事发生于1933年至1948年间,那个时候几内亚还没有独立。小说的开头描绘了主人公巴巴一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父亲神奇的金银加工技艺和母亲神秘的通灵术。莱伊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在他的笔下,法国人开办的学校、当地人提高胆量的习俗“宫登·迪亚拉”以及黑人的割礼场面无不生动有趣。小说的最后,作者追忆了巴巴考进科纳克里技工学校后在叔父家度过的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以及被保送到法国阿尔让特汽车中心后的校园生活。从库鲁萨到科纳克里,从科纳克里到法国,巴巴逐渐走向了成熟。他对城市的生活时而感到兴奋,时而感到彷徨。但是,巴巴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在懵懵懂懂的孩子眼中,没有什么工作比金银加工更加高尚了,唯有打金人的作品才真正配得上“艺术”二字。但是,巴巴又无法将自己视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他本能地感受到内心深处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这种身份上的困惑同样表现在他在丹迪港附近割小麦时的沉思之中:“我不在这儿生活……也不在父亲的作坊生活,可我在哪儿生活呢?”田野里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场面深深打动了他,让他体会到大都市里少有的幸福和温暖。但是,他仍然无法摆脱与出生地格格不入的疏离感。尽管巴巴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份特殊,但他似乎在纷乱的身份迷宫里找到了一个出口:也许自己更喜欢在学校里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就法语文学而言,加勒比地区的法语文学同样举足轻重,因为那里的绝大部分居民都是非洲人的后裔。艾梅·塞泽尔就是其中之一。塞泽尔于1913年生于加勒比地区的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青少年时期,他怀着远大的理想前往法国巴黎留学。20世纪30年代,他在巴黎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朋友一道发起了“黑人性”运动,从此走上文学之路。他用充满非洲意象的法语,表达了强烈的叛逆精神。塞泽尔一生创作颇丰,他的所有创作似乎都立足于他的民族情怀以及“黑人性”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黑人之美、黑色之美都成了他讴歌的对象。他的诗歌代表作是长篇散文诗《返乡笔记》。从20世纪50年代起,塞泽尔开始创作戏剧。通过改写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并颠覆剧作中心人物的主仆关系,塞泽尔以大众化的戏剧艺术形式生动地表达了后殖民主义思想。这样的表达在法语文本里产生了动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塞泽尔并不是哲学家,但是,他巧妙地将辩证法融入主人普洛斯帕罗与奴仆卡利班的关系之中。他以现实主义文风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黑人寻根”,“自尊、自爱、自强”的旗帜,反对种族歧视以及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简单模仿莎剧的故事情节。塞泽尔想告诉观众的是,在普洛斯帕罗和他的女儿米兰达到来之前,荒岛上的原住民卡利班和艾利尔才是岛屿的真正主人,他们在普洛斯帕罗来了之后才成了失去自由的奴仆。
作为塞泽尔思想的继承人,格里桑善于把“文化身份”的思考融入小说中。在第一部小说《裂缝河》中,通过讲述一群马提尼克年轻人的抗争经历,格里桑把神秘的热带小镇朗布里阿纳(Lambrianne)带进了文学王国。在他的笔下,从裂缝河到甘蔗种植园,从山地到海洋,所有的一切无不带有浓郁的安的列斯元素。独特的诗意表达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这种叙事技巧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格里桑将成为加勒比地区的风云人物。尽管当时的人们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评价《裂缝河》时,免不了给它贴上“介入文学”“反殖民主义”“去殖民化”的标签,但是,主流评论仍然看好其独特的构思和新颖的风格。20世纪50年代,格里桑投身革命洪流,为我们展现了马提尼克如火如荼的革命场景。但是,他没有让自己的文学创作完全屈从于时局。在《裂缝河》中,他超越了传统的殖民主义批判。表面上,他描绘的是马提尼克人的革命斗争,但字里行间流露的则是作者对世界性和文化身份的独特思考。
格里桑不但是个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个举世瞩目的思想家。从加勒比社会现实出发,格里桑提出了一种基于语言和文化的世界观,其核心是“群岛思想”“克里奥尔化”“多元世界”等一些全新的概念。在格里桑的眼里,文化与语言之间永恒的、相互渗透的运动推动着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这种全球化能将遥远的、异质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能产生超乎人们想象的效果。格里桑的哲学思想是塞泽尔“黑人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审视了不同文化的杂糅性及其本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群岛思想”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一种具象表达。在这种表达中,他首先关注的是安的列斯黑人的苦难命运,用“旋风”“洋流”“漩涡”等意象来形容安的列斯文化形成的过程及方式,用“安的列斯人特性”给当地的有色人种送上了一剂自我醒悟的良方,打消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寻根梦想。在格里桑的心目中,“克里奥尔化”并不是加勒比海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现象,而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具有了世界性。但是,格里桑的“多元世界”强调的不是文化的同一化,而是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差异和互相包容,尤其是当今边缘文化的前途和命运。他先后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术语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相辅相成,以各自的思想火花共同照亮了我们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必须承认,尽管黑人的文化传统及其内在的精神属于基本的客观存在,但毋庸置疑的是,其特点和表征是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被加工和提炼出来的。为了消除偏见以及提振信心,非洲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把“传统的非洲”描绘成“现代欧洲”的对立面。在他们的心目中,如果说欧洲人是“理性的”,那么非洲人便是“感性的”;如果说欧洲是一个充满剥削和压迫的工业社会,那么非洲就是一个充满和谐幸福、天人合一的人间天堂。他们认为只有这样,黑人同胞才能在世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在不同于白人的价值理念中找到自信和尊严。
控诉殖民历史,直面社会现实是当今非洲法语文学的特点之一。通常,文学虚构总是与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历史的重构能够唤醒人们的记忆,爱与恨的漩涡能让记忆更加刻骨铭心。非洲法语文学以虚构的方式重建历史,同时对后殖民时代的社会不公进行无情的揭露,这就是非洲法语文学特有的认知能力。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1990—)指出:“文学无法改变世界,但文学可以挑战真实,将真实化为美。”毛里求斯的达维娜·伊托(Davina Ittoo,1983—)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的小说《苦难》(Misère,2020)生动描绘了独立后仍处于殖民阴影下的毛里求斯的乡村生活。《苦难》的主人公是个弃儿,整天沉默寡言,他唯一能说的词语就是“苦难”。后来,有个名叫阿尔琼的小伙子心生悲悯收留了他。他们相依为命,音乐成了他俩之间奇特的交流方式。那里的人们深受传统习俗与现代狂热的困扰。小说作者伊托曾在法国生活十多年,回到毛里求斯后开始文学创作。故事的发生地就是他的故乡,但是,这部小说所表达的思想远远超出那个小城,饱含着对祖国毛里求斯的全部的爱。
2003年,法图·迪奥梅(Fatou Diome,1968—)凭借第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大西洋的肚子》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这部小说后来被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2006年至2019年间,她又陆续出版了《凯塔拉》《我们未完成的生活》等作品。相较于斩获各类国际大奖的非洲作家,迪奥梅这一名字在我国则相对陌生。但是,作为新锐作家,迪奥梅是我们了解非洲文学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存在。1968年,迪奥梅出生于塞内加尔的尼奥焦尔,由祖母抚养长大。求学期间,她接受法语教育并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完成了大学学业。1990年,迪奥梅嫁给了法国人并移居法国,1994年前往法国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深造。2021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桑戈马尔守夜者》。这部小说在继承非洲文学传统的同时,重点凸显了非洲女性的生存命运。作者以2002年“乔拉号”沉船事故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库姆巴在丧夫之后,通过写作来重建个人生活的经历。
“暴风雨摧毁了她的一切,而她把暴风雨关进了日记本里。”这是《桑戈马尔守夜者》中一句令人记忆深刻的话,也是这部小说的灵魂。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塞内加尔的尼奥焦尔岛,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谢列尔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主人公库姆巴也是其中之一。库姆巴深爱自己的丈夫布巴,但布巴以及他的好朋友都在“乔拉号”沉船事故中丧生。按照当地的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必须完成四个月零十天的守丧期。在这期间,妻子应穿着厚厚的长袍,举行礼仪繁杂的悼念活动。除了面对丈夫已逝的事实外,库姆巴每天还要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她被残酷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晚上,她就躲进自己的房间写作,记录她在守丧期间的身心体验。写作让她从身心倍感压抑的生活中获得了短暂的慰藉。日记本成了她的避难所,而且让她获得了与世俗的封建礼教对抗的勇气。库姆巴把她的日记本看作海滩上的贝壳。她像个孩子一样,把自己的不幸都说给它听,想通过诉说来摆脱这些苦难。她用书写的方式将一切想法都记录在纸上,在这些文字中,有她对亡夫的思念,也有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从这一点来看,迪奥梅的文学创作既体现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技巧,又继承了非洲口语文学传统。她的语言富有诗意,又不流于感伤。非洲移民的身份认同以及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一直都是迪奥梅创作的主题。不过,相较于男性作家,她的故事大多从女性角度出发,为我们了解非洲女性幽微隐蔽的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相对说来,我国读者对非洲法语文学较为陌生。一方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没有文字记载的传统,早期的文学主要是口口相传的英雄史诗。例如,古马里史诗《松迪亚塔》、索宁凯族史诗《盖西姆瑞的琴诗》以及刚果伊昂加族史诗《姆温都史诗》。直至20世纪中后期,这些作品才被整理出来正式出版,并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这些作品终于让人们领略到非洲法语区各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世界文学史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人操控,似乎非洲人在文学创作上有先天的缺陷,根本不能与西方作家平起平坐、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阻隔在欧洲大陆与非洲大陆之间的不仅仅是地中海,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之间还横亘着一道肉眼看不见的、无法逾越的思想鸿沟。在这道鸿沟中,殖民主义犹如一个可怕的幽灵,给非洲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至今仍无法愈合。
非洲作家早就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试图终结在文学创作上的附庸地位,而且坚信将来有一天最终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希望通过摆脱对法语的依赖,把本民族的历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这种文学是无法摆脱法语而独立存在的。在非洲法语文学中,“黑人性”文化运动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焦点话题。身为黑人在黑人知识分子看来并不是什么耻辱,而理应是一种发自肺腑的骄傲和自豪。桑戈尔、塞泽尔、达马斯、法农等人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完美地诠释了“黑人性”这一概念,而且还在于他们将这一理念大张旗鼓地付诸社会实践。非洲法语文学引发了有关“去殖民”“文化身份”“文化多元”“后殖民主义”等诸多话题的讨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洲法语文学热潮的兴起也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在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黑人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用“黑人特质”“安的列斯人特质”“克里奥尔人特质”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消解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荒谬论调,为纷繁复杂的后殖民时代提供了一盏又一盏明灯,为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的多元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白人中心主义”“法国中心主义”遭遇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尽管作家们的创作倾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奋斗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法国文艺理论家德勒兹所说的“少数文学”不再是“边缘文学”。这种文学摆脱了过去无人问津的窘境,正在大踏步地朝着世界文学的方向迈进。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法兰西公学院邀请了本书的作者、法国作家阿兰·马邦库(Alain Mabanckou)担任讲席教授。1966年,马邦库生于刚果(布)的黑角市,拥有法国和刚果(布)双重国籍,现定居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其代表作有《打碎的杯子》《豪猪回忆录》《明天,我二十岁》《黑角之光》等。马邦库22岁时曾在法国求学,1998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蓝—白—红》,并一举获得当年的“黑非洲文学大奖”。他的作品多次荣获法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并被译为英、西、葡、意、韩等多国文字。2012年,他的作品被授予法兰西学院亨利·加尔文学奖,也曾入围2015年布克国际奖终选名单。2021年11月,他荣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2022年担任布克奖的评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邦库是法语世界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也是法国最负盛名的非裔作家之一。
确实,马邦库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在其代表作《豪猪回忆录》中,叙事者是一只非洲豪猪,但这不是一只平平无奇的野兽!白天它在丛林里和同伴们撒欢,晚上暴露出另一个身份:黑人小男孩奇邦迪的附体。表面上看,这是一只豪猪的故事,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马邦库实际想要表现的是非洲。在这个故事里,马邦库让动物成了叙事的主体,并且让它们具有人一样的性格特征。动物附体的故事设定源于非洲民间传说,“讲故事”的形式也来自非洲口头文学的传统。因此,这部具有泛灵论气息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非洲本土文学色彩。在这个人与动物共存的世界里,动物成了体察世界的主体,而愚蠢自大的人类则成了动物调侃的对象。
成为附体之后,那只勇敢、快活的豪猪离开了自己的伙伴,尽管有时候它并非心甘情愿,但是它不得不听从主人的吩咐,用身上的刺去杀害他人。随着杀戮带来的快感,主人奇邦迪越来越丧心病狂,可怜的豪猪不禁为主人的安危而担忧,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安,因为按照法则,如果主人遭遇不测,附体也得同时死亡。奇怪的是,当奇邦迪咎由自取,被一对双胞胎杀害时,豪猪却侥幸活了下来。整部小说都是豪猪以独白的口吻向猴面包树倾诉心声,讲述自己的命运是如何与一个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又是怎么执行各种“吃人”任务的。由于成了“邪恶附体”,豪猪不仅能听懂人话,而且有了人一样的阅读能力,因此它在讲述自己经历的同时,也抒发了一连串对人类及其文明的长篇大论,为整部小说增添了一种黑色幽默的荒诞喜剧效果。在非洲的生态系统日益遭遇人类荼毒的今天,将人与动物作如此倒置,无疑具有一种警世的味道。正如豪猪所说:“人类并不是唯一能思考的动物。”在这部小说中,马邦库借助传统的非洲民间传说并进行戏仿,让读者领略了独特的讽刺艺术和文学想象。
读马邦库的《关于非洲的八堂课》,可以让我们对非洲、非洲文化、非洲历史和非洲人的认识又深刻许多。在本书中,作者大的文化诉求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对非洲也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确实,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以来,相较于其他大陆,非洲遭遇的一系列苦难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有2亿黑奴被当成牲口一样贩卖到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非洲沦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如今,西方对非殖民战争的硝烟早已烟消云散,但是,这段惨痛的历史不能忘,因为遗忘就等同于犯罪。西方殖民强盗曾经打着“人权”“自由贸易”“重生”“开化”等各种自欺欺人的借口,在坚船利炮的护卫下,把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非洲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这种不对称的殖民战争给非洲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西方殖民强盗在非洲所犯的滔天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西方列强对非殖民战争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惨痛的。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非洲国家的独立,西方称霸世界、瓜分非洲的美梦最终化成了泡影。靠几艘军舰和几门大炮就能占领一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但是,在倡导“文化多样性”“世界多极化”的今天,从不同的层面通过非洲法语文学来认识和了解非洲,尤其是非洲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诉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言以蔽之,铭记殖民历史,任重而道远。
21世纪以来,非洲法语文学的出版、翻译与传播一路高歌猛进。非洲文学也在世界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相关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数量也在直线上升。在我国,“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研究”“非洲法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等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正在把对这一领域的思考和研究引向深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及加勒比海法语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2023年11月,在“文明互鉴与非洲法语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正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徐真华教授所说:“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庞大的命题,非洲文学研究也是切入点之一。语言是人类文明的钥匙,我们用语言讲故事、写历史,人类文明才能走到今天。人类文明的创造,包括文学小说的创作,它的核心存在于语言的密码中,即人类的意识、人类的精神。作为语言学、文学研究者,我们要始终靠人类的智慧、意识和精神,把非洲文学研究做好,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我们的力量。”
刘成富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非洲大湖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2024年2月24日 于南大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