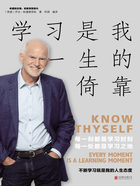
大房子
我们回到希腊后,父亲开始从政,母亲也自然有了更多活动事务。我们家里有了各种各样的人——安保、保洁、保姆、秘书等,他们开始照顾我们。我们需要学习和陌生的人一起生活,并慢慢和他们建立关系。
心理学家经常探讨的一个现象是,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往往更被强调做“对的事情”,而之后的孩子则不然。我的弟弟妹妹们似乎更自由,更乐于分享自我。当孩子变多了时,家长们似乎决定不再带着那么大的压力教育孩子,而是给予他们更多自由,也让自己更为享受。
回到希腊,我们的生活无疑会围绕着大人们的政治活动展开,因此我们家就像一所开放的房子,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进进出出,他们有的人会带吃的来,有的人会留下来吃饭,我们家也像一家餐馆——各种人进来喝咖啡,吃东西,坐下聊天。
很多年后,我弟弟尼克(Nick Papandreou)写了一本书,叫《父亲在跳舞》(Father Dancing),因为在困难时期,我们经常一起跳希腊舞。其中一种舞蹈是一个人在中间跳,其他人围坐鼓掌——这是属于那个人的时刻,他可以尽情表达自己当下的感情。这本书的英国版本叫《一颗拥挤的心》(A Crowded Heart),这个书名指我们从美国搬到希腊后,房子突然就拥挤了起来,每天都有几百人,而不管我们去哪里,都处在人群之中。他从一个有趣的角度讲述了这段故事。
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和多拉·巴戈雅尼(Dora Bakoyannis,曾任雅典市市长和希腊外交部部长)聊过——我们一起作为希腊代表参加了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她还记得小时候,因为她的父亲和我的祖父在一个政党中,因此她时常跟随着她父亲来到我家。当时人们会把我们俩放在一个角落让我们自己玩。她说她记得那时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却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所以有时你的确会感到一些孤单,你只能接受或想办法应对它。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家里雇了一个保姆,她曾在德国受训,对孩子的管理风格非常强硬,比如要求我们下午必须午睡一小时。她甚至会打我的头,有一次我的数学计算题算错了,知道要挨打,于是当她的手甩过来的时候我躲开了,结果她的手打在了桌子上。这下她被激怒了,最终我的下场很惨,被打中了头,撞在桌子上磕掉了一颗牙。
我的母亲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但是保姆转过头来又狠狠地威胁了我们,警告我们别再到父母面前多嘴。那个时候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真是一段难受的时期,一直等到我们要离开希腊回美国的时候,我才敢把真相全都对母亲吐露出来。
在美国,我们只会被当作普通孩子看待,就像邻居家的小孩一样。但是在希腊,我们成了“政治家的儿女们”,他们会随时开始和我们谈论我们的政治立场,问我们问题,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生活中应该做什么。有点像是在说,我必须从政。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并没有想过涉足政治,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我从政是很自然的事呢?
也有一些人会跟我开玩笑。比如保安或者司机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等他有了孩子,而我长大了当了政治家,一定要帮他的孩子找份好工作。我当时才六七岁,心里想的是,如果你的孩子很优秀,找工作肯定不是什么难事,但我怎么忽然感觉自己要担负着好多小孩的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