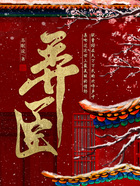
第1章 枕边人
勤政殿的深处,帘幕低垂,有闲散的月光从遥不可及的天井上筛落。
允元屏退下人,揽着长衣赤脚走入来,镶嵌青金石的地面上泛着冷光,像覆了一层薄薄的秋霜。她走到那张宽大的御床边,一时竟还看不清里边的影子,只觉有些微的呼吸声好像从龙凤锦被的缝隙里透了出来。
她已很疲累了。今日朝上议的是南方的水害,一帮老臣梗着脖子逼问她国库存银,她自然是不会应的,但为赈灾安民,也还是需要这帮人去府县上周旋,故不能不虚与委蛇。偏生她又不能表现出疲累的模样,那些人只会认为她因是女人,天生弱些还不承认,连上个朝都要摆脸色给男人瞧。
她往床边坐下,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终于侧躺了下去。
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好好睡一觉更重要的事了。
忽而一只温暖的臂膀缓慢从她身后环了过来,温热微湿的气息倾在她颈项肌肤间:“陛下可回来了。”
柔柔软软、又清清朗朗的声音,含着似有若无的期待,像在跟她撒娇似的。
她闭上眼睛,“嗯。”
“太液池边的凤仙花开了,臣今日去刚好撞见,采了几朵,和着五更天的露水碾出花汁,那大红色比胭脂还好看,薄薄的一层,最适宜入画。”
“入画,画什么?晚霞么?”
“晚霞就很好。”男人笑了,“只要陛下喜欢。”
“你先画,朕看见了,才知道喜不喜欢。”允元懒道。
男人的下巴轻轻蹭过她的发丝,话音巧妙地软下来,将允元引入诱惑的彀中,“陛下今日,不想要么?”
他说着话,揽着她腰的手已窸窸窣窣地伸向衣襟内,却被她按住。她的话音也带了几分冷:“今日累了。”
他却好像全不怕她——全天下人都怕她,偏是他竟不怕她——他笑着说:“您休息,我来动。”
真是个祸水。
沐浴过后,男人在余韵里轻轻吻她的耳根,几缕汗湿的发垂落下来被他抿入口中,还贴着她耳朵发笑。她的表情是享受的,但眼神是遥远的。
她这么想,就这么说了:“杜微生,你真是个祸水。”
他迎着月光微微撑起身子,宽阔的双肩,光洁的胸膛,还有被褥底下一双若隐若现的长而有力的腿。她都冷静地打量着。
她从来不会选次等货上自己的龙床。
他笑道:“承蒙陛下夸奖,微臣愧不敢当。”
她道:“明日去考工署,挑一件你喜欢的玩意儿吧。”
他好像很高兴,还往她耳边又亲了一口,随即便膝行后退到宽大龙床的一角,俯伏下去,“谢陛下恩赏。”
她挥了挥手,像在朝堂上一样。他也就规规矩矩地退下龙床,给她盖好了锦被,还轻轻地拍了拍。
允元没有给他回应,似乎是真的睡熟了。
他无声地穿好衣裳,轻手轻脚地走到了数重帘帷之外,点起了一盏幽亮的长明灯。
一名管事宦官突然从黑暗中出现,半推开了殿门:“公子?”
宦官们不管皇帝床上是什么人,一律只称公子。
杜微生走出门去,那宦官又悄无声息地将门合上了。
“公子回翰林院还是回画院?”宦官佝着身子问。
“翰林院。”他道。
皇帝今日看起来很疲倦,明日大约不会传唤他了。
“是。”宦官应声,低头迈着碎步将他送出了勤政殿,他自家的书童一直在殿外候着,接了他往翰林院走去。
虽在五月末,夜风却已微凉,杜微生想起早晨在太液池边见到的凤仙花,那已是今年的最后几丛。
“听闻南方水害,国库亏空拿不出钱赈灾,今日朝议还吵起来了。”小书童名叫春咏,是宫里分出来伺候他的,许是年少无聊,一路上努力地没话找话。
“国库亏空?”杜微生突兀地笑了一下。
春咏一愣,“大家都这么说……”
“户部的计帐从来都是直送勤政殿,不经宰臣的手,他们如何知道国库的虚实?”杜微生含笑摇头。
春咏挠挠头,“这小的听不懂。公子晚上都会同陛下说这些吗?”
杜微生平和地道:“我说这些作甚,陛下日理万机已经很累了,我还要惹她生厌吗?”
春咏恍然大悟,“公子说得对。”好像终于发现了眼前人圣眷不衰的秘密,乃至于生出几分无知的敬意。
事实也是如此,皇帝自受禅登基两年以来,虽不设后位,但后宫里来来往往的男人已如过江之鲫,俊秀的,硬朗的,柔情似水的,剑眉星目的……皇帝的口味,群臣捉摸不定,也就更上赶着往后宫里送男人。皇帝来者不拒,但都留不长久,大多数都是一两日就打发了出来,长的也不过十余日。
但这个杜微生,自第一次通传到而今,已经在皇帝身边耽留五个月了。
他虽然生得好看,也颇有才华,但算不得特别拔尖的人物。出身乡里,科考取了二甲第二十八名,到翰林院供了个闲职。本来不过是最常见的蹉跎岁月,却不知怎的忽有一日遇见了皇帝,被一眼相中,问对到半夜,第二日就升了翰林学士。他文章写得好是本职,另还喜欢作画,皇帝就给他在勤政殿北边辟出一块地建起一座画院,让他可以专心作画,当然,通传的时候,也更方便些。
外朝群臣都瞧不起他,好端端的进士出身,怎的要这般卖身求荣。但也不乏有人暗地里羡慕他,想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迷魂计,让皇帝对他予取予求。
春咏想着,杜学士说的话真有道理,他要记下来,毕竟这人就是当今天下讨皇帝欢心最有法子第一人。
第二日,翰林院里点卯已过,杜微生才姗姗来迟。其实他在京中没有房屋,仍旧住在刚入翰林时与一众书生们同住的那一排平房,屋檐儿挨着屋檐儿的,就在翰林院的后院。昨晚他从宫中回来,不少晚睡的翰林也都瞧见他了,却没想到他还是会光明正大地迟到。
翰林院分文史书画琴棋诸院,惯常是个风雅清闲的去处,一壶茶闲聊一晌午也无人管。但做到了翰林学士,那就是天子顾问,要随时待命,又赶上今上这样精力充沛、宵衣旰食的君主,勤政殿的吩咐一桩接着一桩,这十几个学士们也并不好过。
暑气从外头卷进来,散在书页衣襟之间,让人心头没的生出烦躁之意。但在这暑热之中,杜微生却好像一个清清凉凉的影子,什么都不贴靠,只孤伶伶地在书架间走动,时而回到桌边落几笔,又思索起什么来。
分给他的差事是今年番邦入贡,要下诏所有州县衙门各司其职,热情款待,谨慎送迎,不能失了上国体面。这一类的诏书年年都有,年年相似,他原本也只需依样画葫芦即可,却不知为何斟酌了许久。
“啪”地一声,是一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下他的肩膀。杜微生转过身,便见是同年入院的林芳景,彼嬉皮笑脸地凑近来瞧了瞧,“嗐”了一声:“我还道是什么了不得的奏议,让子朔兄都为难呢!原来是这劳什子!”
杜微生笑道:“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体,是弟文思迟钝。”
林芳景将眼风往后头一瞥,“你昨晚入内廷了?他们都在议论。”
杜微生道:“是,陛下召我。”
林芳景道:“那陛下有没有问你,南方水害的事情?”
杜微生顿了一下。就在这一瞬之间,后头那几人的议论已入了他耳:“皇上从不留人过夜,就算是他杜学士,也没能让皇上破例嘛!”
杜微生只作未闻,对林芳景笑笑:“没有,陛下昨晚很累了。”
短短若有深意的一句话,与他那似笑非笑的面容,无不透出不可多问的暧昧,甚至让林芳景老脸红了一红。他又在杜微生桌边转了转,实在没趣,也就不得劲儿地走开了。
杜微生终于可以清净下来,思索面前这一道空白的诏书。
他很清楚,这不是什么随便的差事。他的差事,全都是皇帝金口玉言,亲自分给他做的。他若做得好,不见得有功;他若做不好,则一定有罪。
允元这一日则接见了几位前朝的王公。
论辈分,她还要叫他们一声叔伯,但她也知道他们承受不起。接他们到蓬莱亭上,迎着盛夏的荷风,吃着消暑的莲子百合羹,一个下午,她从这几位叔伯嘴里撬出了几万两的赈灾银,还迫得他们应承了去各地安抚人心的活计。
待那些人都离开,已是傍晚,太液池上风声低迷,远处的万寿山顶上是一片灿烂的霞光,摔落到水底,就幻作靡靡的金。
她望着那晚霞光,想到昨夜的男人说,要用凤仙花汁画晚霞。
她开了口:“杜学士的诏书可拟好了?”
亭外的女官杨知礼回答:“拟好了,半个时辰前已送到勤政殿。微臣看过没有大碍,放在陛下的案头了。”
允元道:“拟的什么,你说说。”
“是。”杨知礼略一思索,背诵道,“邦国入贡乃古制,不可轻忽,敕所到州、府、县、道,增饰厨传,依律给食,度有所缺,上礼部酌定。”
“度有所缺,上礼部酌定。”允元低声,“这一句,是过去没有的。”
“是。”杨知礼道,“大约如此更可显得我朝重视,而且于情于理,番邦入贡之事,都由礼部主司……”
允元摇摇头,笑了,“他是在帮朕要钱呢。”
杨知礼怔了一怔,半晌反应过来,“原来如此,微臣愚钝!过去没有此语,地方有亏缺,也只能以税金弥补,再依例做账上报户部,如此所用的实是户部库银;如今说要礼部酌定,则是从礼部出钱……”
允元眯了眼望着晚霞,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沉默。
这个杜微生,乖顺,聪慧,绝不忤逆她,还总能揣摩到她心底去。不论是纸面上的文辞,还是床笫间的动作,全都是她最喜欢的那一种。
但这样的臣子,却不见得是最好的臣子。
因为她仍未看透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