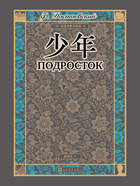
四
总之,在这家地主的众多仆役中,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以外,还有一名婢女,当时她已经约莫十八岁了,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示意他想娶她。大家知道,在农奴制时代,家奴们的婚姻必须在主人的恩准下才得以实现,有时候简直就是奉他们之命的包办婚姻。当时在这片领地附近还住着一位姑姑;她不是我的姑姑,她本人就是位女地主;但是,不知为什么,终其一生,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姑姑,不仅我叫她姑姑,而且韦尔西洛夫家的所有人都管她叫姑姑,其实她跟韦尔西洛夫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这就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当时,她在同一省和同一县还拥有三十五名农奴。韦尔西洛夫的领地(共五百名农奴)倒不是由她来管理,而是因为彼此毗邻,由她来监管,她这种监管,我听说,抵得上任何一位精明的管家。话又说回来,她精明与否同我毫不相干,我只想撇开任何阿谀奉承之词补充一点,这位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是位高尚的人,甚至是位怪人。
正是她,不仅不劝阻郁郁寡欢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听说,他当时阴沉着脸,很不高兴),甚至相反,不知为什么还竭力怂恿,促成此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个十八岁的婢女,也就是我母亲),是个孤儿,父母双亡已经好几年了。她那已故的父亲非常尊敬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由于什么事还十分感激他。他也是一名家奴。在此以前六年,他临终之际,甚至有人说,在他咽气前一刻钟,他让人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来,指着自己的女儿,并且当着全体家仆的面,当时还有神父在场,大声地、坚定地留下遗言:“把她养大后就娶她为妻。”这话大家都听见了。但是他临终时说的话,把它当作死前的胡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他又是一名农奴,他本来就没有这样说这样做的权利。至于马卡尔·伊万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为妻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心里十分乐意呢,还是履行义务。很可能他完全无所谓。这是一个在当时就善于“露一手”的人。他既不是一个熟读经书的人,也不识字(虽然他知道整套的教堂仪规,尤其熟悉某些圣徒的传记,不过多半是听人说的),他并不是那种爱说教爱讲大道理的家奴,他不过是性格固执,有时还有点出格罢了;他说话时很自负,对事情的看法说一不二,最后的结论是,用他自己的奇怪说法就是,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活着”。当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博得了大家的尊敬,但是,也有人说,他让大家受不了。当他摆脱家奴的身份以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只要有人提到他,无不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圣徒,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这一点我深知,而且确信无疑。
至于我母亲的性格,在十八岁以前,她一直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带在身边抚养,尽管这位管家一直坚持要送她到莫斯科上学,而且让她受了某种程度的教育,也就是说,教会了她缝纫、裁衣、走路行动有点姑娘家的样子,甚至还教会了她稍许阅读的本领。至于写字,我母亲从来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学会过。在她看来,跟马卡尔·伊万诺夫的这段婚姻是一件早就决定了的事,因此当时发生的一切她都认为非常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她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样子十分平静,是在这种场合下可能有的最平静的姿态,以致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都说她当时像条鱼似的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关于我母亲当时性格的所有这一切,我都是从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那里听到的。韦尔西洛夫坐车到乡下来,正好是在这场婚礼后的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