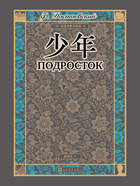
八
最后,为了言归正传,彻底转到19日这个日子上来,我想暂时简短地说一说,即所谓一笔带过,我见到了他们所有的人,即韦尔西洛夫,母亲和妹妹(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妹妹),他们正处在艰难困苦之中,几乎一无所有。关于这点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听说了,但是毕竟没有料到会出现像我看到的那样的情况。我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想象这个人,“我这未来的父亲”几乎笼罩着某种光辉,处处都高人一头,我无法想象他是另一种样子。韦尔西洛夫从来不同我母亲住在同一套寓所里,而是给她另租房子单过;当然,他这样做是出于维护他们那种卑鄙已极的“体面”。但是,现在他们却住在一起,住在同一座木头厢房里,在一条胡同,在谢苗诺夫团[9]。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当光了,因此我甚至瞒着韦尔西洛夫给了母亲我偷偷攒下的六十卢布私房钱。说这是私房钱,是因为每个月都给我五卢布零花钱,我省吃俭用地攒了两年,才攒到这六十卢布;这钱是从我确立我的“思想”的头一天开始攒起的,因此韦尔西洛夫不应该知道一个字。而我担心的正是这点。
这点帮助只是杯水车薪。母亲在工作,妹妹也常揽些针线活儿干;韦尔西洛夫则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任性,挑剔,仍旧保持着许多过去的相应奢靡的生活习惯。非常爱唠叨,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他的许多作风还十分专横。但是母亲、妹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以及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他是一名科长,兼管韦尔西洛夫的一应事务,大约三个月前刚去世)全家(人数众多,而且都是女人),都把他奉若神明。关于这点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要指出的是,九年前他还风流倜傥,没人比得上。我已经说过,他在我的幻想中一直笼罩着某种光辉,因此我无法想象,从那时以后总共才过了区区九年,他怎么会变得如此苍老和憔悴的呢;我顿感悲哀、可怜和羞愧。我对他的看法,是我来彼得堡后最初获得的十分沉重的印象之一。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还根本算不上是老头,他总共才四十五岁;再仔细往下打量,我发现,在他的一表人才中甚至有某种比残留在我回忆中的印痕更加令人吃惊的东西。少了点儿昔日的风采,少了点儿外表的神韵,甚至也少了点儿优雅的风度,但是生活却在这张脸上留下了某种较之过去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的痕迹。
然而,一贫如洗还只占他种种失意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这点我实在太清楚了。除了一贫如洗外,还有某种严重得多的情况——且不说他还有望赢得一场遗产官司,这官司韦尔西洛夫与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打了一年,如果这场官司打赢了,韦尔西洛夫就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一片领地,价值七万卢布,甚至更多。我已经说过,韦尔西洛夫一生已经挥霍掉了三份遗产,现在又有一份遗产在等着使他脱离困境!官司在近期即将由法院裁决。我就是为此而到彼得堡来的。没错,单凭有希望打赢这场官司,是没人会借给他钱的,他们只好暂时忍着。
但是韦尔西洛夫也不出去拜访任何人,虽然有时他整天出门在外。他被逐出社交界已经一年有余了。尽管我十分努力,尽管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整整一个月,我还是弄不清这事的要害。韦尔西洛夫到底有没有错——这对于我很重要,这也是我到彼得堡来的原因!大家都对他扭头不顾,不再理他,而且不再理睬他的还全是些有影响的显贵,过去他在整个一生中尤其善于跟这些人结交,就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风传他似乎在德国干过一件非常卑劣的丑事,最糟糕的还是在“上流社会”的目睹下,甚至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挨了人家一记耳光,打他的人正是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族中的一员,而他居然没要求对方决斗。甚至他的孩子们(合法的,婚生的),一男一女,也对他扭头不顾,另外单过,不再理他。诚然,他的儿子与女儿通过法纳里奥托夫家和索科尔斯基公爵(过去是韦尔西洛夫的朋友),仍然出入于最上层的圈子。不过,在这整整一个月里,我仔细观察他,我看到,与其说社交界把这个傲慢无礼的人开除出了自己的圈子,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把社交界从他身边赶走了。——他的神态是那么孤芳自赏。他有没有这样做的权利——这也正是我感到不安的问题!我一定要在最短期限内弄清这一切,因为我来此的目的就是弄清这人的是非曲直。我到底有多大能量,我还一直瞒着他,但是我必须做的是:要么承认他,要么把他一脚踢开,弃之不顾。如果不得已而选择后者,我将会很难过,我将因此而感到很痛苦。我终将完全承认:这人对我很宝贵!
我暂时还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寓所里,该上班时上班,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对他粗暴无礼。有时,我甚至觉得忍无可忍。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我与日俱增地确信,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向他摊牌,让他向我彻底解释。这个孤芳自赏的人站在我面前简直像个谜,因而使我感到受了深深的侮辱。他对我的态度甚至很亲切,有时还开开玩笑,但是我宁可跟他吵架,也不愿看到这样的嬉皮笑脸。我与他的所有谈话总具有模棱两可、语意暧昧的性质,也就是说,他经常露出某种奇怪的嘲弄口吻。他从一开头对我从莫斯科来此,态度就不太严肃。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样干所为何来。诚然,他达到了目的,他让我看不透他,但是我决不会低声下气到请求他严肃地对我。再说,他还有某些令人惊诧和无法抵御的伎俩,让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才好。简言之,他对我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一样。尽管我早知道会这样,但是我还是感到几乎无法忍受。因此,我自己也不再严肃地说话了,而是等着,我甚至几乎根本不开口。我在等一个人,只要这人一来彼得堡,就会真相大白,我就会知道一切,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不管咋说,我已经作好了彻底决裂的准备,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我可怜我母亲,但是……“或者是他,或者是我”,这就是我想给她和我妹妹提出的建议。甚至日期我都确定好了,而现在我暂时还是去上班。
[1] 伊万诺夫是马卡尔的父称,正规的写法应是“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是民间俗称。
[2] 多尔戈鲁基公爵家族是俄罗斯15至19世纪著名的世袭贵族,所以才有此一问。
[3] 加着重号文字在原著中是斜体,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4] 《苦命人安东》是俄国作家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的中篇小说,最早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6期。《波琳卡·萨克斯》是俄国作家德鲁日宁(1824—1864)的中篇小说,最早刊登于《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12期。《苦命人安东》写的是一名农奴艰难困苦的生活。《波琳卡·萨克斯》则提出当时的所谓女权问题,充满乔治·桑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两部小说都曾受到别林斯基的赞扬。
[5] 本书第三部第七章第一节提到,阿尔卡季曾在韦尔西洛夫的书房里见过母亲年轻时在国外照的一幅照片。
[6] 楷体文字在原著中是法文,以下不再一一标注,其他语种另注。
[7] 作者曾不止一次地批评,俄国当时的法庭常对一些明显的罪犯作无罪判决。律师们关心的不是弄清事实,辨明真相,而是提高自己的律师声望,能使有罪被定为无罪。
[8] 俄国古典中学是八年制。
[9] 旧时彼得堡的一个区,位于芳坦卡河、环形排水渠和奥布霍夫大街(现名莫斯科大街)之间,因沙皇御林军谢苗诺夫团曾驻扎于此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