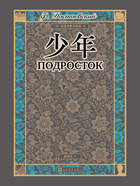
二
伸手要钱,甚至要薪水,如果你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得到这钱的话,那就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恶心的事。然而头天晚上母亲却悄悄地瞒着韦尔西洛夫(“免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1]知道了不高兴”),跟妹妹低声商量,她想把神龛里的一帧圣像拿出去典当(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这圣像特别宝贵)。我在这里工作,月薪五十卢布,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薪水该怎么领。让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什么也没跟我说。大约三天前,我在楼下碰到了那名办事员,我就向他询问:在这里该向谁领取薪水?他露出一副十分惊奇的样子,笑嘻嘻地看了看我(他不喜欢我):
“您还领薪水?”
我想,他在我的回答之后一定还会加上一句:
“凭什么,您哪?”
但是,他只干巴巴地回答了我一句“什么也不知道”,接着就埋头于他那打了很多格子的账簿,把某些单据的账目填在账簿上。
但是,他不会不知道我还是做了点事情的。两周前,他交给我一份工作:让我誊写一份草稿,结果几乎等于重写,我足足伏案工作了整整四天。这是公爵准备递交给股东委员会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意见”。必须把这一切归纳起来,组织成文,然后按照某种文体,予以重写。后来,我同公爵坐在一起,讨论了一整天,商讨这文件,他跟我争论得很激烈,但最后却觉得很满意;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把这文件递了上去。我且不说还有两三封信,也是商务上的信件,也是应他之请由我捉刀代笔的。
讨薪水的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恼火,还因为我已决意辞职不干了,我预感到,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将不得不离开这里。这天早晨我醒来,正在楼上我那小屋里穿衣服,我感到我的心跳起来,虽然我满不在乎,但是,在走进公爵家大门的时候,我又感到了那同样的激动不安。这天上午会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到这里来,我一直指望她来后会帮我弄清使我感到痛苦的一切!这女人就是公爵的女儿,那位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一位年轻的寡妇,关于她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了,而且她与韦尔西洛夫誓不两立,有着刻骨的仇恨。我终于写出了这女人的名字!当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女人,同时我也想象不出我会怎样同她交谈,会不会同她交谈。但是我总觉得(或许有充足的理由),她来后,我心中围绕韦尔西洛夫周围的那片迷雾必将烟消云散。我没法始终保持平静:我心中十分懊丧,刚迈出第一步就那么胆怯,那么手足无措;我感到十分新奇,而主要是又十分厌恶——这就是当时横亘在我心头的三个感受。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整个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关于女儿可能到来的消息,公爵还一无所知,他以为至少还要过一星期她才能从莫斯科回来。我在头天晚上就知道了这事,不过纯粹出于偶然,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告诉我母亲时说漏了嘴,因为她收到了将军夫人的信,而我恰好在场。她俩虽然在悄悄说话,而且又是让人捉摸不透地绕着弯说话,但还是被我猜到了。自然,我并不是在偷听:我看到我母亲听见这女人要来的消息后忽然变得十分激动,因此,我简直没法不听。当时,韦尔西洛夫不在家。
我不想把这消息告诉他老人家,因为我不能不看到,在整个这段时期,他对她的到来感到很害怕。三天前,他甚至还说漏了嘴,虽然是怕兮兮和绕着弯说的,说他担心的是我,怕她来后将因我而找他的麻烦。不过,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家庭关系上他始终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家长的地位,尤其在支配金钱方面。我起先认定,他是个胆小怕事的十足的娘儿们,但是后来我改变了看法,即使说他胆小怕事,说他是娘儿们也罢,他身上毕竟还保持着某种倔强,如果不是真正的刚强的话。常有这样一些时刻,看来,他的性格似乎是胆小怕事和万事忍让的,可是他发起倔来,简直拿他毫无办法。关于这点后来韦尔西洛夫曾对我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现在,我想好奇地提一提,我同公爵几乎从来没有谈到过将军夫人,就是说,我们似乎在逃避这一话题:尤其是我,而他本人则避免谈到韦尔西洛夫,我一下子就猜到,如果我向他提其中某个我非常感兴趣的微妙问题的话,他肯定不会回答。
如果有人想问,在这整整一个月里我跟他到底谈了些什么,我会回答,说实话,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不过总是谈些怪人怪事。我很喜欢他跟我谈话时那种非常天真的样子。有时候我非常困惑地注视着这人,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他哪能像过去似的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呢?像他这样的人只能送到我们中学去,而且只能进四年级——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同学。”他那张脸也不止一次地使我感到惊奇:表面看去一本正经,很严肃(而且几乎很潇洒);一头浓密的灰白的鬈曲的头发,开朗的眼神;而且他整个人很清瘦,身材挺拔;但是他的脸却有一种令人不快、几乎有失体统的特点,它会忽然从异常严肃的表情转变成某种过分轻薄的神态,这也是初次看到他的人无论如何不会料到的。我曾经把我的这一看法同韦尔西洛夫谈过,他十分好奇地听了我的这番话,似乎没有料到我居然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却捎带地指出,公爵只是在病后,很可能也仅仅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我们谈的主要是两个抽象话题——关于上帝及其存在,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以及女人的问题。公爵是一个笃信上帝、十分敏感的人。他书房里挂着一个很大的神龛,点着长明灯。但是他却忽然异想天开——忽然怀疑起上帝的存在,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显然想让我回答。其实,一般说,我对这种想法一点不感兴趣,但是我们俩却谈兴很浓,往往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一般说,所有这些谈话,即使到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愉快。他最爱谈的还是女人,可是因为我不喜欢谈这类话题,没法做他的好的谈话对象,所以他有时甚至觉得颇为扫兴。那天上午我刚去,他就抓住我谈这个话题。我发现他情绪轻快,可昨天我离开他时他还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但是我却必须在今天,在某些人到来之前,解决薪水问题。我估计今天我们俩一定会被人离间(难怪我的心在怦怦跳)——到时候恐怕就无心再谈钱不钱的问题了。但是,由于钱的问题始终谈不起来,我自然很生气,怪自己太笨。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提了一个十分开心的问题,我感到很懊恼,因此我就十分热烈地一口气向他讲了我对女人的看法。结果他倒更来劲了,恨不得搂住我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