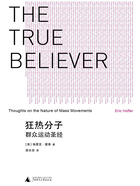
第一部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
第一章 对改变的渴望
1 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是热情的发电厂[1]
很多人参加革命运动,是因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革命运动明明白白就是一种追求改变的工具。
但较不为人知的是,宗教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可以是改变的手段。要实现迅速和巨大的改变,某种广为弥漫的热情或激情显然是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热情是由黄金梦还是由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诱发,则无关宏旨。在美国这里,自南北战争以来各种波澜壮阔的改变就是受到一种激情洋溢的气氛所驱动,而人们之所以会洋溢激情,则是因为感受到有无限自我改善的机会[2]等在前头。不过,在自我改善是不可能或不容许的地方,如果要让声势浩大的改变得以实现和维系,则势必要在别的地方寻求热情的来源。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正是这一类普遍热情的发电厂。
在过去,宗教运动是变革的主要媒介。宗教的保守性格是后起的事,是一度高涨的反抗活力沉寂凝固后的结果。一个勃兴的宗教运动带来的是全面的变革和实验——它会容纳来自各方面的新观点与新技术。以伊斯兰教为例,在其兴起的阶段,伊斯兰教乃是一种促进阿拉伯人团结与现代化的媒介。相似的,基督宗教对欧洲的蛮族亦起过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作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改革运动,都是把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停滞状态摇醒的关键因素。
但到了现代,能实现巨大而迅速变革的群众运动,则是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它们有时是单独发生,有时是合并发生。论热忱、权势和性情的冷酷,彼得大帝大概不输许多最成功的革命运动或民族运动的领袖,但他却未能达成一个他向往的主要目标:把俄国转化为一个西化国家。原因是他无法在俄国群众当中注入激情。他要不是因为不觉得有此必要,就是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憧憬转化为一场群众运动。这就不奇怪,消灭最后一位沙皇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应该会觉得自己与彼得大帝有血缘关系。因为彼得大帝的目标现在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希望达成他未竟其功的理想。将来,布尔什维克革命会被史家大书特书的,除了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企图,还有就是把地球1/6的土地现代化的尝试。
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最后都演变为民族主义运动。这个事实意味着,在现时代,民族主义乃是群众激情最丰富也最持久的源泉,而任何大变革计划想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利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有鉴于此,我们不禁怀疑,现在英国工党政府改变4900万人生活方式的大计之所以阻力重重,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有去营造一种狂热的气氛,没有许诺英国人民一些大而无当的远景。当代大部分群众运动的丑陋面貌,让高雅正派的工党领袖望革命激情而却步。不过,事态的变化仍有可能迫使他们采取较温和形式的沙文主义,以便让英国也得以“通过国家的社会主义化,达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化”。[3]
日本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功是惊人的,但要不是经历过一波民族主义运动,这样的成功大概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大概适用于一些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它们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拜民族主义热情的涌现与扩散所赐。有证据显示,亚洲国家想要复兴,应该借助民族主义运动多于任何其他媒介。凯末尔(Kemal Ataturk)[4]之所以能够几乎一夜间把土耳其现代化,就是拜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助。埃及则刚好相反。即便从阿里(Mehmed Ali)统治的时候开始,埃及的统治者即已欢迎西方的观念,而埃及与西方的接触也频繁而密切,但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群众运动,其现代化显得步履蹒跚。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种有助落后国家革新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把店主和脑力劳动者转化为农人、工人与士兵。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religiofication”(宗教化)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的“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
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在唤醒落后和停滞的亚洲国家一事上扮演直接和积极的角色:它们不是无意就是没有能力唤起亚洲亿万人民的复兴精神。不过,西方民主国家倒是以一个间接和意料不到的方式唤醒了东方:它们点燃了仇视西方的激情。目前让东方从历时多个世纪的停滞中苏醒的,正是这种反西方的热情。[5]
尽管渴望改变往往只是人们投身群众运动的表面动机,但分析一下这种心理,说不定还是可以让我们对群众运动的内在动力有多一分的了解。因此,以下我们会先分析一下这种渴望的性质。
2 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哪怕我们自身的处境是由能力、个性、外貌或健康等个人因素造成,我们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所以梭罗才会说:“如果一个人生了病,无法发挥身体功能,甚或是肠子痛……他就会动念去改革——改革世界。”[6]
失败者会喜欢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世界,这是不难理解的。较不易理解的是,成功者内心深处同样相信——不管他多么以自己的远见、坚忍、勤俭和其他美德自诩——他的成功是环境中各种偶然因素加在一起造就的。哪怕他一直成功,他的自信仍然不会是百分百的。他不敢断言自己知道造就他成功的一切因素。在他眼中,世界是一个勉强取得平衡的天平,而只要这种平衡对他有利,他就不会敢去扰乱它。因此,抗拒变革和热望变革事实上是同源的,前者的激烈程度也可以不亚于后者。
3 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
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改变现状的渴望。要让不满加深为愤愤不平,还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拥有权力感。
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当饥寒逼迫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所以说,贫困者的保守性格和特权阶级的保守性格同样深厚,而前者支撑社会秩序的作用也不亚于后者。
会不假思索就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发动法国大革命的那一代人都深信人类理性的全能和人类智慧的无边——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人类从来没有这样自负过,对自身的全能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信心。随这种夸张自信而来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普遍热望,它会不请自来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冒出来。[7]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子,他们会无所顾忌地投入创造一个新世界,就是因为相信马克思学说无所不能。纳粹没有那么掷地有声的教义,但他们深信领袖不会犯错和新技术无所不能。要不是德国人相信闪电战和新的宣传技术可使德国无敌于天下,纳粹运动会不会进展得如此神速,其中不无疑问。
即使是渴望进步这种良性的渴望,[8]也是受到信仰支撑的:相信人类本质善良和科学万能。这是一种桀骜和冒渎的信仰,思考方式跟那些着手兴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的人相差无几。他们都相信:“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9]
4 怀有大希望者可以从最荒谬的来源汲取力量: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
一般以为,只要是拥有权力的人,自然会对世界抱持傲慢态度,也易于接受现状的改变。但事情不总是这个样子。有权势的人有时也会像弱者一样胆怯。一个人是不是欢迎改变,更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掌握权力,而在于是否对未来有信仰。有权力的人如果对未来没有信仰,就会用他的权力来排斥新事物,以保持现状。另一方面,极不切实际的梦想即使没有实际权力作为后盾,一样可以让人产生最大无畏的胆气。这是因为,怀有大希望者可以从最荒谬的来源汲取力量: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没有信仰是有力量的——除非它也是一种对未来的信仰,除非它含有千禧年[10]的成分。任何教义主张也是如此:如果想要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它必须宣称自己是打开未来之书的钥匙。[11]
企图改造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的人,不可能单靠培养和利用不满情绪成事,单是展示变革的合理性或诉诸强制手段亦不足以为功。他们必须知道怎样在人们心中燃起一个极不切实际的希望,至于这个希望是一个天上的王国、地上的天堂、闻所未闻的财富还是统治世界,都无关宏旨。倘若共产主义者有朝一日能够征服欧洲和大半个世界,那将不是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去煽动不满情绪或仇恨,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宣扬希望。
5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
因此,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野,看来主要系于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害怕未来会让人紧抓住现在不放,信仰未来让人热衷改变现状。富人或穷人、强者或弱者、有大成就者或无所成者,一样有理由害怕未来。当“现在”看起来是完美无瑕的时候,我们充其量会希望它维持下去,因为任何改变只能意味着走下坡。因此,有杰出成就和过得充实快乐的人,通常对剧烈革新都不怀好感。病弱者与中老年人的保守性格也是产生自对未来的恐惧。他们都随时留意走下坡的征兆,感觉任何改变都只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赤贫的人对未来同样没有信心。在他们看来,未来就像是埋在前方路面的陷阱,改变现状就是自找麻烦。
至于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既有特权阶层发动的革命,也有低贱阶级发动的革命。16和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富人发起的革命。当时,毛纺工业高度繁荣,畜牧也比耕种更有利可图。于是,地主赶走佃农,圈禁公地,对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深远的改变。“有时是通过暴力,有时是通过施压和恐吓,达官贵人推翻了社会秩序,使古代法律与习俗为之解体。”[12]另一个由富人发起的英国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就是工业革命。机械化那种令人惊叹的潜力让工厂主和商人头脑火热。他们所发动的革命“极端和激进得不亚于任何思想偏狭者”所发起的革命[13],在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这些敬天畏神的社会贤达就把英国的面貌改变得难以辨认。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14]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15]
6 经验是一种障碍
一头栽进某种变革大业里的人,都必然怀有极度不满情绪而又不是一贫如洗,都必然相信某种万能的教义、某个永远正确的领袖或某种新技术已给了他们所向无敌的力量。另外,他们必然抱有极不切实际的憧憬,深信未来具有无限可塑性。最后,他们对他们要做之事所涉及的困难也必然一无所知。经验是一种障碍。发起法国大革命那些人都是全然没有政治经验的。布尔什维克、纳粹和亚洲的革命家也是同样情形。革命中熟通世事的成员都是后来者,到了运动已告汹涌澎湃方始加入。英国人也许正是富有政治经验,才会对群众运动避之唯恐不及。
[1]本书每章之内的各级小标题,均为中文版提取作者语意而成。——编注
[2]这里的“自我改善”指财富、声望、地位等方面的提升。——译注
[3]E. H. Carr, Nationalism and After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5), p. 20.
[4]土耳其的国父。——译注
[5]见第104节文末。
[6]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Modern Library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 p. 69.
[7]Alexis de Tocqueville, On the State of Society in France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789 (London: John Murray, 1888), pp.198-199.
[8]19世纪的西方人普遍相信人类处于不断进步中,也以追求这种进步为己任。——译注
[9]《圣经·创世记》第11章第4节、第6节。
[10]基督教神学末世论认为有1000 年的黄金时代,其间弘扬基督的精神,接着是末日审判。——译注
[11]见第58节。
[12]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Inc., 1944), p. 35.
[13]Ibid, p.40.
[14]这里“胆怯的人”是指那些不敢在群众运动中与群众一起施暴的人。——译注
[15]“末日四骑士”又译“天启四骑士”,一般是指瘟疫、战争、饥饿、死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