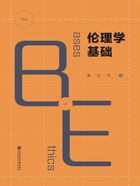
第六节 自由与伦理学
一个人如果认识到自己或他人存在心灵自由,而心灵自由是人们所做出的、不完全被决定的行为的根据或原因,那么对他来说,具有心灵自由的人(包括他自己)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自主选择行为,可以遵守诸如风俗、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等各种规范。当然,一个人所做出的行为并不都是不完全被决定的或是可自主选择的,也包含一些完全被决定的行为。对于那些完全被决定的行为,由于对它们的了解与对自然事物的了解没有根本的区别,因而它们通常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伦理学或实践科学所关注的内容。伦理学或实践科学所谈到的行为往往是那些不完全被决定的行为。由于这样的行为基于心灵自由,因而接受“存在心灵自由”或“人是自由的”的看法也就成了研究它们的前提。考虑到这一点,除非特别说明,这里所谈到的行为是指那些不完全被决定的行为,有时我们也简单地称之为自由行为。
尽管“存在心灵自由”或“人是自由的”观念的确立使伦理学或实践科学有了基础,其意义却也不可夸大。一方面,对于伦理学来说,仅仅研究一般行为产生的条件(如心灵自由)是远远不够的。伦理学主要关心“何种行为是合理的”或“人在实践活动中应当做何种行为”之类的问题。无论是合理的行为还是不合理的行为,很可能都是不完全被决定的行为,都要以心灵自由为根据。然而,人们不能仅凭心灵自由而断定一行为是否合理,或断定人在实践活动中应当做何种行为。也正是如此,对伦理学来说,一旦确定了心灵自由的存在,了解到了它的有关性质,对它的主要讨论便已完成,就不能停留于此,而需要进入下一步的讨论中。西季威克是清楚这一点的,他说,意志自由的“伦理学意义可能被夸大”,“任何严肃而缜密地考察这一问题的人都将发现这种意义是极其有限的”[23]。
另一方面,那些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尽管没有对心灵自由的存在做出可靠的论证,但基于直觉,他们也能获得对心灵自由的一些了解,可以由此确定心灵自由的存在。实际上,他们在进行相关思考或日常判断时,常常设想存在心灵自由。正如物理学家没有对自然哲学做深入研究,他们直接接受一些本体论信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物理学的探索,也可能获得伟大的物理学成就一样。那些没有对心灵自由做深入研究的人,基于直接认定“存在心灵自由”的信念而进行伦理学探索,也能推进伦理学的发展,甚至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些人竭尽全力希望证实心灵自由的存在,明确所谓“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并试图完全或主要基于心灵自由来建立伦理学。可以预见,这些做法要么没有太大的意义,要么困难重重。就基于心灵自由的伦理学而言,它尽管比较花哨,但其内容往往是贫乏的。之所以如此,与它面临如下的两难有关,即伦理学家如果严格坚持这种自由的含义,断言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就会发现,这种自由能为任何可能的行为提供根据;然而,他一旦要基于这种自由构建伦理学,就有必要告诉人们,何种行为是合理的,何种行为是不合理的,就要给出判定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当他试图给出这样的标准,试图为实践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时,他就必定要冲破这种关于自由的设想。这时的伦理学要么不完全或不主要基于心灵自由,要么其中的自由就将包含一些其他的含义,以致人们在理解自由时将难以避免地出现诸多混乱与歧义。
这种混乱与歧义可一再地在康德的著作中发现。康德没有把心灵自由与理性自由区分开,因而当他把自由当作他的伦理学的“拱顶石”时,他的“拱顶石”其实是一堆混凝土。西季威克就曾指出,康德及其追随者没有分清两种类型的自由。他说:“如果我们说就一个人是在合理地行动而言,他是一个‘自由的’主体,那么当他在不合理地行动时,我们显然不能在同一意义上说他是根据自己的‘自由的’选择而不合理地行动的。”[24]萨特也试图基于自由建立起他的伦理学。他强调,人是自由的是指他可以自主地进行选择和行动,也即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具有怎样的规定性,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他是完全自由地造就他自己,并创造出他自身来的。因而他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先定的,而是由人自身创造出来的,即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到此为止,萨特所谈的自由与心灵自由没有太多的区别。但当他试图从这种自由观引出某种伦理观念时,就越出了这种含义,以致出现了混乱。在萨特看来,人具有自由表明除了要对自己负责外,还必须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他提出:“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25]人的自由尽管表明他可负责,却不能告知他要担负何种责任。萨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直接以一个道德家的方式来说话。他说,“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一个人在选择时,“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26],等等。
这里不准备表明不可基于自由观念来构建伦理学。不过,如果不加区分地把各种自由含义混合在一起,并希望由此来构建伦理学,那么将会发现,这种伦理学尽管辞藻华丽,语句晦涩,但难以掩盖其中的言辞混乱、思想矛盾。试图从事这种工作的伦理学家当然也可能区分心灵自由与其他自由,或者基于某些特定的含义来使用“自由”一词。不过,由于这种伦理学并不常见,同时也由于其自由的含义不太符合日常的用法,基于它的伦理学常常难以运用于生活实际,因而这里不打算关注它。我们之所以在此讨论自由问题,主要是为后面的讨论提供基础,以便可以放心地谈论后面的问题。当然,它也使后面的讨论尽可能少地受那些基于自由的伦理学的干扰。鉴于不同自由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难以对它们进行清晰的区分,为使后面的讨论更为清晰,在谈到除心灵自由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自由(如政治自由、身体自由、情感自由等)时,将使用诸如规范、身体阻碍、行为等语词来表达或替代,而一般不使用“自由”一词。除非特别说明,我们将用“自由”一词特别地指心灵自由。
[1]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08页。
[2]Richard Sorabji,“The Concept of the Will from Plato to Maximus the Confessor”,in The Will and Human Action: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Thomas Pink and M.W.F Stone(eds.),Routledge,2004,p.15.
[3]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72页。
[4]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11页。
[5]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569页。
[6]斯马特:《伦理学,劝说与真理》,载万俊人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51页。
[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433页。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10~11页。
[9]约翰·L.卡斯蒂:《虚实世界》,王千祥、权利宁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第221页。
[10]费希特:《伦理学体系》,梁志学、李理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53页。
[11]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5页。
[12]休谟:《人性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82、289页。
[13]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王新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349~350页。
[1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435页。
[1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11页。
[16]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224页。
[17]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564~581页。
[18]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22页。
[19]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第37~38页。
[20]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26页。
[21]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51页。
[22]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09页。
[23]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88~89页。
[24]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81页。
[25]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708页。
[26]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