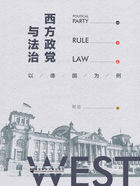
导论
宪法是政治法。按照宪法的制定设想有效地调控一国的政治活动,是制宪和修宪的基本目的。即使宪法实施不能带来一国政治活动的健康,也至少要保证政治活动的稳定。如果宪法不能有效回应一国政治活动的需要,无法将规范上的效力转化成现实中的效力,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这种调控作用,最终沦落成纸面上的宪法,国家的政治生活或者将陷入无序,或者另一套自说自话的“政治宪法”大行其是,使人们对宪法失去尊重和信心。
不幸的是,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过程中,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宪法对于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政党活动严重关注不够。政党不是宪法学研究的传统对象。大部分宪法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都是公民和国家机关,在两者之外或者说两者之间,仿佛不应再存在第三类主体。政党是一类特殊的政治社团。目前研究者在讨论社团宪法权利时往往倾向于认为,社团权利来自公民权利,如果社团在宪法上也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利或义务,那更多的是因为,社团是公民结合的产物,是公民主张和实现自身权利的组织手段,社团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宪法权利义务。
这些倾向同样存在于西方各国的宪法发展史中。西方国家的宪法实践,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固守公民和国家机关才是宪法实施当事人的思想。在这种保守思想的影响下,虽然各国的政党政治进行得如火如荼,西方国家的宪法思想和制度实践却一度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承认政党的存在。这种无视现实的思想,也是西方国家宪法发展中遭遇过很多问题和挫折的思想源头。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和挫折的反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的宪法,以德国基本法为代表,都开始或多或少地承认政党的宪法地位、重视政党法治问题。随后,政党活动法治化的问题普遍进入了各国立法者甚至修宪者的议程,最终带来了许多宪法和法律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出了西方宪法、法制和政治制度发展的新动向。由于西方国家在世界民主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宪法在政党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以及带来的制度变化,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继承和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世界课题。
德国在政党法制建设方面的成果最丰富,相应的,在西方国家宪法政党制度研究方面,德国学界的研究也最为丰富。无论是作为对整个政党法制研究成果的政党法评论[1],还是针对政党取缔、议会党团、政党姐妹组织如政党基金会这些专门问题,德国学界都积累了厚重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形式法治传统的国家,德国学者对政党法治问题的研究,更多地还是从规范法学的视角出发,以法教义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概念分析、规范演绎,没有或者不愿充分面对政党的特殊身份,即政党是在现代法治实践中高度能动的一个组织,其本身具有法律规范的创制和修改权利。当政党具有这种特殊身份时,研究者仅利用形式法治的视角分析政党法治问题,可能会带上不切实际的静态法治观。例如,在关于政党和联邦宪法法院关系的问题上,德国政党法学者多是将一个个的宪法判决作为既成事实来讨论,认为这是联邦宪法法院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在规范演绎的基础上,逻辑必然正确的结果。或许这些政党法学者内心也意识到了过于形式化的思维的不足,但是受学科界限的影响,他们不愿或者说无法跳出制度形式的限制,去分析制度背后的运作逻辑,例如,联邦宪法法院针对政党制度的各种判决,究竟会对政党制度的运作、对政党与联邦宪法法院的关系造成何种现实影响,政党究竟是顺服地听从联邦宪法法院的指示,还是努力想赢回重新失去的领地。当然,这些问题不是典型的“法学”问题,有观点会认为这是一些“政治学”的话题。但是针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会影响到相关法律制度的现实运作,法学研究人员其实是不能回避讨论它们的。
其他西方国家对宪法政党制度的研究,不及德国学界这么全面。其他西方国家,多为发达的民主法治国家,政党制度已经比较成熟。由于在这些国家宪法发展的早期阶段,各国宪法普遍不承认政党的存在,也就谈不上专门的政党立法。当国家的民主政党政治已经成熟后,也不需要一部调整范围广泛的政党法,所以与德国不同,这些国家都没有制定统一的政党法典。规制政党活动的法律规则,或者是散见于其他选举法、社团法中,或者只有针对政党活动某一方面的法律,例如政党财务问题的规定。[2]在西方国家中,德国具备相对发达的政党法律制度,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德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水平在西方国家中一度是非常落后的,只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后来者居上。这种有意理性设计、赶超式的发展过程,也为德国民主法治建设在政党法治领域留下了丰富的制度遗产。
目前国内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对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有了比较长期深入的研究,但是从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的视角全方位研究该问题的著作还不多。
崔英楠教授2009年2月出版的《德国政党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践》[3]一书,对德国政党法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开创性研究,对政党宪法地位、政党取缔、政党公共资助、党内民主等政党法治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都进行了一定的展开讨论。但是正是因为该书的开创性,该书的内容更多地侧重于制度介绍和既有学说引用,对于政党地位宪法化、政党活动法治化的深层原因和问题,例如德国民主政党国家理论对西方传统宪法思想的继承与扬弃、政党制度与基本法其他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论述不足,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引申空间。
如果说崔英楠教授的著作偏重于制度介绍,那叶海波教授同样出版于2009年的《政党立宪研究》[4]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偏向理论思辨的对照。该书力图对政党地位宪法化问题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为了实现这种全面研究的目的,研究者往往首先需要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论框架,所以《政党立宪研究》一书的理论论说较多,作者在这些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党法治实践中的各种制度运作情况。但是与德国政党法学者的研究思路类似,该书也带有一定的静态法治观,认为政党是在宪法实施和法制运作中逆来顺受的被规制主体。而且在重视比较研究的情况下,该书对个案的深入剖析尚显薄弱,无法充分揭示政党与宪法制度的互动关系,这也是该书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地方。
正是在这些前人宝贵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力图在研究过程中,将理论推演与制度实践分析结合起来。本书先从理论设想出发,分析制度设计的目的,然后再在制度运作的具体过程中,分析制度设计目的、理论设想是否得到了切实的落实。考虑到政党在西方宪法实施过程中的高度能动地位,本书还重点关注了政党在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政党与相关宪法制度的互动关系。在讨论理论问题时,面对西方国家在制宪思想、民主政治制度设计目的上的高度趋同性,本书进行了一定的比较研究。在讨论制度实践问题时,为了比较深入地揭示制度实践的真实面目,本书选取了有发达的政党法律制度的德国作为讨论的个案。
本书分为三篇:政党地位宪法化、政党活动法治化、政党与宪法制度的互动。第一篇侧重于理论和世界比较研究,第二篇更多地从形式法治的角度出发,分析政党以及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第三篇则重点讨论政党在制度设计、运作和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在“政党地位宪法化”一篇中,本书讨论了西方国家政党地位宪法化现象背后的理论变迁史,以及通过政党公共资助制度表现出来的政党宪法化的具体实践。本篇包括第一、第二两章。在第一章中,本书主要从理论视角出发,讨论了西方国家宪法对待政党问题的看法转变。在第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宪法早期实践中,普遍存在厌恶政党的思想,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宪法不仅不承认政党的存在,相反,还会想方设法抑制其活动空间。例如,英国宪法以限制大众参与并逐渐扩大选举权的方式来限制政党影响,美国宪法利用分权原则和联邦主义在限制政党活动空间上做出了大量制度安排,大革命后初期的法国宪法实践更是对政党极端憎恶。但这些抑制努力从未成功,政党活动依然在宪法的重重限制下发展开来,相反,政党活动有时还会对宪法实施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如美国宪法对在总统选举中加强政党作用的第十二修正案、政党活动对法国第三共和稳定的支持。这种将政党视作宪法之敌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论、政治哲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历史背景根源,其也为西方国家的早期民主法治实践带来了许多挫折和教训,其中最大的挫折和教训就是魏玛共和的垮台和纳粹政权的登场。正是因为德国在政党问题上吃过最大的亏,德国基本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了民主政党国家理论,在继承传统制宪思想的基础上在政党制度上有所创新,将政党引入宪法并强化了其宪法地位,甚至一度承认了政党是垄断政治代议功能的政治中介。
第二章讨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的政党公共资助制度。政党地位宪法化是纠正过去敌视政党思想的产物。正是因为这种宪法化代表着对政党的宪法肯定,落实这种宪法化,宪法实施不能只是提供一些纸面上的肯定式的规定,还需要相应地赋予政党各种权利。这种宪法肯定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了政党公共资助制度,该制度的设计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用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限制金钱对政治的过度影响,实现选举权的绝对形式平等。不过深入的研究也显示,该制度在实践中也面临许多问题,突出地表现为该制度对国家政治和政党内部治理结构的反民主性的影响,其过度修正了金钱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削弱了政党活动对民主政治的一些积极影响,并在民主政治中造成新的不平等即政党间的不平等,这些都是政党公共资助制度的立法者始料未及的,这揭示出政党地位宪法化对西方宪法思想和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篇的主题是“政党活动法治化”,即在政党地位宪法化后,政党在西方国家的宪法实践语境下,相应地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应当履行哪些义务。从本篇开始,本书重点讨论德国的例子。在政党是西方宪法实施中的关键当事人的情况下,政党的宪法权利义务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宪法制度的方方面面。本篇共三章,重点讨论了三个关键问题:政党活动的宪法边界、政党议会内活动的法治化实践、政党党内活动的法治化实践。
第三章以德国基本法政党取缔条款为例,讨论了政党活动的法治边界。正如公民的宪法权利会受到限制一样,政党地位宪法化后,其宪法权利也不可能是无限的。出于对传统宪法思想忽视甚至敌视政党的态度的认真反思,并且吸取了魏玛共和垮台和纳粹政权登场的历史教训,德国基本法第21条第2款运用民主政党国家理论和自卫民主理论制定了政党取缔条款,对政党的宗旨和活动划定了宪法边界,以此来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但是20世纪50年代联邦宪法法院做出的政党取缔判决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审判色彩。政府在决定是否提出取缔申请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投机考虑的影响,这进一步削弱了德国民主过程的开放性。2003年,三联邦机关提出的取缔德国民族民主党的取缔申请因为程序问题被联邦宪法法院驳回。后联邦参议院又独自提出了取缔该党的申请,但是在2017年,联邦宪法法院在肯定了该党违宪性的同时,又以该党不具有现实危害性为由驳回了取缔申请。联邦宪法法院的这种态度转变表明,政党取缔条款和自卫民主理论在德国基本法实践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这种衰弱主要是因为自卫民主理论本身存在的矛盾,从这一点上看,政党取缔条款无法承担起保卫民主的重任。
第四章讨论了德国政党的议会内活动的法治化实践。议会是西方国家政党的传统活动领域。民主政党国家理论的出现和运用标示着德国宪法实践的新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政党的议会内活动制度相应地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本章重点考察了德国联邦议院的党团制度。在德国联邦议院中,党团是在议会组织、活动与资源分配中有着明确宪法地位的基本单位。党团合宪地位的确立,是在基本法完成了对经典宪政模式中贤人政治和整体人民观的批判、引入政党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才实现的,前两种观点以基本法议员独立条款为表现,该条款依然为议员相对于党团的独立提供有限保护。为了发挥党团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基本法规定了党团相对于议会、政党独立。党团相对于议会独立的本质,是少数党团相对多数党团的独立,只有实现了这种独立才能落实立法与行政分权制衡的宪法原则,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围绕着党团成立条件与资助平等。随着政党社会动员功能的萎缩,党团对政党的控制日益加强,但是为了督促政党保持并扩大其社会基础,有必要保证政党相对于党团的独立性,对此,德国的实践主要从切断党团与政党的法律与经济联系着手。
第五章讨论了德国政党党内活动的法治化实践。德国法律对政党的党内候选人推选活动规定了比较详细的保证党员参与以及选举前后的审查制度。实现民主政党国家理论期待的政党帮助人民有效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宪法功能,并保障作为公民的党员的选举权,都要求政党的党内候选人推选实现民主化,并需要国家的监督。但是为了保护政党自治自由,党内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国家的干涉。从制度实践上看,目前德国政党党内治理存在民主制度空洞化的问题,不同政党区别对待党员的选举权有可能损害选举平等权原则,在选举举行前对公民的救济机制存在严重限制。在选举后司法机关对选举活动的审查过程中,议席相关性标准是判断选举是否有效的普遍标准。对于党内候选人推选活动中存在的违法事实是否足以否定选举的有效性,目前德国司法机关间还存在不同意见。这些理论和制度实践中的问题都揭示出,对于政党这类特殊的宪法实施当事人,法治监督的作用是有限的,更多地还需要加强政治监督以实现一个民主的宪法政党政治。
第三篇以政党与宪法制度的互动为讨论主题。第二篇的讨论在很多地方显示出,与更多的只能利用制度的普通公民不同,具有巨大政治能量的政党不会乖乖地听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制。有时它们会规避各种制度约束的要求,有时它们会索性去修改制度,使制度符合其政治利益。在前文的研究情况介绍中,本书也提出,目前的国内外法学界对政党问题的研究,可能是囿于学科的界限,对政党与宪法制度的这种动态关系讨论不多。本书的第三篇就想在这一领域有所推进。在本篇,本书也运用了一些历史分析、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
第六章讨论了政党与重要的横向分权制度之一——违宪审查制度之间的关系,选取了德国政党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之间的互动作为讨论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活跃在西德政治舞台上的少数几大政党,在反思魏玛共和失败和纳粹政权恶政教训的基础上,在对直接民主的厌恶情绪中,通过间接民主的程序制定了联邦德国基本法,相应地创建了联邦宪法法院。制宪各党期待联邦宪法法院扮演解决政治争议的中立仲裁机构的角色,希望宪法法官能够懂政治并受政党人事控制。在联邦宪法法院的运作中,法院面对作为整个人民代表的各政党时表现出高度的克制态度;面对作为一个政治阶层的各政党时是与其分享基本共识的谏言人;面对作为政治过程弱势群体的单个政党时,积极保护政党间的实质机会平等和政党代表的公民的形式平等。联邦宪法法院在政党的紧密人事控制中,成功创造了其政治中立的形象并获得了高度权威,有效扮演了政治争议仲裁者的角色,实现了政党与法院的双赢。这种成功部分来自联邦德国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联邦德国的法律和政治精英高度重视基本法的实施,法院也充分利用其作为一个司法机构相对于政治机构所具有的优势。
第七章重点讨论了政党与重要的纵向分权制度之一——联邦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像基本法规定的联邦宪法法院制度一样,基本法中对联邦制度的规定也是制宪各党妥协的产物。在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联邦制度的运作受到政党制度的影响,出现了严重背离制宪各党预期的情况。实证研究显示,政党制度会对联邦制度的运作产生中等偏强的影响,而且联邦制度的活跃程度更多地受到反对党因素的推动。个案研究显示,当联邦政府的决策涉及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时,例如在央地财政制度领域,政党制度对联邦制度的运作有可能会失去影响力。这表明,虽然基本法由政党主导制定,政党也希望垄断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权,但是,当制度运作起来,新的政治当事人登场后,这些当事人会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形成自己或与政党重合,或与政党冲突的利益诉求。联邦宪法法院如此,各级政府也如此。这些利益冲突的存在,也显示出了基本法民主政党国家理论的不足,以及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影响力的有限性。
[1] 目前在德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政党法评论有:Jörn Ipsen,Parteiengesetz:[Gesetz über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Kommentar,München:Beck,2008;Schönberger,Sophie,Parteiengesetz und Recht der Kandidatenaufstellung,Handkommentar,Baden-Baden:Nomos,2011。
[2] 关于欧美国家中政党资助问题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Michael Koß,The Politics of Party Funding:State Funding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Western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Karl-Heinz Naßmacher,The Funding of Party Competition:Political Finance in 25 Democracies,Baden-Baden:Nomos,2009;Keith Ewing and Samuel Issacharoff eds.,Party Funding and Campaign Financing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Oxford:Hart Publishing Ltd.,2006。
[3] 崔英楠:《德国政党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 叶海波:《政党立宪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