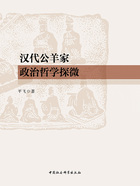
二 儒家政治哲学的主题关键词
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12]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段话,突出了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中心和焦点意识——“务为治者”。而所谓治者,其实就是政治。
在中国古代,对政治的哲学思考,有一个字很有哲学味,这就是“道”。它的意义非常丰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规律、原则、模式、方式、方法、境界等。所谓天道、地道、人道、王道、霸道、周道、汉道、君道、臣道等都涉及政治根本问题,其中王道、霸道、君道、臣道专论政治的根本问题。讲到这些“道”的话,就涉及对政治规律、政治原则、政治制度、政治模式、政治境界等的讨论。到了现代,这个“道”字还和“政治”两个字拆开来连接使用,这就是“政道”与“治道”。这是现代新儒家牟宗三的创造。问题是,中国古代是否言“治道”而不言“政道”呢?牟宗三有一个断语:“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有政道之治道是治道之客观形态,无政道之治道是治道之主观形态,即圣君贤相之形态。”[13]这个断语是立足现代民主政治的立场来论述的,是在自造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概念框架中来评价的,意在肯定儒家有精美的治道。[14]所以当他说:“人类自有史以来,其政治形态,大体可以分为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以及立宪的民主政治。(马克思从经济立场,分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彼以经济决定政治,倒果为因,而人类表现精神,实现价值的奋斗,遂泯灭而不见,今兹从政治形态方面言,而不从经济方面言,则人类表现精神实现价值之奋斗自可豁然。)从政治形态方面言中国文化史尤见贴切而合真实。如果立宪的民主政治是一政治形态,有其政道,则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亦各是一政治形态,亦当有其政道。如是,吾人可进而论以往中国之政道之意义。”并说:“政道者,简而言之,即关于政权的道理。无论封建贵族政治还是君主专制政治,政权皆在帝王(夏商周曰王,秦汉以后曰帝)。而帝王之取得政权而为帝为王,其始是由德与力,其后之继续则为世袭。吾人论以往之政道,即以开始之德与力及后继之世袭两义为中心而论之。”[15]这显然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政道”,而不是他心中理想的“可以被称之为政道的政道”。如果不把理想的标准随时介入一般的论述中来,就是按照牟宗三的概念框架,其实中国古代也是既言“治”又言“政”的,是既讨论治道、治权又讨论政道、政权的。至于中国古代讲的是什么样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大可不必和自己认定的“理想的政道与治道”混为一谈,造成讨论的前后矛盾。在我们的讨论中,自己的“理想的政道与治道”暂且悬置。至于牟宗三认为马克思“经济决定政治”是“倒果为因”,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是反对的。而就一个社会形态而言,“政”与“治”是一个整体,“政道”与“治道”是一个整体,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古代的儒家治道不可能和现代的民主政道嫁接在一起,即所谓古代有古代的政道与治道,现代有现代的政道与治道。
谈论儒家政治哲学,除了这个“道”字外,还有很多其他古代固有的术语,如王政、善政、仁政、暴政、虐政、善治、乱治,以及王化、王制、德治、礼治、法治、人治、教化,还有正名、正君心、修己安人、大一统、奉天承运、改元改制,等等。这些概念及其具体展开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与宗教、伦理关系以及对政治的神圣根源、人性基础、制度结构、核心理念、言说方式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认识。
翻开五经元典,政治的哲学思考深深把握到了政治的根本问题。在《尚书》中,对天命政治、民本政治、道德政治的思考都很有哲学味。《尚书·五子之歌》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泰誓》所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中),等等,深刻地触及了政治合法性的哲学思考,体现了对天命政治与民本政治的形上探求,即“政治的天”或“天的政治”与“政治的本”或“本的政治”。《尚书·尧典》所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禹谟》所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蔡仲之命》所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深刻地触及了政治道德性的哲学思考,成为以后伦理政治的直接基础,即“惟德是辅”与“为善于治”,即“政治的善”与“善的政治”。[16]
《尚书》中言说的政治合法性、政治道德性,《左传》中显露的政治秩序性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具体说来,特别表现在围绕以下几组概念展开思考。
一是“有道无道”,这组概念是最根本的,重点探讨“政治的善”与“善的政治”,涉及政治伦理性、政治合法性、政治秩序性,以及相关的政治批判。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有道的社会就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天子、诸侯、大夫、庶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享其乐。孟子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有道的社会是一个道德的社会,贤德起主导作用,而不是权势武力起主导作用。儒家讲的天道、地道、人道,仁道、王道、君道、臣道,无不为凸显“政治的善”。儒家以“伦理的善”直贯推广到政治领域。孔子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孟子的“王道仁政”、“民心君心”,《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都把政治往“善的境界”上推,往“个体的德性”上推。王道、霸道与无道,仁政、暴政与乱政,周政与秦政的对比都在凸显“政治境界”的高低,“政治善性”的有无。顺天应人的天意、民意既是对良善政治的诉求,又是对政治合法的论证,其合法又通过“受命”与“革命”的合法具体体现出来。“道”与“善”是一切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二是“君道[17]臣道”,这组概念是最重要的,涉及君权合法危机、君权转移继承、君主权威维护、君主责任义务、君权约束制衡、君心教化格正、君臣君民关系、君相外戚宦官权力关系、君主家事与国事、家天下与公天下等一系列问题。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强调君臣要名实相符,各尽义务,各有所得。孟子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在这里,孟子突出君臣要效法尧帝以仁心行仁政。荀子专辟君道、臣道进行详细阐发。他说:“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荀子·君道》)在这里,荀子强调君主要善群能群,善于用人治国。孔孟荀虽是各有所重,但都积极探讨君道臣道问题。在古代社会,不管是贵族世袭政治,还是君主专制政治,“圣君贤臣”事实上始终是政治的真正主体,决定着整个政治的走向与兴衰,因此是仁政是暴政还是乱政,关键取决于君臣,正所谓“为政在人”。《礼记· 中庸》载哀公问政,孔子的回答指出了君道臣道何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荀子·君道》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认为人治优于法治:“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儒家认为良善政治关键在于圣君贤臣,如此化政治为道德,化外王为内圣,无疑是人治主义。
三是“修己安人”,这组概念是最概括的,涉及儒家对道德与政治、心性与事功、治心与治世、个体与秩序关系的哲学思考。谁不是一个个体己?谁能够脱离人群体?己要成人必修己以德,成就独立人格,心安理得,己要合群就需安人以善,追求秩序和谐,立人达人。孔子之后,孟子讲“仁心仁政”,荀子讲“修身隆礼”,《中庸》讲“成己成物”,都不出其外。而《大学》又作了系统的展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宋儒朱熹将此概括为“三纲八目”。这个人心人生图式本可以适应每一个生命个体,因为每一个生命个体都面临着一个自身修养的问题,都面临着如何推己及人的问题。但在封建社会,人君操生死大权,人君“修己安人”对于整个社会和谐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18]与明儒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把这个后人称为“内圣外王”的纲领直接指向帝王君主,又进行了充分的衍义,简直发挥到了极致。[19]宋儒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说:“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感,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明儒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序言中说:“臣惟《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孔子承帝王之传,以开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万年,所以为学、为教、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内圣外王”表明了儒家把秩序治理扎根在个体修养上的逻辑进路。儒家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传心经世”、“立教垂世”,体现了对政治的独特精微哲学思考。
四是“仁义礼乐”,这组概念是最核心的,既是道德范畴,又是政治范畴;既关涉个体心性,又关涉社会秩序。儒家辨群己关系、公私关系、义利关系、王霸关系、理欲关系,仁义礼乐都贯彻其中,而归根到底落实在社会生活中,都是为了实现合理秩序。仁与礼相比较而言,仁更向内指向人心,而礼更向外指向人身。礼与乐相比较而言,礼更强调异与等差,而乐更侧重同与和合。孟子重仁义,在心性上着力,更有理想主义品质,荀子重礼法,在王制上着力,更有现实主义精神,殊途同归于孔子的仁礼并重。孔子讲德治善治,体现在孟荀那里就是仁政与礼治,仁政反暴政,礼治兼法治。仁在儒家那里可谓全德,礼更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礼在各个领域,无论是道德、政治、教育、军事、宗教乃至日常生活中,都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具有政治功能、道德功能、宗教功能、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心理功能[20],正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上》)。一句话,无论是做人、行事和治国,都非礼不成:“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归结到孔子的说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即是“克己复礼为仁”。仁义、礼乐、刑政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关键词。仁义精神与礼乐制度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根本标志。
五是“民心民本”,这组概念是最动人的,充分地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生命价值。从《尚书·五子之歌》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孔子讲“富民教民”,再到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及荀子讲“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先秦儒家一以贯之地强调民心的重要与民本的地位,并围绕此阐发了像明儒丘浚所概括的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憨民之窃、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虞等一系列关于经济民生、政治民生、文化民生的思想。在儒家看来,善政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解决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得民心,得了民心就可以王天下、安天下、治天下。
当然,不同的儒者对儒家政治哲学的主题以及核心理念进行阐发的重点、路径、话语是各有不同的,可谓一本而万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