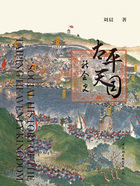
绪论
太平天国史研究曾是中国史研究领域内的“显学”,甚至一度被作为专学而冠名“太史”“太学”。但自20世纪末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主要与其研究领域之广、研究成果之多造成的研究难度加大有关。[1]太平天国史研究虽已硕果累累,但并不代表没有耕耘的余地。任何学科的发展创新,都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与开拓。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飞力(Philip A.Kuhn)“从中国内部事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方法和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以宗教为主线,以社会史为角度探索太平天国兴亡轨迹的视角为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2]国内学界则没有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太平天国史研究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与之相比,美国学界在近几年形成了一股研究太平天国的小热潮,以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和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著作为代表。
2013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梅尔清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中译名)提供了一个研究太平天国的新视角。[3]过去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侧重于以政治史和革命史的视角观察战争的历史进程。而梅著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的民众,她希望建立起战争与日常生活和个人感受的关系,从民族国家和革命史的叙事语境中超越出来,展现平民在战争中及战争后的经历。
梅著的研究主要有四点创新,值得借鉴:一是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民间话语体系与政治话语体系的剥离;二是突出个案研究,重点介绍了善士余治、乡绅张光烈的事迹;三是叙事时空的延展,例如政府、民间对死难者的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四是“内战”的语境,“叛乱”“革命”的消失,理解个人情感,描述生活、体验和身体。特别是民间视角下的太平天国史构建,是既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2012年,美国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助理教授裴士锋的《太平天国之秋》出版,该书将小历史置于大历史中通盘衡量的视角是传统中国史学较为缺少的,将太平天国战争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全球市场等因素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非常新颖。2013年,台湾卫城出版了《太平天国之秋》的繁体中译本;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简体中译本,引起国内学界对太平天国的再次讨论。[4]
两部研究各具特色,又互相弥补。梅著从民间视角观察太平天国,裴著则从宏观的全球化视野解读这场中国内战;一个是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的“小”视角;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大”着眼。不同视角下的太平天国应有不尽相同的历史形象。视角的转换和开拓对更加全面地认知太平天国十分必要,也有助于推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过去学界讨论的政治视角和革命话语体系下的太平天国历史形象已经被充分展现,而对民间视角下太平天国的历史形象缺少理性的建构和评判,这却是关系深化认识“天国”陨落的原因,审视太平天国历史地位、评价历史人物和总结历史教训的重大问题。单一的民间视角可能无法完整反映太平天国时代的全貌。社会史研究倡导自下而上与上下互动的研究取向,力图以历史的多重面貌,探讨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复杂性。[5]所以在强调眼光向下的同时,以太平天国历史发展变迁为主线,将民间视角融入宏大的政治叙事语境中,关注太平天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以期通过全景式的描绘呈现太平天国政治权力与地方社会(民众)的互动,探讨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否存在“特殊镜像”,借以总结“天国”陨落社会层面的历史原因和教训。至于重点研究的对象,应该从死难者的身后之事转移回当时幸存者的切身感受,可能对重新评说这段历史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