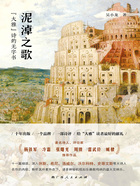
诗歌,一个新物种的诞生
——读休斯《思想之狐》

休斯是个痛苦的诗人,就像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张照片那样:他霜冻般的头发扭着结,双眉紧锁,皱纹深陷,似乎是被其卓越的才华与浪子般轻浮的生性——这奇异的联合体煎熬而成;而那耷拉的脸,更像是被他一生长久的愁苦地心引力般吸引着垂向地面,那黑暗的中心。他沉浸于痛苦中无法自拔,这似乎成了人们对休斯的一般印象。然而,另一张照片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那里喜悦变得极为具体,生动得似乎可以跳出画面以更新人们的固有印象:在一条阳光辉映的流水河里,他穿着单薄的白色衬衣,挥舞着长长的钓竿,一脸欢笑。黑白胶片没有褪去这巨大的欢乐的色彩,反而让它如颗粒般放大,变得更直接。在这里,完全不同于那蚀刻、沟壑般的眉间褶皱,不同于那黑暗的情绪,休斯像从未被那恶魔的诅咒封印,他释放、舒展,如那空中回转为几道美丽弧线的细长鱼线——在那尾端是喜悦的果实,一条鱼。
钓鱼,是休斯小时候就萌发并延续一生的爱好。事实上,幼时的他除了钓鱼,还喜欢捉小动物——各式各样的动物是他生活中的精灵,陪伴着他的生活,牵引着他的喜怒哀乐。而成年后,这些精灵,虽然已经不再是他现实生活里的一部分,却成了他倾尽一生打磨的艺术——诗歌的主题:他以动物命名的诗集《雨中鹰》成名,此后出版的不少同类诗集,《穴鸟》《林怪》《望狼》等,也多以动物命名(他的不少童话也是如此);而随便翻阅,各样的动物诗大量充斥着他每一本诗集;甚至,乌鸦——这种他所谓的最聪明的鸟类,许多神话的核心、极端神秘的动物,从始至终贯穿他的著名诗集《乌鸦》,成为笼罩在每一首诗上面挥之不去的乌黑的影子。因之,休斯被称为动物诗人。
从动物到诗歌,从捉小动物到写诗,这中间,似乎存在神秘的一跃。它如同放大镜中生物的细胞分裂,既无比自然,又仿佛是得自不可思议的上帝之手。那么,对于休斯而言,从现实的生物走向纸上的造物,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动物与诗歌,动物的身体、呼吸、行动、生命,与诗歌的语言、节奏、结构、意义,不管是比喻上的还是隐秘的,它们有着怎样的关系;进一步,动物以及日常的物事,它们是如何走向诗歌的?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经由休斯被提出来。
如何解开上面的线团?“《思想之狐》翩然而至,之后我提到的其他诗篇相继而来。”休斯如是说。在《思想之狐》之前,休斯已经有了十余年的写作经验,但休斯把它称为自己的第一首动物诗,是他诗歌生涯的起始。在诸多休斯的选本中,这首诗都被放在开篇,甚至在《巴黎评论:诗人访谈》的采访提问中,《思想之狐》被当作休斯诗学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这首诗对于休斯的重要意义。因此,理解《思想之狐》,细究它的外在触须和内部神经,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对于理解动物与休斯诗歌的转化关系乃至洞悉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就有了某种可能性。
一、动物,世界“普遍的枯索寂灭”
休斯说,他的自我意识开始于两三岁。如果说之前人处在一种物我不分、朦胧混沌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人开始区分“我”与外在的“物的世界”。对意识初开的孩子来说,此时,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奇迹和新鲜的世界,意味着全新的经验,而接近和了解这些事物,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对于休斯而言,这种经验更进一步,因为它与动物有关。休斯从小就生活在动物的世界里,动物玩具,动物照片,充满他年幼的记忆和世界。据休斯描述,在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对动物产生了兴趣,他从店里买来铅制动物玩具,四岁的时候,姑妈又给他买了一本厚厚的绿皮动物书当生日礼物。而他哥哥对狩猎的强烈爱好和热情,让他走出动物的玩具世界,被狩猎和动物世界迷得神魂颠倒。大约八岁时,休斯一家搬去南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小镇,但那些年的日记,里面除了记录捕猎物,别无所有。就这样直到十七八岁,除了书本之外,对动物的沉迷构成了休斯生活的全部。
休斯幼年的记忆让我们看到,物的世界,在休斯的动物世界里得到拓展,经验因为动物得到了最大化。从一开始的“不动”的“动物世界”——从铅制动物玩具、绿皮动物书,到狩猎的世界,一个活生生的动物世界。这个世界迥异于自己熟悉的周遭世界,而那些动物(在休斯诗集中随处可见),它们来自无数陌生的山林、河流、大海和天空,蜥蜴、蛇爬行,兔子、鼬鼠蹦蹦跳,老虎、豹子地上跑,鲑鱼、梭子鱼水中游,喜鹊与鹰空中飞,它们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它们与这个世界的照会方式,它们所沉浸的那个精微的时空,它们观察与表达的方式,都全然不同于我们,不同于那个混沌的世界。动物,大大更新了幼年休斯的生活经验,拓展了世界的范围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们让这个外在经验的物的世界得以最大化。
然而,“到了十五岁左右,我的生活变得比以前复杂,我对动物的态度也改变了。我责怪自己扰乱了它们的生活”(《诗的锻造》,杨铁军译),此时,休斯开始变换立场和角度,他已经隐隐发现,人的意识也无比微妙和复杂,神秘莫测。那个曾经与自我融合的动物世界,开始表现出独立的意识,开始拒绝,开始离自己而去。这是一个意识的危机。这也代表了物的世界的极限和边界。对于休斯,甚至对任何人而言,这意味着意识初开的惊喜之后一个最新的困局:它们不可避免地变得具体、重复而贫乏;它们短暂易逝,难以把握、难以驾驭——这个物的世界,是一个有局限的世界!而对于我们而言,越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抛掷出去,就越有可能触碰到那个更重要的、精神的临界,并反弹到自身。这时,他遇到更多的是精神的困惑。此时,他已经开始创作,但留存极少。休斯说,这时的写作似乎也是因为“老师和同学们觉得有趣”;休斯还没有将自己更为复杂的精神经验,与外在世界有效整合为一个有效的物质体;他还未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与语言投射的对象。
直到几年后《思想之狐》的写作,它让休斯跨出了飞跃性的一步。此时休斯已经二十多岁了,他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了。一天深夜,下着大雪,在伦敦一个阴郁的住所,他写了这首诗。休斯将住所解说为“阴郁”,当然也影射了他的精神处境,他说,“那篇(《歌》)之后,我保存的诗作是那首名为《思想之狐》的诗,这期间是六年的混乱。六年!这也是我读书读到自己也碎成一地的时期,尼采说学生就会如此”(《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明迪等译)。显然,此时休斯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物的世界的局限问题,“阴郁”“混乱”“碎成一地”“尼采”……这些关键词,都暴露了休斯的精神处境,据说,早期诗歌写作的中断,从文学跳到人类学,对世界的信任危机,都证明休斯开始面临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休斯在后来回忆《思想之狐》写作时,将它表述为“普遍的枯索寂灭”。
正是这“普遍的枯索寂灭”,推动了休斯的《思想之狐》的诞生。更重要的是,它们既是推动力,也是“解脱力”——是他要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之所在。休斯用了一行诗交待自己的这种处境,于是,这首诗就开始了:
我想象这午夜的森林
在午夜,外在世界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东西。这里影射的就是休斯面对的问题,“普遍的枯索寂灭”。但是,作为这首诗的起点和背景,作为一首短诗,从写作技术上来说,花费大量笔墨将会让它显得滞重;而另一方面,它又是这首诗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无法忽视。而这句惜墨如金的诗,一方面显得轻描淡写,就像它的外在形式一样——仅仅一行诗,仿佛可以一笔带过;另一方面又让它不可忽视,有力地奠定了整首诗的基调。这种效果的实现,很大的原因得益于它化用了但丁《神曲》的前三行:
在人生的中途,
我发现自己在一片幽暗的森林,
迷失了正路。
对照《神曲》的查尔斯·S.辛格尔顿英译本,两首诗的内在关联是明晰的:一是年段相仿,两诗都由词缀“mid-”引导,但丁用“midway”(“中途”)、休斯用“midnight”(“午夜”)来比喻自己处在人生的“中途”;二是意象相似,但丁是“dark wood”(“幽暗的森林”),休斯则为“midnight moment,s forest”(“午夜的森林”);三是处境相似,但丁“迷失了正路”,而休斯也处在“阴郁”“混乱”中……休斯的这种巧妙借用,以极简的方式融入了一个富于高度隐喻色彩的史诗巨构,尤其是在对其物的世界的局限和精神困境的表达上,将中年但丁的痛苦、迷惘以及他对死亡和来世的思考等,都化为《思想之狐》最丰赡的背景音,它就像一个丰富却又模糊的景深,让前景中的事物变得全然不同:休斯的一叶扁舟如同在黝黑的深海上穿行,凸显,放光。
而更重要的是,但丁通过穿越三界以获得解救,获得醒悟和净化,这也是《思想之狐》首先要解答的重要问题,是这首诗推进的方向:它与《神曲》一样有着同样的黑森林,同样希望在迷途中探出一条路来。所以,从诗歌技术而言,《思想之狐》的第一行巧妙借力史诗《神曲》,这样,一首二十四行短诗的起点就举重若轻,不同凡响。
二、思想之狐,一个新物种的诞生
《神曲》的影响伴随着这首诗,它暗示了一种走出黑森林的方式:但丁由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引领,由黑森林出发,穿过地狱和炼狱,最后到达天堂,在那里,将见到他暗恋的情人,他在现实世界中无法相遇的贝雅特丽齐的灵魂。对于中世纪的但丁而言,这种解救是诗学上的,但更是神学的。然而,超越的宗教维度却是休斯极力摆脱的,休斯这首诗的发展,走出这个黑森林的过程,并非由一个幽灵引领穿行于浩渺的三界,而仅仅是在一个场景,由一个新的物种探索和引领。
有什么别的东西还在动
在这孤寂的时钟和这张
我以手指摩挲的白纸之外。
这是第一节的后三句,一方面,它进一步延续了上面的问题,呼应了但丁式的现实处境:“孤寂的时钟”,这是抽象的概念化表述,它是时间的单一、重复,也是生活的孤独与寂寞;同时,时钟也暗示着终结——死亡,这可谓“普遍的枯索寂灭”的极致状态。然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它提出了解救的方向,它明确,在“孤寂的时钟”所代表的“普遍的枯索寂灭”之外,“有什么别的东西还在动”。仿佛一个无限放大的焦点,这一活物的“动”,突然之间,让这“死亡”活了过来。那个令人窒息的世界摇晃了!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摇晃世界的活物,让全诗的焦点发生了神奇的转换,精神的困境转移到了一种类似“物化”的解答中,休斯提供了自己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全诗呈现的,就是这个活物在黑暗中从蠢蠢欲动到逐渐现身的过程,也是这个活物引领诗的发展走出黑森林的过程,更是一首诗由灵感逐渐印满纸面的生成过程。而在这些推进过程中,黑森林的现实性与象征性,对但丁宗教性的挣脱和世俗的回归,旧世界的克服、新世界的诞生,始终相互交缠、相互伴随,并呈螺旋式上升状态。从下面开始,我们将跟踪它,呈现这个神秘的活物如何闯入、搅动并引领我们的世界的过程。
第一个问题:这个摇晃世界的活物在什么地方?物的僵死世界和精神寂灭的世界,与这个活物是不相容的,它定然在我们“之外”,在时间“之外”(时钟代表时间)。但是,如何理解这个“之外”?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东西——它在外在的“物的世界”、自我的“精神世界”乃至彼岸的“宗教世界”“之外”吗,什么东西可以挣脱这三重枷锁呢?第二节的第一句更深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透过窗户我看不见星星
窗户隔绝屋内和屋外,透过窗户,可以呈现不同的理解视野,所以,它似乎代我们更深地提出了上面的问题。如果屋外仍是现实,休斯将再次遭遇困境,物的世界的局限一直在那里。透过窗户,是一个主动的向外寻求的动作,“窗”有一般的摆脱效果;或者向更高远的实景,将自己的有限愁绪化入无垠,这是我国诗人抒情的惯用方法;或者,寻求更广阔的、更高深的意义,如康德所言,头顶灿烂的星辰,这是超越性的、外在于我的意义的显现,这种超越性,再往前走一步即是宗教性的象征(星星与宗教有着一般性关联,比如,星象学家、东方三位博士知道基督诞生,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代表基督的星星出现在天空)。但诗人很快封闭了这种路径:我看不见星星。那个活物,不在于我,也不在于高悬于我“之外”的遥远意义、超越宗教的闪光。休斯拒绝陷入轻巧的浪漫主义,拒绝走向超越性的救赎。
那么,这个“之外”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英文中,“biside”,它除了“除……之外”,也有“在旁边”“与……并行/同时”的意思,也就是:它就在我们旁边,与我们并行。它在说,这个活的东西,一方面有别于我们,在荒野、在森林;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深刻关联,就在我们手和纸的近处。所以这句诗就变成了,在时钟、手指摩挲的白纸的同时/旁边,有什么别的东西在动。休斯强调的是它“在旁边”与我们“并行/同时”,它所诉诸的并非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宗教性解答。于是很清楚,虽然“手指”和“白纸”仍属于“物的世界”,但是除了它们,尚无其他更好的接近那个神秘活物的方式,因为它们离我们也离“活物”“最近”。这里,休斯通过自己手指的“动”(“move”),与那个活物的“动”(“alive”),从意义的关联和隔行的押韵,以极为凸显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呼应关系。它似乎在说,因为手指的“动”(写诗),成了接近那个活物的唯一方式,它们同等重要(也就是诗歌与活物的关系)。这样,全诗就同时聚焦于这个活物以及手指的活动上了。然而,以手指月,手并非月,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biside”在“之外”与在“旁边”的这种矛盾关系,后面更进一步进行了强化:
更近的什么东西
但没于黑暗中更深
正进入这孤寂
从场景上说,天空没有星星,于是休斯将目光从窗外移到近处,移到手边、纸边。但是他所寻求的,并非眼前的事物,对眼前“物的世界”的厌弃和解脱是这首诗的出发点。休斯企望的是前面提到的活物,然而它与纸和笔仍隔了一层,所以他强调,是“更近的什么东西”。并且,休斯将它描述为——“没于黑暗中更深”,似乎休斯勉为其难,只能借助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更近”。但它又更远,它在黑暗中,“黑暗”是客观的场景,伦敦深夜住所外面一片漆黑;也是休斯的心境,内心“阴郁”和“孤寂”——它是物的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阻塞凝滞、晦暗不明。但是,这里强调“更深”,在于黑暗意味着未知和神秘性,它是新的发端和可能——那个既不属于物的世界、精神世界又不属于超越性宗教世界的活物,就来源于这“黑暗中更深”处,来源于一种物的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混沌、汇合的地方。这是一种柳暗花明,因此,这个“黑暗中更深处”,它既遥远又迫近,既杳无踪迹又真实具体,外在于黑夜又内在于心灵:它是物我相互敞开交缠的旋锥。
冰冷,细微,似那暗雪
一只狐狸的鼻子碰触着枝,叶;
两只眼睛转动了,一下
又一下,一下,又一下
第三节,活物出现的第一阶段:狐狸有了生命气息,在黑森林中蠢蠢欲动。这一节的第二行,交代了这活物“本尊”——它是一只狐狸。为什么是一只狐狸?这与休斯以及狐狸本身有关。对于爱动物、爱捉小动物的休斯而言,狐狸是让他一直很沮丧、“从来没有养活过”的动物,它是休斯失败的记忆;而作为动物,狐狸精明、灵动、变幻、难以把握,在众多文化中,它都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介于灵和物之间,休斯将其称为“小妖精”“一个幽灵”(对于写作而言,没有比它更适合形容人的念头的了)。狐狸妖艳、迷人,因此,从未捕获成功的休斯,希望在一个新的世界(纸上世界)长久地将它捕获。
这狐狸出现的过程并不容易。前面三行,随着一行一行推进,狐狸的动静,鼻子,眼睛,几乎是一帧一帧地逐渐揭开神秘面纱的,这种句式的错落和主语的放大,加强了狐狸出现的诡异感,也强调了它出现的艰难。第一行,你还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有“冰冷,细微”的迹象,它显得遥远、脆弱、几微,随时可能消失不见。第二行开始露出鼻子,“鼻子”(它对应的呼吸)首先出场,让我们想到西方文化,上帝吹了一口气,于是事物有了呼吸,而有了呼吸新生命才真正开始。第三行,狐狸“两只眼睛转动了”,如果说呼吸意味着生命,那么眼睛则如探灯,它意味着解开身体的捆绑,可以将视野投射得更远,探索更为开阔的世界。于是,诗句进一步明确“动了”,“有鼻子有眼”的生物真正“活”起来了!对于休斯来说,与那个持续的枯索的世界对照,这种别样的生机太难得了,因此,在一首短诗中,第三和第四行连续两行,并没有提供更多信息,而是被“now”充斥,“一下,又一下”,急剧的重复,加之狐狸眼睛本身的圆滑、灵动感,仿佛让我们感觉到,它和我们一样,因为新生的激动,沉浸在一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和喜悦中!
这节诗可以分为左右两边,一边是主语狐狸,另一边是狐狸带动的宾语,二者刚好构成一种对照,上面我们看了左边,下面看一下右边:第一行“似那暗雪”,它提示这是一个冰冷的被霜雪覆盖的世界,在句子结构上,它在狐狸出现之前,似乎成了一种阻碍,考验那新生灵的出现;而同时,雪铺天盖地,雪意味着掩盖原有的物的世界,意味着探索新世界的可能(雪当然也是对有待书写的新世界的暗示)。第二行,“触碰着枝,叶”,触碰,是感受这个世界最原始的方式,而“枝叶”,它意味着生机,向上生长,在句子结构上,它在“狐狸”出现之后,似乎在说,因为狐狸的出现,克服冰雪和黑暗,走出黑森林就有了可能!暗雪在前,枝叶在后,中间是狐狸作为主语引领,这似乎在说,狐狸终将克服困难,走出黑森林。这一节,就像一场庆祝,“触碰”这个词的原文“touch”,它也是感动、震动的意思:狐狸初现,带来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冲击和新鲜的感动,不同于那“普遍的枯索寂灭”!
这一节诗有着多重的隐喻关系:它关于狐狸生命的迹象(意象选取极富代表性,有鼻子有眼,有呼吸);同时也是对写作的暗示,诗的灵感闪烁,诗的呼吸和节奏,都与诗歌的推进存在内在关联;它还是对探索“黑森林”出路的一种准备,那只战战兢兢却又极富生命力的狐狸,开始蠢蠢欲动,它似乎兴奋又迫不及待,想要在这个冰封的黑森林中探索了。
把整齐的足迹印进雪里
在树林间,小心翼翼,一个瘸行的
影子在树桩边缓缓移动,
空荡荡的身体将大胆地
第四节和第五节,是活物出现的第二个阶段:狐狸现身,它探索并走出了黑森林。第四节,狐狸在有了生命力后,它开始行动,在黑森林里探索,“把整齐的足迹印进雪里”,因之,这神秘而不易捕捉的生灵开始有了踪迹,那白雪地有了清晰的痕迹。而那个迷宫般的黑森林,在“树林间”出现了新的线索,它正努力试探出一条路来。但是,在冰天雪地中探索,坑坑洼洼,一瘸一拐,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这里的“stump”,除了“树桩”的意思,也有“困难”之意(它是克服困难的界标),那只狐狸,很可能在途中就折了足、迷了路,再一次隐没于黑森林中,它如同一个游移在冰天雪地的黑森林中的影子(“shadow”,也可以译为“魂魄”,也或可见与《神曲》的关联),未必可以确定走到我们面前,未必能引出一条出路。所以,“warily”是小心翼翼,也是一个警告。这当然也是写作的隐喻,比如雪地之于白纸,隐喻着写作的艰难探索和尝试,就像休斯所说的,狐狸并不是总能出现的,“正如那么多次,我捕获的猎物并非我之所欲的时候,我所做的那样”“我会将它丢进废纸篓”(《诗的锻造》)。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stump”的多义可以在这里复合,困难即是界标,一旦被克服,经受住了考验,狐狸终将克服黑暗,大胆地穿越,越来越真实。
穿过开阔地,一只眼睛,
一种扩张着、加深着的绿,
闪亮地,全神贯注地,
干着自己的事情。
经过艰难的探索,经过冰天雪地,狐狸穿过一个个“stump”,终于得以从黑森林中走出,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在这里,通过狐狸灵动的眼睛,我们得以看到其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原本黑漆漆、空落落、白茫茫的世界,正如前面“枝叶”所暗示的,它有了生命的颜色——绿色,并且它扩张、加深,变得一片生意!这崭新的绿意,绝不同于屋外黑漆漆一片,也不同于内心枯索寂灭的灰暗——它闪闪发光(“闪亮”)。这里再次与前面呼应,我们看到,由开始休斯的“透过窗户我看不到星星”,到这里,由于狐狸的出现,它走出了黑森林,闪闪发光,给灰暗枯索的世界带来了光亮。
但是,这狐狸的出现,不同于物的世界,又不全然是主观的造就——它“全神贯注地,/干着自己的事情”。狐狸自行探索,全神贯注,干着自己的事情(“own business”),它不能被人为惊扰,如同那绿意,那光亮,它扩张、加深、延展,它是自我独立的。狐狸的这种独立性,其实就是诗歌的独立性,诗歌写作,并非“我”的一意孤行(那是精神的黑森林)、主观造就,正如休斯所说,诗“也拥有自己的生命。和动物一样,它们和人保持距离,甚至和作者也保持距离,写成后既不能增,也不能减,否则,分毫之差都会对其造成致命的损害”(《诗的锻造》)。诗歌,就像这只狐狸,它有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灵魂,“每一首诗都是其自身创作过程的一种描写或戏剧化”(《巴黎评论:诗人访谈》)。
三、诗歌,客观有效的纸上新世界
那只雪地上的狐狸,从最开始它微弱的生命气息,到它开始探索,克服难关,穿越黑森林,来到敞亮的开阔地——它实现了自我。而这一切,都来自它的专注,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全神贯注地深深沉入“自我”。但是,这狐狸想象的自我,倘若不客观化、物质化,不在我们的世界出现,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吗?它所隐喻的诗歌写作,是否仅仅是主观情绪的发泄,它能够获得客观、真实的有效性吗?如果“我捕获的猎物并非我之所欲”,如此则一切尽成枉然。显然,这只狐狸,在黑暗中暴露了,但为了避免自说自话的癔症,它还需要另一种形式的客观化、物质化。最后一节的第一、二行对此做出了回应:
直到,带着一股突然的浓烈的狐狸热臭
它进入头脑的黑洞。
最后一节,是活物出现的第三个阶段:与人的世界发生关联,它开始客观化,被写在了纸上。如果说,第二到第五节,描写的是一直专注于“自我”的狐狸,它有着某种虚构性,是一只“想象”(“imagine”)的狐狸,那么到这里,它终于在“现实”中探出了自己,它与人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关系,与第一节呼应,这只狐狸终于在“此岸”、在现实场景中出现了!一个正反合辩证法式的生长。而这种呼应,休斯向我们强调,它来自气味和嗅觉。在第三节中,狐狸有了呼吸,于是走出黑森林有了转机和可能,因为呼吸意味着生命;而这一节,“狐狸热臭”,它所对应的是人的呼吸,这里强调的是,那只狐狸开始在现实中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于休斯,对于读者,这种变化当然是巨大的:它让我们从“普遍的枯索寂灭”走出来,就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可对“突然的浓烈的狐狸热臭”试做分析:
狐狸臭,并非取悦于人的香味,相反,它令人不适,甚至反感;但恰恰是这种味道,它既源自现实,又迥异于现实世界的平庸和寡淡,它意味着拒绝陈旧,意味着对日常世界的洗礼。它也告诉我们,这狐狸绝不同于日常的经验,而与诗歌有着严密的内在对应:“突然”,是诗歌的不期而遇、突如其来(“sudden”),就像《思想之狐》的翩然而至是因为“那晚突然有了写东西的想法”;“浓烈”,是诗歌意义的重量、强度和密度;“狐狸臭”,则是艺术的陌生化,意味着对认知水平的要求,它让日常发生裂变并获得新的意义,意味着震动!这种重获新生,它与前面第二节的“冰冷”的世界构成对比,这种狐狸臭是“热”(“hot”)的,它是温暖的,带来安慰。它克服着虚无,“进入头脑的黑洞”。这黑洞,原本是休斯的黑森林,是“普遍的枯索寂灭”,但是那活物爬进了休斯的头脑,“统摄”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因之,那个陷入“黑暗中更深”的世界,那只狐狸,在现实中有了自己的栖居之所——属于狐狸—休斯的“头脑的黑洞”,一个深而又深的,意味着无限可能的创造性的黑洞。
对于这首诗来说,最后两行完成了这个“辩证法”,它回到了最初的场景,一个充满禅意的结尾:
窗外依然没有星星;时钟嘀嗒,
纸上印满了文字。
还是那些事物:时钟,纸;还是那样的场景:夜晚,窗外漆黑一片,没有星星。现实场景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即使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曾经的那张白纸,现在印满了文字,一首完成的诗歌。“printed”,是狐狸最初的足迹,同时也是诗歌的完成:那只随时可能消失不见的狐狸,这首随时可能被“丢进废纸篓”的诗,它最终客观化、成立了。而作为全诗的结尾,它让所有的铺垫都与诗歌建立了联系,它让狐狸与诗的呼应关系更明晰了。其次是时钟,最开始的“孤寂的时钟”,这是隔绝、抽象描摹的词语;而此时,它从抽象变为具体,成了清脆的“嘀嗒”作响,“ticks”,这声音就像扣动扳机,将时钟代表的孤寂和死亡撕得粉碎。更为重要的是,全诗牵动的画面,易于被抽象化的视像,被无法复制、转瞬即逝的声音取代,这诗歌的狐狸,让抽象、概念化的时间具体化——不,是声音化,它甚至打破事物压迫性的象征,让世界回归本身,时钟不再意味着死亡,“嘀嗒”本身即是存在,即是意义。这种结尾可谓“渊默而雷声”。
也因此,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尾了。因为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其实就是生活本身。就像休斯的那个戏剧化的现实场景被窗户所分割,这一扇窗户,隔绝着屋里和屋外两个世界,两个世界不断推演、反转。窗外的世界,那个黑暗、冰天雪地、让人迷失、荆棘丛生的荒野,而窗户的里面,是一种属人的、艺术的、为我的存在,它是诗歌的领地——一个不竭的创造性的黑洞。窗户玻璃是透明的,它隔着里外两个巨大反差的世界,同时,它又是同一个世界。世界仍然如其所是。
小结
以上就是这只诗歌之狐的生长法则。那个物的世界的局限、精神的困境——“普遍的枯索寂灭”被克服,休斯走出了黑森林。同时,休斯童年的动物,从一开始就成了他思维机制的一部分,而二十多年后,它以全新的——诗歌的形式被保留下来,成为了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就像休斯说的,“它们已成为一种语言——一种象征性的语言,也是我一生的语言”(《巴黎评论:诗人访谈》)。至此,我们或许可再瞥一眼,这只“进入头脑的黑洞”,已“长大成人”的狐狸;这首在纸上“印满了文字”、没有被“丢进废纸篓”的诗歌,看看这诗歌的狐狸究竟是怎样的:
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如同一个小妖精,它诱惑、吸引着我们;它是隐秘的,灵动,变幻,难以把握,从来不是容易捕获、容易养活的,它可能随时消失不见,让我们的所有努力变得枉然;为了捕获它,你需要付出极艰辛的努力,需要极为专注,不畏缩,攻坚克难,进入当下,“用眼睛、耳朵、鼻子,味觉、触觉,整个身体倾注”(《诗的锻造》),同时,你又需要去除骄傲,打破成见,敞开自己,小心翼翼地听从它,让它自己现身、自我呈现;它不同于僵死的物的世界,也不是我们的主观创造,它是一个意向性的构成和相互成全,从想象到真实,介于物和我之间,有鼻子有眼有呼吸,有着自己的生命独立性,“被一个灵魂所统摄、推动”;它在现实“之外”,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但它又像与现实仅隔着窗户的一层透明玻璃,它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又处于同一个世界,最遥远又最切近;但它最终仍需客观化、物质化为一个纸上的世界,它需要找到文字、意象、节奏这些“活生生的零件”的对应法则,“如果任何一个零件是死的……那么这个生物将是残缺的,它的灵魂将是病态的”(《诗的锻造》)……
不过,这文字的物质属性一点都不能定义它,它一旦有效出现,就不会消失不见,就像但丁《神曲》中的超越与永恒的追寻,它是此岸的超越、现世的永恒、内在的安慰。就像这首《思想之狐》,“每当我读这首诗的时候,狐狸便会从黑暗中出现,走入我的脑海。我想即使我离世很久之后,只要这首诗还存在,每当有人读到它,狐狸便会从某处黑暗的所在浮现,向他们走去”。这只狐狸,“你看,我的狐狸在某些方面是比一只普通的狐狸更好的。它是永生的,不怕饥饿,也不怕猎犬。不管去哪里,它都会守在我的身边”(《诗的锻造》)。
我想,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诗歌,是一个新的物种;一旦诞生,它们就不会死去,不同于其他事物。
附:《思想之狐》
我想象这午夜的森林
有什么别的东西还在动
在这孤寂的时钟和这张
我以手指摩挲的白纸之外。
透过窗户我看不见星星
更近的什么东西
但没于黑暗中更深
正进入这孤寂
冰冷,细微,似那暗雪
一只狐狸的鼻子碰触着枝,叶;
两只眼睛转动了,一下
又一下,一下,又一下
把整齐的足迹印进雪里
在树林间,小心翼翼,一个瘸行的
影子在树桩边缓缓移动,
空荡荡的身体将大胆地
穿过开阔地,一只眼睛,
一种扩张着、加深着的绿,
闪亮地,全神贯注地,
干着自己的事情。
直到,带着一股突然的浓烈的狐狸热臭
它进入头脑的黑洞。
窗外依然没有星星;时钟嘀嗒,
纸上印满了文字。
(休斯作,综合曾静等多个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