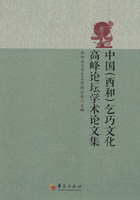
第17章 秦风余响:西和七夕风俗的复兴
刘锡诚
一、西和七夕风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2006年5月20日,我国政府颁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把“七夕节”(乞巧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六个传统节日和“农历二十四节气”一道纳入国家保护名录。但“七夕节”这个项目并没有确定具体的保护单位,因为全国30个省市,没有一家主动申报,只好临时动议把国家文化部搬出来作为保护单位。两年后的2008年7月6日,中央政府又颁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第一批名录的扩展名录”里,把甘肃省西和县确立为“七夕节”的唯一保护单位。大家知道,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中国文化史著作里,传统节日是从来没有地位的。即使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里的“礼俗”这一小节里,也没有对传统节日着墨,也就是说作者并不把传统节日(或曰民俗节日)算作文化。民俗节日,只在地方志或随笔等杂著里简略地被记载着。即使20世纪40年代接受了外国的社会学、文化学学说的中国文化学者们,也很少有人在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上有什么新的作为。1931年11月14日,费孝通翻译的马林诺夫斯基著《文化论》出版时,他把老师吴文藻撰写的《论文化表格》作为马氏大著的“附录”放在了全书的末尾,实际上是想对马氏这一名著作一补充。但,即使在这篇作为他们这一文化学派的纲领性大作里,吴文藻也只是在阐释“文化三因子、八方面”的理论框架时,在“实地调查报告的体裁”这一小节里写上了“节序”二个字[1]。21世纪第一个十年,把“七夕节”(西和)这样的节候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一点不要小看。
在西和县把“乞巧活动”向文化部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前后,西和的包红梅副县长和县文联的同行们来京,向我介绍了当地的传统乞巧活动的情况,并邀请我前去考察观摩,因年老体弱未能成行。未久,西北师大的赵逵夫先生把他的先父赵子贤先生身后留下的一部20世纪30年代在西和口头流传的《西和乞巧歌》记录手稿交我,嘱我为之写序。由于这样的一个机缘,我对西和的乞巧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因而获取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对其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我把这些粗浅的看法和思考大胆地写在了《序言》里:
作为编者,他(赵子贤)对这部《乞巧歌》所录的节令仪式民歌,以及这些作品所记述和反映的当地流传既久的七夕节候的乞巧风俗与社会情状,特别是封建礼教和社会不公给妇女带来的悲苦命运和心灵创伤,充满了深切的同情、甚至愤懑;对这些民间作品的文化史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把这些隐没于漾水和西汉水流域草野之中而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民歌,称为“国风”。何以称之为“国风”?他在《题记》中写道:“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响正回萦。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水旱兵荒多苦难,节候耕播富风情。真诗自古随风没,悠远江河此一罂。”也就是说,他把西和一带的这些传统的乞巧歌,看作是《诗经》中著录的“秦风”的“余响”。
《诗经》所采集的“十五国风”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在中国的北部,稍入南方的,只有《周南》《召南》和《陈风》(朱希祖《罗香林〈粤东之风〉序》);北部的《秦风》选录了十首之多,应该主要是周室东迁、秦文公“居西垂宫”时代的作品,其中的《无衣》《黄鸟》《蒹葭》等歌诗,颇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尤其是那首“表现了人民慷慨从军,团结御侮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华文学史·古代文学编》)的《无衣》。但也有学者认为,《秦风》之诗,大体都是秦人思贤、访贤、得贤、弃贤之作,而并非都是真正从民间采撷而来的民众作品。战国时代,屈原写《九歌》,后人辑为《楚辞》,主要辑录了以楚地为中心的江南的“风诗”,而不涉及北方。到了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诗,所及地区,最北方包括了燕、代(今之张家口辖蔚县一带)、雁门、云中,西北到陇西,而陇西地区,也大体就是《诗经》的“秦风”之地,即天水一带,至于建立古仇池国的氐人的发迹之地、也是周秦中原文化与氐戎(羌)文化交汇之地的陇南及西和一带的民间歌诗,则少见涉及;且汉武帝采诗所得乐府歌诗,已佚亡不存。宋郭茂倩所辑《乐府诗集》,在《横吹曲辞》里收入了不少取材于陇头、陇水、陇坂的歌诗之作,细细读来,也多是随军文人或后世歌者歌咏或追怀中央王朝与氐戎战事中的征伐勤劳之作,而看不出有多少来自陇南一带真正的“风诗”。这样一来,赵子贤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所编订的《西和乞巧歌》把采集足迹扩展到了前贤所未至的、地处漾水和西汉水流域的西和,第一次记录了农村姑娘们所唱的歌诗,也就弥补了自《诗经》《乐府诗集》以来陇南一带的民间风诗在诗歌史和民间文学史上的阙位,因此可以说功莫大矣。
“乞巧歌”具有两重意义:首先,它是社会历史和群体民俗的重要载体;其次,它是依附于特定的节候——七夕——而产生和咏唱的民众口传文学作品。由于地域和历史等的特定原因,这些歌诗(与《诗经》和《乐府诗集》里的作品一样,大半是可以演唱而不是徒歌)的流传地西和,在周秦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被逐渐边缘化了。边缘化的好处是,在农耕文明和家族人伦社会条件下的七夕风俗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歌诗,尽管是以口耳相传这种易变的方式世代传递,其嬗递变异的速度相对较慢一些,以相对完整的形态被保留下来,传承下来。而子贤先生所记录编订的这本《西和乞巧歌》中的歌诗文本,就是“千年乞巧千年唱”,流传至20世纪上半叶的歌诗形态。正如子贤先生说的:“西和如此普遍、隆重、持久的乞巧活动其他地方没有,这给女孩子一个走出闺门、接触社会的机会,在古代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表现,在今天是一种对社会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方式,既反映老百姓之心声,也是存史,同《诗经》中的诗有同样的价值。”从这一情况来说,西和的七夕乞巧风俗历史久远,风格与形态独特,乞巧歌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妇女的地位和命运,认识农耕文明和家族人伦社会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以及追溯七夕节和乞巧歌的源流和意涵,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当然,包括乞巧歌在内的所有民间文学形式是流动不居的,不会停止在一个时间点上。在历史的匆匆步履中,民间文学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仅内容,也包括形式。属于时政歌谣的作品,大都随着时代的变迁,往往成为绝唱,除了研究者的需要而外,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而那些表现民俗生活和民众心态与情感的作品,则永远伴随着历史和人们走向未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乞巧歌的嬗变,与民间文学的其他体裁和形式一样,是遵循着文化进化规律渐进的,而并不是按照“那些自命为革命家的人”(列宁《共青团的任务》)的指令和路线图发展前进的。关于这一点认识,只要把赵子贤版的西和乞巧歌,与当下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新搜集采录的乞巧歌加以粗略地对照研究,就可以相信是大致不错的[2]。
时光进入了21世纪,具体地说,2007年,西和县为了把西和的乞巧风俗申报国家名录作准备,由西和一中的师生们组成的乞巧文化课题组,对西和的乞巧活动以及乞巧歌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录(录像记录和文字记录),并出版了他们记录的《西和乞巧风俗图录》和《西和民间乞巧唱词集》,向世人贡献出了西和县的地域里民众在七夕节候里的乞巧活动和乞巧歌在21世纪初的活态样相和文本。这两本书,无论是作为项目申报和立项的依据,还是作为七夕节期间的乞巧活动和乞巧歌研究的对象资料,都是极其必要和可贵的。笔者没有见到《图录》,但有幸读到了《西和乞巧歌》,好在乞巧歌文本,无论就其所附丽的乞巧风俗与活动而言,还是就其唱词文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而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西和地区的七夕节候的全貌。这些当今时代记录的乞巧歌文本,反映了或囊括了当地七夕节期间的全套乞巧活动,从七月初一把巧娘娘请进屋内上桌供奉起,到七月七日之夜的最后一个程序“照花瓣”(卜巧)结束,送走巧娘娘止,这七个昼夜里“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六个环节(程序)的全部仪式歌,为我们提供了与1930年代赵子贤记录的《西和乞巧歌》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昔日的乞巧活动及唱乞巧歌的情景及其意义,如赵子贤先生所说的:“西和如此普遍、隆重、持久的乞巧活动其他地方没有,这给女孩子一个走出闺门、接触社会的机会,在古代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表现,在今天是一种对社会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方式,既反映老百姓之心声,也是存史,同《诗经》中的诗有同样的价值。”而如今的唱巧活动,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我们看到,在妇女们以全身心的情感和精神吟唱的乞巧歌中,依然让我们感受到妇女对自身命运的悲悯呼唤的延伸。一如《西和民间乞巧唱词集》序言作者宁世忠先生所说的:“在这漫长的‘娱巧’过程中,妇女们自己的创作都大量涌现出来了。除了口耳相传的唱词,她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唱起自己的追求与愿望、家庭、困惑与酸楚、牢骚与不满,唱着唱着,心情激动了,泪水滴下来了,以至泣不成声了,甚或相抱痛哭了。我以为这才是乞巧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3]诚然,在乞巧节期间,参与乞巧唱巧的妇女(早前,据记载,参加乞巧唱巧的,一般是未婚的青年女子,而如今,已婚的、阅尽沧桑的青年妇女也参加进来了),她们除了一遍一遍地反复吟唱那些传统的乞巧歌之外,也根据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即席编唱新的作品,不过最后仍然是把老歌的传统结构,即把“巧娘娘,下云端,我把巧娘娘请下凡!”(或略加修改为“巧娘娘,驾云的,我把巧娘娘请下凡!”)这样的衬词唱进去。
我们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一味地崇尚古老的、不变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不过是一种虚拟的想象罢了),但由于地理和人文两方面的原因,如生存环境的封闭性和社会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西和的七夕节节期中所固有的古老的乞巧风俗,比较完整地被保留下来,且流传至今,实在是难得的一个文化个案[4]。尽管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从文学上说,乞巧节所演唱的乞巧歌也许比一般的山歌、花儿显得略逊一筹,但就其所反映的歌者主体的情绪、愿望和憧憬,以及中国农业社会的社会情状而言,它又是颇为精彩、独到而深刻的,不愧是“秦风的余响”。西和的“七夕风俗”被列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这一事实说明,溯源于周秦——中原文化传统的以乞巧为核心的七夕民俗活动,虽然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历史风雨的洗礼,在当今之世,仍然在其“原生地”的土壤上葆有异常的生命力,不仅被继承着,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很快复兴起来。
笔者没有掌握21世纪非遗保护运动中有关七夕节现状的全面调查资料和数据,只能像许多民俗学家那样,根据已有的书面资料、尤其是历史上的记载进行立论,尽管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或者说有缺陷的,但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有记载说,七夕节从清代中期或晚期起就逐渐开始衰微或没落了。这个结论已被有些学者和著作所认可和采用[5]。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编刻的广东省《澄海县志》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七月)七日,旧俗妇女陈瓜果‘乞巧’,今无。”[6]清光绪四年(1878)浙江省《浦江县志》:“至‘乞巧’之说,或鲜有知。”[7]到民国时期,七夕活动逐渐衰微或消失的报道屡见于书籍和报刊。民国二十年山东省《临朐续志》:“七日,旧传是夕妇女陈瓜果于庭‘乞巧’,然今已成往迹,无复有佞织女者矣。”[8]1931年,汕头林培庐编《民俗周刊》刊载姚世兰《七夕谈》报道说:“我们潮州民间对于(七夕乞巧)这种习俗,虽然也曾有过,但是久矣哉不见有人举行。据龚志清《潮州四时竹枝词?咏七夕》说:‘乞巧天孙俗久无!不须瓜果设庭隅;他年莫被聪明误,沿海生涯口易糊。’……现在我们民间关于乞巧这事,唯有存留一种传说而已。……就是每逢七夕来临,一般闺秀便集姊妹行七人,组织一个乞巧会。她们除供些瓜果之外,并共同取苎麻织成七尺来长的布一幅(须在这日织完才算),然后各剪一尺遮于脸蛋儿上,朝着牛女双星瞧去,若能看见空中任何景象,便据这景象来猜卜终身的好歹。这一来,好的自然暗心喜欢,歹的就要抑郁于怀!新人物说:庸人自扰,委实活该!”[9]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些材料,说明至少晚清到民国期间,七夕的乞巧活动已经不同程度地衰微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来,七夕的风俗活动和牛郎织女传说的流传情况,民俗学家们的著作,笔者查阅了陶立璠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俗大系》(31卷),发现绝大多数(少数例外)省卷本,都是大而化之地征引或重复旧时地方志里的记载,基本上没有自己调查的纪实材料,缺乏历史主义的态度。从这些专业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七夕节的历史上和今天的翔实的存废情况,只有5种有所交代。杨景震主编《陕西民俗》卷中记载:“唐以后各代,民间的乞巧活动,一直盛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祭奠织女与牛郎的活动基本消失,但乞巧活动,仍然在各地农村中流行。”[10]刘永立主编《河南民俗》卷中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七月七的乞巧习俗在乡间仍可见到,但大多已是年轻人的嬉戏逗乐,其情其景其神秘成分已甚淡漠。”[11]余悦主编《江西民俗》卷:“现此俗已废,但‘七月七做果吃’之俗仍然在农村盛行。”[12]尚洁主编《天津民俗》卷:“此俗现已绝迹。”[13]邢植朝、詹贤武主编《海南民俗》卷:“如今这种习俗几乎已经绝迹。”[14]这就是说,除了这5种以省卷的名义编纂的民俗志著作里,以略有差异的文字说“已经绝迹”了以外,其他26种基本上都是用“旧时”一词来表达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非遗”时代君临之前,七夕节候及其乞巧风俗已经基本衰微、或者绝迹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和县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或复兴起来传统的七夕节候的乞巧风俗,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记下一笔!
二、乞巧节是女儿节——少女节
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人,适应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小农耕稼生产方式,以及自给自足的劳动者的精神诉求,在早期的原始农耕时期就创造了和形成了许多与时序相适应的节候,这些节候在以后的农业社会中得以继续传承和逐渐完善,“七夕”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国传统的节候之一,“七夕”从雏形到形成迄今已经两三千年了。在起源问题上,学界持汉唐说者有之,持战国周秦说者亦有之[15],持楚文化说者有之,持周秦文化说者亦有之,至今并没有统一的看法。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被重视,起源问题与起源地问题相纠缠的倾向不断升温,讨论还在继续之中。但自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末至秦始皇三十年间竹简《日书》甲种155简和3简关于牵牛织女的情节文字发表以来,应该说,战国周秦说的分量逐渐占了优势。而西和、礼县传承至今的七夕风俗,特别是“请巧娘娘”的仪式以及作为仪式之组成部分在巧娘娘面前所唱诵的乞巧歌,为战国周秦说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再从流传地区来说。“七夕”的流传非常普遍,几乎覆盖了全国各地,“在中国境土之内,几于无处不传述及知闻之了”。笔者查阅21世纪初编纂出版的31卷本的《中国民俗大系》,发现没有乞巧节活动记录的卷本,仅有宁夏等少数几个民族聚居的省区。可疑的是,在《中国民俗大系·甘肃卷》里,如今完整流传着的西和、礼县的七夕风俗,竟付诸阙如。于是,在赵子贤搜集记录的《西和乞巧歌》(1936)和当今搜集记录的《西和民间乞巧唱词集》(2007)之间,横亘着的是70年的空白。这个疑问还有待当地专家们的释疑解惑。
20世纪20年代,钟敬文说:“中国许多重要的节候和风俗,多发源于或附丽着颇有意味的神话和传说。最著者,如元正的贴桃符,元宵的迎紫姑,端午的悬钟馗像,挂艾剑,饮雄黄酒之类,不一而足。七夕呢,既为重要的节候,并有多般的风俗,而其和这二者——节候和风俗——有甚大的连环关系的,是一个有力的传说——织女会牛郎的故事!”“说到这个传说之所以形成,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原因,无疑是由于两种星的名字,易于教人把它们当做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看待。从一种怪富于给人附益性的实物的名称,把四周何种适应于配合的材料而充益之,终局结构成了一篇有意义有系统的神话故事。……自此(指《续齐谐记》)以后,这个故事,便很顺利地向着空间及时间两面展延流泻。”[16]
30年代,欧阳云飞说:“这个故事之所以形成,最大的原因是由于那两个易于教人把它们当做神话中的‘人物’看待的星名,民俗学上叫做‘民间的语源解说’(folketymology)。……牛郎织女的名见诸于最早的是诗经,小雅大东章云‘睕彼牵牛,不以服箱’;又云‘跂彼织女,终日七襄’,是周以前就有这两个星名的酝酿了,不过它是只具有一个雏形而已,还没有指出他们是神仙,也没有说出他们是否有夫妻关系,只是一些诗人随意拈来的想象语罢了。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就渐渐把他形出人物来,天官书云‘织女是天地外孙’,然而也只是记到织女而已。……直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出世,……民间对于这故事就当做千真万确地看待,于是就演出结綵缕、穿七孔针、陈瓜果、曝盎水、献糕饼、剪彩、持热豆相饷……等的迷信举动来了。”[17]
40年代,常任侠说:“牛郎与织女的神话……大概早产生于中国原始的耕稼时代,因为约当西历纪元前十一二世纪的时候,中国周代的民歌中,已经唱着牵牛织女双星的名字。……牛女的神话,也许在这时更加发育得美丽起来,而且成为定型化了。到汉代这凄艳的故事,更常为诗人咏唱着。……七夕又是宫廷贵族所喜好的节令。《西京杂记》说:‘汉綵女尝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穿针即是七夕的游戏之一。《舆地记》说:‘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天宝遗事》说:‘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清华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七夕的七巧与乞福,也成为民间普遍的风俗。《风土记》说:‘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儿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又《四民月令》说:‘七月七,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曜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乞愿,三年乃得。’”[18]
把作为节候的“七夕”的起源,追溯于牛郎织女传说的影响和延伸,而牛郎织女传说,又来源于人们对牵牛星和织女星两星的崇拜。这是20世纪前半叶学界比较普遍的意见。两星的隔河相望而不能相见的天文布局引发了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拟物化”思维,牛郎织女悲剧故事顺势而生,同时也激发了与“七夕”相关的种种习俗的遐想与建构,以及对妇女命运的思考。从“七夕”节候与风俗的起源,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在我国,大凡一个节日的形成和持续,总离不开相关的风俗和传说为其基础或支撑物,没有相关的风俗和传说,节日的持续就难以为继。换言之,相关的风俗和传说,乃是节日之成为节日的最基本的条件和支撑物。作为七夕节这一节候的基础和支撑物的,乃是包括牛郎织女传说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风俗,而这一风俗系统,包括神灵崇拜(先是织女星,继而是被称为天孙的神人织女),逐渐演变为一个悲剧性的人间的情爱故事。
笔者要强调指出的是,与其他的传统节候,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是全民参与不同,七夕节主要是未出嫁的少女这一特殊人群的节日,故而民间也俗称乞巧节、女儿节;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逐渐把少妇这一群体也增加进来了,故而有的地方又称其为女人节。西和的乞巧节及其乞巧活动,应该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有不少40岁以上的少妇参与其中,由于她们的阅历多,体验深,所以她们所唱的乞巧歌,其内容所涉及的社会情状和人生图景,显然要比阅历较浅而纯情的少女们更为广阔和深沉,甚至流露出某些忧郁、悲戚的人生情怀。赵子贤的女儿赵兰馥所撰《〈乞巧歌〉与我所经历的乞巧节》里,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所述乞巧歌所唱乞巧歌的心理感受,可谓鞭辟入里:
《乞巧歌》中有不少是说男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自己将来会遇上怎么样的人,那时并不去想,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有一首说:“大姐娃成给南门下,南门下他是有的家。房上瓦的筒筒瓦,槽上绑的枣红马。二姐娃成给东门下,一个铁印升子大。不是骑马当官的,是个抡锤打铁的。”一个巷道里年年一起乞巧年龄相近的,相互间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大体上在同一年龄层次上一起玩得好的,有的就按年龄、月份大小称作“大姐”、“二姐”等,实质上形成了结拜姊妹的关系。从十二三到十六七,年年一起乞巧,一两年、两三年中先后嫁人,其命运又各不相同,婚后或为自己的家庭、生存而挣扎,或由于婚姻不满意而心情不畅,或受到公婆、丈夫的虐待;即使家庭情况好的,也受到一些礼教的束缚,再不能像当姑娘时一样自由。青春时代的快乐已一去不复返了。这首歌实际上表现出乞巧的小姑娘,由已经出嫁的大姐姐们的今天,想到了自己的明天,表现出来对青春时代的无限珍惜与留恋。这首歌流传较广,各地虽有些不同,但表现的心情是一样的。之所以流传广,和其中包含的难以抑制的情绪的反映有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武都县妇联工作时还写出一些,在妇女工作中作为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实例来讲。像《太阳出来一盆火》中说的,媳妇子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担水、砍柴、喂猪、做饭,没有人帮助,“抱上湿柴去烧锅。一口两口吹不着,阿家骂我像猪猡。流着眼泪吹着了,头发眉毛燎着了。男人过来脸上打,阿公过来拔头发。小叔子过来揪耳朵,阿家过来身上掐。”确实连奴才都不如。这媳妇偶然碰到娘家哥哥,讲了自己的遭遇,她哥哥只是让她忍着,等到婆婆死了,自己也当阿家。按这种旧风俗当了阿家后再去欺负、折磨自己的儿媳妇,这一代一代互相压迫,不是妇女自己压迫、折磨自己吗?[19]
读着西和同行们记录下来的乞巧歌,读着赵兰馥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不禁令我想起了国内外许多作家、学者和哲人不约而同指出的忧郁是民歌的基本格调这一至理名言,这种见解,在西和的乞巧歌里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三、“巧”与“乞巧”
作为七夕节候整套风俗系统之核心的核心,不是别的,而是“乞巧”。妇女希冀从“乞巧”的习俗中获得“巧”,“巧”是她们对人生的憧憬,“巧”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巧”是她们改变悲苦命运的法宝。
有必要对“乞巧”稍作一点分析。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整套的礼教和伦理压在妇女头上,譬如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以及“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等戒律,就规定了妇女的卑下地位,要求妇女要“夫唱妇随”,否定妇女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譬如世俗生活的磨难,日复一日地摧毁了女性的创造力和柔美天性,她们在默默无闻的劳苦中变成了黄脸婆,她们一个个蜕变成了谁都可以使唤的工具。于是,“巧”和“乞巧”便成了妇女要改变自身卑下地位、从被压榨的处境中突围的一种现实的路径和高尚的追求。“巧妇”也就成了漫长的耕稼社会里民间对有为女性的赞赏和评价。“巧娘娘”成为所有妇女心中圣洁的神灵和翘首企望的楷模。她们一遍一遍地吟唱着“我请巧娘娘下凡“,她们说:“天荒荒地皇皇,我请巧娘娘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先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汉源镇黄磨村的代玉翠唱道:“七月初七天刚亮,水泉门上跳着唱。今天她是喜庆人,巧娘叫我剪花样。进水宫来照一眼,样样本事教得全。明千针仓仓穿,绣出的花儿突噜噜颤。巧手学会裁衣服,裁缝裁的端又端。”“绣”的主题特别多,什么《绣村庄》啦,《绣扇子》啦,《十针绣》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女孩儿们乞求巧手的愿望。她们不仅为自己乞求学得巧娘娘的“七十二样好手段”,向巧娘娘乞求个人幸福家庭幸福,而且乞求她们的孩子也能成为“巧子”。何为“巧子”?研究者王笠衫注意到了乞巧者的这种心愿,写道:“七月七日生的女孩,大率都叫巧子,所以到了七月七,想起女儿要抓周了。”[20]有一首扬州的乞巧歌弥补了西和乞巧歌的缺憾:“七月七,看牵牛,我家巧子要抓周,三十子是个佛睁眼,还要到地藏庵里上灯油。”
“七夕“的唱巧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年轻的女儿们避开男人而委婉表达这种愿望和追求的时机,她们在唱巧的时候,暂时忘掉了她们悲苦的命运和不幸的境遇,歌声成为她们心灵之声的寄托。她们咏唱青蛇白蛇也好,咏唱梁山伯祝英台也好,咏唱孟姜女送寒衣也好,咏唱七仙女下凡也好,咏唱王宝钗也好,咏唱莫愁也好,她们在歌唱中给予被咏唱的人物的悲剧命运以深切的同情,一波一波不停地捕捉和寻找那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愫。尽管如此,却也掩饰不住美好愿望背后的丝丝悲凉,正如咏唱牛郎织女的悲剧故事的歌中所说:“朝朝暮暮一朵云,岁月凄凉在天空。”
2013年7月31日草成于北京
此文为“2013中国(西和)乞巧文化高峰论坛”作
(作者为国家非遗保护委员会委员、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注释:
[1]“文革”后的80年代中期,1987年,笔者把自己从香港得来的费孝通译、马林诺斯基著《文化论》一书交给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作为我所策划设计的《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的第一种重印出版。当时,迫于学术界和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我把原书中作为《附录》的吴文藻撰《社会学丛刊总序》和《论文化表格》撕下来,只印了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书稿。现在借这个机会,把30年前这段往事记在这里,以求还原历史。
[2]拙文《西和乞巧歌·序》,先后发表于《文艺报》2011年7月20日,题为《秦风遗珠足珍贵》;《甘肃文艺》2011年第1期(2月25日),题为《弥补陇南风诗阙位的重要文献——〈西和乞巧歌〉序》。该书由香港银河出版社于2010年4月出版。
[3]宁世忠:《西和民间乞巧唱词集·序》,第2页,内部资料。
[4]参阅柯杨:《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关于甘肃省西、礼两县传统乞巧节的调查》,见《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8月。
[5]张勃、荣新:《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就采用了这种说法,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济南。
[6]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册)第77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7]同上书,《西南卷》第90页。
[8]同上书,《华东卷》(上册)第204页。笔者对这则记录有些怀疑。临朐县是我的故乡昌乐县的邻县,儿时在家乡,每逢七夕,姐妹们还有在院子里陈瓜果乞巧祭祀、穿针、在瓜架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私房话之类的乞巧活动,不过,乞巧活动和祭祀仪式与志书中的记载相比,比较简单而已。
[9]姚世兰:《七夕谈》,林培庐主编《民俗周刊》第1—20期之《民俗周刊汇刊》,第87—88页,1931年11月1日,汕头。
[10]杨景震主编:《中国民俗大系·陕西卷》,第21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11]刘永立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河南卷》,第27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
[12]余悦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江西卷》,第20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
[13]尚洁主编:《中国民俗大系·天津卷》,第18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
[14]邢植朝、詹贤武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海南卷》,第12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5]持战国周秦说的,如柯杨和赵逵夫。柯杨在前引《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关于甘肃省西、礼两县传统乞巧节的调查》里说:“当地的乞巧节,乃是古老的秦文化在民间节日习俗中的传承。”(《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第37页,学苑出版社2007年8月。)赵逵夫在《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汉水、天汉、天水——织女传说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等文章里说:“周人先是逐步南移,至长武一带又东南移。秦人由西汉水上游渐渐东移,至原来周人所居之地。周秦居地的重合也必然形成文化的融合。这应是牵牛、织女故事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来在战国之时牵牛娶织女为妻和以后二人分离的传说已形成。”
[16]钟敬文:《七夕风俗考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12期合刊,1928年1月,转引自施爱东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第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17]欧阳云飞:《牛郎织女故事之演变》,上海:《逸经》文史半月刊第35期,1937年8月。
[18]常任侠《牛郎织女神话后记》,见《民俗艺术考古论集》,第68—71页,正中书局1943年,重庆。
[19]赵兰馥:《〈乞巧歌〉与我所经历的乞巧节》,见赵子贤编《西和乞巧歌》第173—174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12年。
[20]王笠衫:《扬州奶奶经》,娄子匡主编《孟姜女》第1卷第5期,1937年6月1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