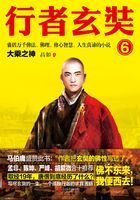
第9章 思乡是一种病
乌波苏特完成了向导的任务,他不能离开他的国家,因此只能与玄奘分手,回大都城去了。
玄奘独自一人沿着海岸线往南走,在他的身边,是一大片茂密的阿输伽树,还有阔边剑麻、荨麻和扇叶棕榈组成的森林,红羽鹭群沿着海滩的边缘缓缓飞行,成百上千双粉红色的翅膀层层叠叠地连成一片,看上去蔚为壮观……
在羯陵迦国,玄奘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向一位精通因明的婆罗门学习《集量论》。[1]
接着,他又折向西北,来到位于内陆的南憍萨罗,这个处于印度腹部地带的国家以龙树菩萨的故居而闻名。[2]
对玄奘来说,龙树这个名字实在是太熟悉了!《入楞伽经》第八卷中记载:“大慧菩萨白佛言:佛灭度后,是法何人受持?佛以偈答曰:于我灭度后,南天竺大国,有大德比丘名龙树菩萨,住欢喜地,为人说法,能破有无见,往生安养国。”
龙树是大乘中观学派的创始人,确切地说,也是整个大乘佛教的创始人,是佛陀之后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论师。
崇敬佛法的南憍萨罗国国王给玄奘讲述了许多有关龙树的故事。他虽是个国王,但同南印度地区的其他龙树信徒一样,习惯于把龙树看作是一个拥有大神通的人。
而玄奘却从这些故事中,感受到了大乘佛教传播之初的艰难。
龙树之前,大乘佛教虽然已经萌芽,却一直处于隐而不发的阶段,无法为广大教徒接受和理解。到了龙树时期,他阐发大乘义理,著书立说。其玄奥的思想、独特的文风,与原有的佛教思想迥然有别,因而引起了旧式佛教僧侣的怀疑。
许多佛教徒对龙树的学说提出质疑,认为他所倡导的教义是“魔说”,不是“佛说”,于是相互间争论起来。
这种争论延续了很久,甚至影响到了中国佛教界。
那个时候,北印度早已是部派佛教的天下,南印度则被各种外道占据了优势,并且得到了许多皇家贵族的支持。
龙树是南印度人,他的大乘思想被部派学者看作是异端学说,难以相容,这迫使他将自己的学说向南方发展。一方面可以避开各部派教徒的攻击,另一方面又可扩大佛法的传播区域。他是个极聪明的学者,在传教过程中感化了引正王,于是,大乘佛教首先在南印度得到弘扬并盛行起来,龙树本人也得到了南印度人民的普遍敬信。直到龙树去世百年之后,南印度诸国仍为他立庙供奉,礼仪之重,香火之盛,不在佛陀之下。[3]
在憍萨罗国西南方向三百余里,有一座黑峰山,山上有一座寺院,依山势而建,十分宏伟。
寺院每阁分作五层,每层各有四院,皆铸纯金佛像,饰以重宝。设计之巧妙,工艺之精微,当得起“巧夺天工”这四个字。
玄奘来此寺挂单时,寺中僧侣告诉他,这所寺院便是当年的憍萨罗国引正王为龙树菩萨所建,龙树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
龙树精于药术,擅长养生长寿之学。传说他寿高数百,依然神清气朗,容貌不衰。
他将长寿之术教给了引正王,这件事引起了太子的焦虑,于是太子向母亲诉苦道:“我的父王已年过百岁,仍然身强体健,不见衰容。这样下去,我何时才能嗣位为王?”
王后回答:“以现在观之,确实是漫漫无期了。这一切都是龙树的福力所致。如果龙树死了,你父王的寿命只怕也会尽了。龙树是佛教名僧,常有慈悲利物之怀,素禀布施救度之志,视财物性命犹如粪土。你可去求他,让他将头颅布施与你。只有如此,你才能如愿登基。”
太子受王后怂恿,便来到龙树的寺院,对他说:“我今日与母亲谈论佛法,说到佛教的布施。以我看,佛教虽有能施之士,但身家性命向来为人所贵重,不会有愿意舍弃性命布施与他人者。母亲不同意我的看法,她说在从前的时候,十方诸佛、三世如来修习佛道,为救度众生,或投崖饲虎,或割肉救鸽,如是之类不可胜数。母亲还说,若以世人而论,龙树菩萨您就怀有这种高大的志向。我有一件事,需要以人头为用,求了几年也没人肯施舍于我。想要行暴杀戮,又怕残害无辜,招致恶名,获罪不浅。听了母亲的话,我便想到了您。您修习菩萨圣道,视身命如浮云、视肉身为朽木。远期佛果,有大布施之心。故而敢请您行昔日诸佛之所行,以项上人头布施与我。”
龙树听完,知道太子是来要自己的命的,便回答道:“你说得不错,我求佛道圣果,视身命如泡影虚云,没有不可施与人者。只有一事不知如何是好,我一旦死了,你的父王也将命终。太子您看怎么办呢?”
王子缄口不答。
龙树等了好久,见太子始终不做反应,于是长叹一声,顺手拿起一片干茅草叶子,向颈中轻轻一割。草叶锋利如剑,龙树菩萨立即身首异处。
引正王听说龙树自杀的消息,大惊失色,随即命终。太子如愿以偿,登基为王了。
这仅是有关龙树之死的一个传说。除此之外,玄奘还听到过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他是在部派学者及婆罗门信徒的重重逼迫下,自行坐化的。
可见龙树的一生充满艰辛与波折,他的思想传播与各种王族势力不断产生冲突,与民间及学界的其他思潮更是格格不入。这种冲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达到以性命相搏的地步。龙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弘扬和发展了他的大乘中观理论,并推动了大乘佛教的发展。
至此,玄奘已经完全进入了南印度境内,当地人讲达罗毗荼语系的泰卢固语,其语音语调与中印度、东印度均有很大的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人才是印度半岛的真正土著。至于北印度、中印度的那些人,都是不同时期的入侵者的后代。
通过这些年来不断的学习、游历,与各地长者谈古论今,所得到的零零星星的片断组合在一起,使得玄奘对印度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多多少少有了些概念——
印度的古代史始终是次大陆北部的发展史,特别是在恒河两岸,摩揭陀的国土上,更是充满厚重的历史感。
难陀王朝、孔雀王朝、巽迦王朝、笈多王朝均发祥于恒河两岸,在那些古典时代里,摩揭陀国的故都华氏城一直被他们视作宇宙的中心。
只有贵霜帝国是个例外,它的政治中心更加靠近西部,在印度河一带。
相比较而言,南印度的历史一直则较为平静,这里是土著人的天下,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自成体系,与中、北印度大不相同。
而且,与精于算计、戒备心高的北印度人相比,南印度人也显得悠闲质朴、性格憨直。
就连这里的佛经,也是由当地文字写成,基本上以故事为主,且语言通俗,读起来十分稚朴古拙。
不过,玄奘并没有在这个群山环绕、拥有近万僧人的佛教国家停留太久,而是折向东南,穿过密密的丛林,继续前行。
雨季就在这个旅途中如期而至,天空好像漏了一般,倾盆大雨将整个东南印度变成了一片泽国。
这一次,玄奘没有停下脚步,他头戴斗笠,身背竹箧,艰难穿行于大沼泽之中。
茫茫的雨幕遮住了蓝天,挡住了群山,只能隐约看到远处丛林淡淡的影子,如同汉地的泼墨山水画。玄奘拨开茂密的芦苇和杂草,穿过高低错落摇曳不定的灌木、丛林,在风雨中走了一程又一程……
偶尔,他会看到一些湿滑的长满花花绿绿斑纹的生灵,比如蟾蜍、青蛙和水蛇,以及各种线虫。它们生长于大沼泽中,毫不怕人,悠闲地在这路人身边游来跳去,有的甚至蹦到了他的身上。
还有巨大的独角犀牛,这些家伙的体形仅次于大象,皮肤坚硬无比,深灰带紫,肩胛、颈下及四肢关节处有宽大的褶缝,皮上还有许多圆钉头似的小鼓包,这使得它们看上去酷似穿了铠甲。
玄奘知道,这种庞然大物虽然以草、芦苇和细树枝为食,却远不及大象温顺,稍不留神就会主动攻击人。因而他显得格外谨慎,遇到了就停下来,等对方离开后再继续前行。
偏偏这东西还贪玩好耍,有时跳到泥浆里,弄自己一身泥,并且乐此不疲。等它玩够了离开时,天往往已经黑了。
雨季里极少有星月,夜幕降临之时,便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夜黑如墨,暴雨如注,怀里的点火之物全部湿透,他只能蜷缩在灌木丛下勉强歇息,手捏佛珠,静静地等待天亮……
这片方圆不过三四里地的沼泽,玄奘竟在里面足足转了七八天。
在沼泽的边缘地带,他看到一头惊慌失措的鹿被几头模样丑陋的鬣狗逼进了烂泥塘,陷进了泥淖之中。
玄奘觉得奇怪,鬣狗不是只吃腐肉的吗?居然也会打猎?
眼看那头鹿在泥沼之中挣扎不休,越陷越深,玄奘思索片刻,砍了些灌木绑成木排,小心地放在泥塘里,慢慢地靠近那头鹿。
那鹿看到木排就不再挣扎,也不再动,似乎认命了。就在玄奘替它着急的时候,就见它猛然爆发,纵身一跳,便上了木排,再一跳就到了硬地上,瞅了玄奘一眼就跑开了。
真是个聪明的小家伙!玄奘的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托了托身后的行囊,继续向着雨水茂密的地方走去。
一个月后,精疲力竭的玄奘终于来到了印度东海岸的驮那羯磔迦国。[4]
这里是因明学大家陈那的故居,伽蓝倒是不少,可惜大多已经荒废,尚存者只余二十多所,僧徒三千余人,多数崇信龙树的中观宗。国中有一座石头砌成的窣堵波,是陈那论师作《因明论》《理门论》之处。
陈那师承世亲,不过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因明,创造性地把因明论式从五支法简化为三支法,前者主要是归纳式逻辑,后者主要是归纳与演绎并用。这是因明学的重要发展。
据说当时有一位迦皮罗仙人,总是担心自己会死,就去请教大自在天湿婆。湿婆告诉他,去频陀山上找一种东西,吃了之后就能长生不死。谁知迦皮罗吃了之后却变成了一块床榻大小的石头,无法动弹,但却依然拥有生命和灵气。人们有什么问题,写成偈子去问他,往往就能得到答案。
有一天,陈那写好偈子去问石仙,石仙回答不出,立刻碎裂成一堆石头。这就是著名的“陈那裂石”的故事。
芨多王朝时期,国王在此大兴土木,兴建庙宇,竟在这座窣堵波附近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佛学院。
这座佛学院不仅教授大乘佛教和十八部派的佛教,还讲授婆罗门教和“吠陀”文献,以及医方和术数。在玄奘眼里,这里简直就是个缩小版的那烂陀寺。
玄奘到驮那羯磔迦国的主要目的是寻访陈那论师的遗迹,当然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学习和解惑的机会,于是停下匆匆的脚步,从苏部底、苏利耶两位比丘学习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
雨季一过,驮那羯磔迦国的码头上就变得熙熙攘攘,行人络绎不绝,炙热的阳光下,一群群的人们在高谈阔论,不时地向着大河的尽头张望。
“船来了!船来了!”
一艘硬木大船从河湾处缓缓驶出,在清油似的河面上拉出许多张力。衣着鲜亮的船工站立在船头上,岸上的人群立刻发出阵阵欢呼。
大船绕了一个弯,缓缓靠上了码头。船工朝岸上扔出棕缆,有人抢上前去,把绳子系在木桩上。
一块破旧的船板很快被放了下来,岸上的人提着大包小裹,赶着各种牲畜,拥挤着上了船。
身背竹箧的玄奘也在人群之中,他要乘坐这艘渡船前往南印度达罗毗荼国的大都城建志补罗城,那里是南印度的出海口,也是他的师祖护法菩萨的出生地。[5]
大船的甲板上堆满了乳酪、芥子油,以及用棕榈叶子覆盖着的鹿肉、石榴和柑橘,船舱里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气味儿。
船上乘客大都是达罗毗荼人,他们的肤色、语言和服饰,与中、北印度人有着明显的差异。男子习惯把一块麻布围在腰上,长短收放自如,在农田里干活时,还可撩起布角,掖在腰间。
宽阔的河面上渐渐起了风,船帆鼓胀起来,如同被吹到水面上的布匹。弯曲的河岸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越过高大的树冠极目远眺,可以看到在阳光下苍翠欲滴的蔗田和那遥远的海岸线。
海的那一边就是狮子国了吧?
在他身旁的是两个年轻人,他们是卖各式扇子的,其中一个打开包裹,给玄奘看那堆放成一叠的,用各种植物叶片晒干后制作而成的扇子。
“法师喜欢吗?买一把吧,看,这把最大,扇起来可凉快了!”
玄奘微笑着摇头,在他看来,炎热正是最好的修行环境,可以静观自己的内心是否清净,又何需扇子呢?
那人见他不买,也不介意,低头继续整理着。
突然,一柄大约半尺长的折扇从里面掉了出来,这把扇子个头很小,做工却很精细,黑黝黝的楠木柄隐隐散发着香气,在一大堆粗糙简陋的叶扇中显得格外惹眼。
玄奘忍不住拾起来打开,淡黄色的丝质扇面儿上,熟悉的中原字画扑面而来!
那画面很简单:一处宁静的山谷,一株兰草伸出柔弱的叶脉,默默散发着生命的芳华。没有烁烁花蕊,也无蜂蝶飞绕,宁静、疏离、清雅,令人一见之下,内心便充满了安宁与平和。
玄奘觉得这株兰草似曾相识,仿佛触动了他心灵深处最柔软的角落,没有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只有最简单的淡泊与从容。
“漂亮吧?”卖扇的青年笑问道,语气颇为得意。
玄奘点了点头:“这把扇子是从哪里来的?”
问话间,声音竟有些微微颤抖。
“有人从汉地带来的。”卖扇人自豪地说道,随即又补充了一句,“这把扇子不卖的。”
“这是扇子?”先来的那个恭御陀国商人伸手拿了过去,用力摇了摇,“扇不出多大的风嘛,这么小的玩意儿,光漂亮有什么用?”
“怎么没用?”卖扇人伸手夺过道,“汉地的东西,可值钱啦!别用这么大力,当心给我糟蹋了。”
玄奘默然无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把小巧的折扇,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涌出一首小诗:
有风不动无风动,
不动无风动有风。
举处随时消酷暑,
动来常伴有清风。
在中原,扇子,特别是这种书画扇,堪称风雅之物。它绝不仅仅是一种解暑的生活用品,更是人们抒发情怀的好去处。
夏日炎炎,握上一把折扇,扇上题上两句自己喜爱的联诗,在树荫下、宅园中,一扇轻摇,凉风习习,虽系身外之物,却给人以天地广阔、境界深邃之感。
而这种感觉,怕是这些天竺商人永远也无法体会得到的。
“法师?”那卖扇青年突然叫了一声,把玄奘从遥远的故国情思中拉了回来。
“法师是从汉地来的,那儿一定有很多这种扇子吧?”
玄奘点了点头:“当年,书圣王羲之,见蕺山老妇沿街卖扇,生意冷清,不禁心生怜悯,遂提笔在每把扇子上写了五个字,署上大名。如此一来,扇子身价倍增,每扇百金,霎时被抢购一空。”
“怎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恭御陀国商人显然不信,说道,“写上几个字,画上一幅画,顶多比原来的漂亮些,增加一两枚钱也就够了,毕竟扇子是用来扇风的,不是用来看的。在上面写字能增加清凉感吗?”
“能增加。”玄奘认真地说道,“一把普通的扇子,只能从外面扇风,去不了人心中的燥热;而一把拥有好字好画的扇子,带给人的清凉爽快,却是起自内心的,有时甚至可以增长智慧。”
见周围人都是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玄奘接着说道:“三国时期,蜀国军师诸葛亮,与晋宣帝战于渭滨,乘素舆,戴葛巾,手摇白羽扇,指挥三军作战。扇子代替了指挥刀,可谓功不可没。”
玄奘说的话,这些印度人显然是听不懂的,因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中国文化。
其实,山水花竹也好,琴棋书画也罢,都没有固定的主人,谁有闲暇去细致品味,谁就是它们真正的主人,谁就能从中得到无穷乐趣,体味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清凉与舒适。
不过,卖扇人显然是被玄奘的话吸引住了,他打开手中的折扇,观赏着,感慨道:“啥时候能见着汉地的船队就好了,我定要跟他们去那里看看。”
“你见不着的。”旁边有人凑趣道,“我有一个朋友倒是去过汉地,他是个生意人,有自己的船,还有水手。他们到过很多地方。”
“吹什么牛?”恭御陀国商人撇了撇嘴。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那人道,“我那朋友是狮子国人,平常主要去爪哇一带做生意。你们知道的,那些小岛上的人很富有,他们从海里捞取的大宝珠,个头比这里的至少要大一倍!我朋友从狮子国带过去很多东西,地毯、粗布衣、马头梳、骨质汤勺,还有各种器皿、串珠、那麻达斯小毡毯、带翅膀的狮子座……跟那些傻瓜交换。回来时,船上满载着大宝珠和鸟粪,他就这样发了财!有一回,船在回国的途中遭遇了风浪,船只向东漂移了很远,食物也快吃光了,就在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的时候,就像神话一般,他们竟然看到了一座用黄金堆砌的城市!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汉地啊!我朋友在那儿住了一年,用大宝珠跟当地人换了很多的黄金和绸缎,后来他修好了船,这才重新起航,半年后回到这里,引起了轰动!”
对于这个人的话,玄奘有些半信半疑:“这位檀越,你那朋友到过的那座汉地城市,叫什么名字?”
“这我可不知道,没问。”
周围“哄”的一声,众人笑成了一团:“吹牛,就是吹牛!”
那人急了:“你们若不信,可以去问问大德菩提迷只,他刚从狮子国来。你们问问他,从狮子国坐船去汉地,是不是只要半年?”
玄奘心中不禁神往起来,不管此人所言是真是假,从南印度到中国有一条海路却是千真万确的。想当年,携经归国的法显大师、将禅宗带到中国的达摩祖师、立志去中原弘法的波颇密多罗大师,走的不都是这条路吗?
半年,只需要半年时间,我就可以回归故土。这是多么吸引人的一条路线啊!
夜已经深了,船舱内传出一片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玄奘仍安安静静地坐着,双目低垂,有如禅定。
舱外难得地起了风,为他带来了丝丝凉意。河水流速缓慢,一轮满月倒映河中,散发出柔和的清幽的光辉,舱内的一切都像是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丽。
这本该是一个能收获酣眠的美好舒适的夜晚,可玄奘却毫无睡意,那把浸透了故乡风物的折扇,以及商人们所说的那条便捷海路,将他心中压抑已久的乡愁重新勾了出来,此时此刻,他的内心便如翻江倒海一般,难以平静。
河的尽头是海,海的那一边,就是大唐了吧?此时的故乡,应该是冬天了吧?
依稀记得在那有雪的冬夜,他在禅房内就着火炉读经。炉上煨着一壶热茶,听着滋滋水声,嗅着缕缕茶香,一股暖流在周身荡漾,如风过竹,其音不绝。窗外的雪地泛着蓝莹莹的光,空气半明半暗,夜静如水,更显深邃和明亮。
玄奘忍不住轻叹一声,出家人四海为家,心随境走,随遇而安,有如行云流水一般。这道理他当然明白。从长安到天竺,他也一直都是这般要求自己的。可是现在,他却有了一种极其强烈的不安定的感觉,一种淹没在异域的空虚之感,霎时间覆盖了整个身心。
夜阑人静,明月的倒影在水中悠悠摆动,那些曾经有过的温暖,一点一滴地从心头升起,他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孤独。
“唉,我真不像是个方外之人……”他无奈地想着。
玄奘抵达建那补罗国时,这个国家还有百余座寺庙,万余僧众,大小乘兼习。当然,外道的数量也不少。
王宫城侧有一座大精舍,其内有悉达多太子的宝冠盛放在一只宝盒内,每逢斋日,便取出置于高台之上供人参观,其有至诚观礼者,多感发异光。
不过,玄奘眼中的这一宝冠却有些模糊,自打下了船,他就感觉头晕眼花,四肢无力,若非被周围的人扶住,怕是半路上就要倒下。
众人只当他是中暑发病,忙将他送入精舍内休息。
玄奘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是被那把来自故乡的漂亮折扇给扇倒的。
思乡是一种病,唯有乡情能医,可惜这里无药。
“大师是要走水路去康契普腊姆吗?”门外传来一个声音,“我们可不准备到河边去了,您知道,那些水盗可是专门猎取人胆的。”
“弟子听说,胆和心是连在一起的,取胆之前一定要先剖心呢。”这是另一个声音,听起来很年轻,有些微微发抖。
“这些都是谣言,不足为信。”一个苍老平静的声音缓缓传来,“你们看,世尊的宝冠就在这里,他会保佑我们这些修行人的。”
伴随着这些议论,从门外走进来一群人。
最前面的是一个瘦高的老僧,目光矍铄,神色淡然。在他的一左一右,是两位向导模样的人,身后则跟随着七八十个中青年僧侣。
尽管身体十分虚弱,玄奘仍强撑着起身向他们合掌问讯。
“想不到这里还有一位外国同修呐。”老僧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意,欠身还礼道,“请问法师尊号?”
“弟子玄奘,是来观礼佛陀宝冠的。”
“玄奘?”老僧眼前一亮,“可是那烂陀寺三藏法师摩诃耶那提婆吗?”
“不敢,正是弟子。”
老僧大喜:“世尊慈悲啊!五印各地的僧侣无不传颂‘大乘天’的美名,老僧在故乡就有耳闻,却不承想竟是这样一位青年才俊。今日在此得遇法师,也算难得的佛缘,看来我们没有白受那海上的风波之苦啊!不知法师是否要去康契普腊姆?若是,可否与我们同行?”
“多谢大师好意。”玄奘道,“弟子欲登船前往僧伽罗国。”
“哦?”老僧更奇,“法师去狮子国做什么?”
“玄奘听说,那里是提婆菩萨的诞生地,佛法兴隆,国中有通晓上座部三藏教典及深解《瑜伽师地论》的大德。”
听了这话,老僧不禁轻叹一声:“佛法隆盛,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狮子国的僧侣大都过海来投南印度了。”
玄奘心中奇怪:“这是为何?”
老僧叹道:“说起来也是业障,鄙国国王遇害,国内出现饥乱,僧徒四散。老僧不得已,只得携三百多位狮子国僧侣,过海来投南印度。”
这时,身后一位中年僧侣插口道:“法师要见通晓上座部三藏的大德,我师父便是。”
玄奘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老僧就是从狮子国来的高僧菩提迷只!看来那些商人所言不虚。
两天后,玄奘的病略好了一些,他决定接受大德菩提迷只的邀请,同他们师徒结伴,启程前往印度西海岸的康契普腊姆。
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狮子国境内发生内乱,原本打算的渡海之旅,自然也就作罢了。
他们所走的这一带全是大沼泽,瞿萨旦那国甚至以此作为东部边境的关防,身周的野草足有数人高,外缘遍布着酷似莲花的水生植物,密密匝匝,行人甚至可以踩在上面,在水面上自由地行走。
好在行不多远就看到了河道,可以搭乘船只,沿河道而行,立刻感觉轻松了许多,这也是由南印度去往西北印度的最佳通道。
玄奘静静地站立船头,透过白雾般的蒸气,注视着水面上那些清晰的极具层次感的森林倒影。
这片森林主要是由贝多罗树组成,绵延三十多里的贝多罗树,树叶又长又阔,油光闪亮。包括那烂陀寺在内的印度各地的僧侣学者,都喜欢到这里来,摘取树叶抄写经论。
当然不是白给你摘的,这些树叶价值不菲,是当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阳光使这片沼泽变得热气蒸腾,色彩缤纷。密林深处挤满了各种果木,呈现出浓郁的苍青色,远处的森林与近处的棕榈木则是稀稀落落的橄榄色,其外围又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剑麻与芦苇的阴影交替着,四周还有玫瑰红的大叶花朵和淡紫色的多刺毛荚果杂乱地生长在一处,交错而列……
就在这色彩斑斓的水草与树丛间,他们乘坐的灰色船只划开水波,缓缓行来。
玄奘在船头站得累了,便坐下来,双手抱膝,显出一个较为随意的姿态。茂密的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大面积的亮点,与视线合拍,令他昏昏欲睡。
这时大德菩提迷只也走出船舱,坐在他的身边,给他讲起了狮子国的故事——
“狮子国原先是没有佛法的,直到世尊涅槃后一百年左右,阿育王的弟弟抛弃人间爱欲,证得阿罗汉果,四处游化时,这才将佛教传到那个国家,并建立了许多寺院。”
“阿弥陀佛。”玄奘感叹,“阿育王兄弟对佛法的传播居功至伟。”
菩提迷只用手指了指远方,接着说道:“王宫旁边,有一座佛牙精舍,高几十丈。其侧又有一精舍,其中有先王所造的纯金佛像,佛髻上镶有一颗宝珠,据说非常珍贵,价值连城。”
“玄奘听说过,在东印度的夜晚,常看到东南方向有一颗亮星,有人说,是那颗宝珠在放光。”
“是啊,那宝珠的光能照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法师您是知道的,僧伽罗国被大海包围,出产各种珍珠宝贝。国王亲自祭祀,神灵就会献出奇货,国中居民纷纷出海寻找、采集,随其福报的不同,收获也有差别。凡是采得珠玑的,都必须缴纳赋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采取一颗可与那座佛像上的宝珠相媲美的珠子呢。”
“如此珍贵之物,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偷取?”玄奘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盗贼是何时都有的。”菩提迷只道,“有一群贼人曾经穿凿地道潜入其间,可是佛像太高了,他们无论怎样都够不到,于是便说:‘昔日佛陀修菩萨道时,为了众生,难舍能舍,即使是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怎么如今却连一颗宝珠都舍不得了呢?可见传说都是假的!’想不到这话一说完,那佛像竟然弯下了腰,让他们拿取宝珠。”
玄奘笑了:“这倒真是一桩奇事。”
“确是奇事啊,所以无人肯信。”菩提迷只道。
“我也不大信呢。”玄奘道,“倒不是那佛像肯不肯做这样的布施,而是佛陀居然会受一群盗贼的激将法,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菩提迷只也笑了:“这也是老僧感到怀疑的地方,但是传说如此。说起来,南印度人似乎特别喜欢对圣贤使用激将法,那个龙树之死的故事不也是如此吗?”
玄奘沉吟道:“关于龙树之死,我听到过很多版本。北印度人说他是对佛法理论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以至于陷入到深深的矛盾和不安之中,无法排遣,自尽而亡;中印度人说,他是被一大群论敌所逼迫,自行坐化;而南印度人却说,是引正王的太子为了早日登基,要求他布施头颅,而且那太子使用的是最为拙劣的激将的方式。”
说到这里,玄奘有些遗憾:“要是当地人将历史也像经典一样记录下来,而不是口口相传的话,就不会这么混乱了。”
菩提迷只倒不介意:“世间之事都是过眼云烟,本就用不着执着于真假的。”
“说得也是。”玄奘道,“后来呢?那些盗贼取了宝珠之后,怎么样了?”
“哦,那些盗贼拿了宝珠,到集市上去卖。看到的人都知道那是佛像头上的珠子,就将他们扭送王宫问罪。他们告诉国王说:‘这不是我们偷的,是佛自己给我们的。’国王当然不信,但还是决定亲自前去察看,果然见到佛像还保持着弯腰低头的姿势。国王大为震动,从此信心倍增,又以许多珍宝将这颗宝珠赎回,重新安置于佛像头上,直到今天还保存着。”
玄奘感慨,佛陀的慈悲真是无处不在,连盗贼都能感受得到。可叹的是,这些盗贼只会利用这种慈悲,满足自己的贪欲。
注释:
[1]《集量论》,印度新因明学重要著作,新因明创始人陈那论师著。分析佛教和外道的各种认识论,宣扬佛教,破斥外道。
[2]南憍萨罗,位于今天的马哈纳迪河上游的赖普尔或比拉普尔。
[3]引正王,音译娑多婆诃,古印度南憍萨罗国之主,皈依龙树。
[4]驮那羯磔迦国,即今天的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附近。
[5]达罗毗荼国,位于今天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