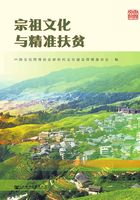
中篇 前沿研究
论太平天国运动后族权的强化
摘要 晚清以降,中国传统宗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在经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后,由于族权被严重削弱,反而激起了宗族势力的反扑,加之封建国家强有力的扶植,族权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空前强化,族权强化的方式有修葺宗祠、广置义田等。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回光返照”的确起到了延缓宗族制度土崩瓦解的作用,是晚清乃至民国宗族制度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太平天国 宗族 族权 佃农 义田
由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宗族制度在晚清呈现衰落的征象并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所以对晚清宗族的研究很多。 从整体上看,晚清宗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衰落主要表现为:西方经济的入侵使传统家族制度的根基产生动摇,近代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使传统家族组织渐趋瓦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家族共同体发生肢解,族田的兼并买卖使家族组织的活动日趋涣散;
从整体上看,晚清宗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衰落主要表现为:西方经济的入侵使传统家族制度的根基产生动摇,近代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使传统家族组织渐趋瓦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家族共同体发生肢解,族田的兼并买卖使家族组织的活动日趋涣散; 以太平天国运动为首的一系列农民革命及革命后的影响也重创了宗族势力。但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族权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正是宗族制度在晚清乃至民国没有发生根本变革或延缓变革的原因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无系统的论证,笔者略陈己见,不妥之处还望学界前辈指正。
以太平天国运动为首的一系列农民革命及革命后的影响也重创了宗族势力。但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族权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正是宗族制度在晚清乃至民国没有发生根本变革或延缓变革的原因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无系统的论证,笔者略陈己见,不妥之处还望学界前辈指正。
一 削弱与反扑:族权强化的原因
晚清伊始,宗族依然保持很强的凝聚力,如道光年间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及闽广之间,其俗犹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 但是1851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省,加上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宗族势力,被削弱的族权和战后被强化的族权形成鲜明对比,笔者才认为是“空前强化”。
但是1851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省,加上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宗族势力,被削弱的族权和战后被强化的族权形成鲜明对比,笔者才认为是“空前强化”。
关于族权被农民革命削弱的记载比比皆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时各地的团练,团练多是宗族势力组织和指挥的宗族武装,在与起义军交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削弱。湖南郴州士绅“曹魁隆咸丰五年率族壮丁随道员王鑫剿贼,叙六品军工”,但在当年十月全军覆没。 安徽贵池地主“王月高咸丰四年率族团击贼古田岭”,后战殁;
安徽贵池地主“王月高咸丰四年率族团击贼古田岭”,后战殁; 贵池诸生高都臣“咸丰四年率族人团练击贼,至同治元年死事者二百八十余人,都臣全家殉难”;
贵池诸生高都臣“咸丰四年率族人团练击贼,至同治元年死事者二百八十余人,都臣全家殉难”; “张成蹊,寿州武生,咸丰七年率练拒粤贼死之,阵亡三百余人,张族居其半。”
“张成蹊,寿州武生,咸丰七年率练拒粤贼死之,阵亡三百余人,张族居其半。” 凤台徐登善等“聚其族人”,在家族的防御工事内死守,“苦战九月,粮尽援绝,老弱饿死,丁壮多战殁,圩遂陷……圩内男妇死难者数千人”。
凤台徐登善等“聚其族人”,在家族的防御工事内死守,“苦战九月,粮尽援绝,老弱饿死,丁壮多战殁,圩遂陷……圩内男妇死难者数千人”。 团练主要由宗族武装组成,可谓“师皆父子,旅尽兄弟”,宗族性十分明显。据郑亦芳先生研究统计,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团练领袖都是以士绅为主体的,其中士绅领袖在广西为79.9%,在广东为78.4%,在湖南为56%。
团练主要由宗族武装组成,可谓“师皆父子,旅尽兄弟”,宗族性十分明显。据郑亦芳先生研究统计,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团练领袖都是以士绅为主体的,其中士绅领袖在广西为79.9%,在广东为78.4%,在湖南为56%。 士绅自然是宗族的代言人,“宗族是以士绅为首的组织”,“是士绅地主自觉的阶级形态”。
士绅自然是宗族的代言人,“宗族是以士绅为首的组织”,“是士绅地主自觉的阶级形态”。
此外,起义军所到之处,普遍砸神像、焚寺庙、毁祠堂、没收族田族产、搜刮富民,打击了宗族统治的精神偶像和物质基础,严重削弱了族权。如合肥龚氏本为当地望族,经过战争冲击,室家荡析,族人星散,趋于没落;桐城一些大的家族如马氏、光氏,同样在战后一蹶不振,威风不再。 浙江孝丰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约有4000人,战争期间颠沛流离,战后族姓生还者不过25人。
浙江孝丰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约有4000人,战争期间颠沛流离,战后族姓生还者不过25人。 很多“甲科相望,名门辈出”的“世族”,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不是“妻孥俱尽”“家败人亡”,就是“老成凋谢”“宗族零替”。
很多“甲科相望,名门辈出”的“世族”,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不是“妻孥俱尽”“家败人亡”,就是“老成凋谢”“宗族零替”。 宗族势力在经济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安徽建德的大家族“岁收田租数万石,商业利亦数万……粤匪扰江南,典业十余座,荡然无存,田荒无租可收,奔走流离,苦不堪言”;
宗族势力在经济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安徽建德的大家族“岁收田租数万石,商业利亦数万……粤匪扰江南,典业十余座,荡然无存,田荒无租可收,奔走流离,苦不堪言”; 陕西诸县“当日殷实富厚各家所有资财衣物房屋,诸产约值数万金或数十万金者,今皆化为灰烬荡然无存”。
陕西诸县“当日殷实富厚各家所有资财衣物房屋,诸产约值数万金或数十万金者,今皆化为灰烬荡然无存”。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仍能体现出对宗族的打击。除了“世家大族公私凋敝,乱定能光缵前绪者十无四五”, 尤其是广大农民在革命期间增长起来的反抗精神和阶级观念并没有因此磨灭,农民革命的影响也不会立即消失,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斗争勇气,对过去一直信奉不移的传统宗族观念产生了动摇,一反以往在族权面前卑怯的心态,从这点上说太平天国的作用在于“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尤其是广大农民在革命期间增长起来的反抗精神和阶级观念并没有因此磨灭,农民革命的影响也不会立即消失,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斗争勇气,对过去一直信奉不移的传统宗族观念产生了动摇,一反以往在族权面前卑怯的心态,从这点上说太平天国的作用在于“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战后宗族在恢复、加强族权和对佃农的支配与剥削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的阻力。浙江萧山“佃农欠租不清即可由业主召唤新佃……洪杨时,田主无权,民心大变”,
战后宗族在恢复、加强族权和对佃农的支配与剥削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的阻力。浙江萧山“佃农欠租不清即可由业主召唤新佃……洪杨时,田主无权,民心大变”, 无法随意撤佃。江苏金坛“昔之金坛故家遗俗礼让彬彬……今承大乱之余,旧德寝湮”;
无法随意撤佃。江苏金坛“昔之金坛故家遗俗礼让彬彬……今承大乱之余,旧德寝湮”; 江苏嘉定原本“佃户驯良,逋租绝少”,在战后“颇以抛荒挟制业户也”。
江苏嘉定原本“佃户驯良,逋租绝少”,在战后“颇以抛荒挟制业户也”。 安徽南陵“咸同以前民皆安业,惧涉公庭”,光绪以来则“畏葸之风为之筲减”。⑩过去浙江南浔的佃农任宗族势力摆布,战后则“奸猾成风”“佃强主弱”
安徽南陵“咸同以前民皆安业,惧涉公庭”,光绪以来则“畏葸之风为之筲减”。⑩过去浙江南浔的佃农任宗族势力摆布,战后则“奸猾成风”“佃强主弱” ,可谓“刁悍之风日甚一日”。
,可谓“刁悍之风日甚一日”。
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宗族势力为恢复和强化被农民革命削弱的族权,巩固宗法统治,必然会疯狂地反扑,这是战后族权强化的直接原因。族权被削弱,必然会影响宗族的地方统治,也就不利于宗族的封建剥削。因为族权与封建剥削二者的联系十分密切,族权是联系宗族内大户与小户、实现对佃农的剥削、维护家族利益的纽带,族规除了规范直系族人外,对依附的佃农也有着严格的约束作用,宗族与里甲结合促使族众按时交粮纳税,以家法族规惩治抗税抗差的族众,保证宗族和清王朝的赋役收入。一个地区的族权越强大,那么那个地区的祠堂、族田数量肯定就越多,如华南“粤民聚族而处,祠产素丰,事无大小皆听族首、族绅、祠长号召,族首等贤否不齐主者,既藉势豪,兼恃财力,取公帑以恣挥霍,敛众费以供侵渔”。 “族首、族绅、祠长”既扮演了封建大家长的角色,又是大地主,佃农不但是农奴,也是家奴。因此封建地主凭借族权对佃农实施暴力统治和经济剥削,族权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封建剥削更加得心应手。
“族首、族绅、祠长”既扮演了封建大家长的角色,又是大地主,佃农不但是农奴,也是家奴。因此封建地主凭借族权对佃农实施暴力统治和经济剥削,族权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封建剥削更加得心应手。
此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也助于族权的强化。在太平天国期间族权就开始了强化的历程,得益于封建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为了迅速扑灭农民革命,有效控制基层社会的力量,清政府被迫改变以往不正式承认族权的政策,于咸丰初年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 族权开始与政权相结合。随着农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在咸丰三年(1853)颁布《办团上谕》“著即颁发各直省督抚广为刊布,督同在籍帮办团练之士绅实力奉行……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
族权开始与政权相结合。随着农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在咸丰三年(1853)颁布《办团上谕》“著即颁发各直省督抚广为刊布,督同在籍帮办团练之士绅实力奉行……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 “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
“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 号召宗族势力兴办团练,这样宗族也就拥有了佣兵权。对宗族势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良机,虽然这只是清政府的权宜之计,清政府不会容忍族权的扩张,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在基层社会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中,封建皇权的力量最终只能让位于族权,清政府推行的排斥宗族的保甲政策最终荡然无存。咸同以降,族权迅速膨胀,一发而不可收,伴随着湘军、淮军的壮大,诞生了一批新的名门望族,如曾国藩“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
号召宗族势力兴办团练,这样宗族也就拥有了佣兵权。对宗族势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良机,虽然这只是清政府的权宜之计,清政府不会容忍族权的扩张,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在基层社会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中,封建皇权的力量最终只能让位于族权,清政府推行的排斥宗族的保甲政策最终荡然无存。咸同以降,族权迅速膨胀,一发而不可收,伴随着湘军、淮军的壮大,诞生了一批新的名门望族,如曾国藩“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 逐渐发展壮大,终成湘军,充当了国防军的角色。
逐渐发展壮大,终成湘军,充当了国防军的角色。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在,大规模的社会重建亦是如此。太平天国失败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地方宗族势力在战后的休养生息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不但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具有先天的地缘优势,因此清政府必须依靠宗族势力来进行战后重建,坐视族权的强化。虽然当政者一再强调选任得力官员担当复兴重任,各级政府不得不倚重地方势力,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在常州战后重建中就大量依靠常州籍的离任官员,他们作为郡望,具有突出作为与建树。 清政府对宗族的控制力度也随着国势的虚弱有所减弱。
清政府对宗族的控制力度也随着国势的虚弱有所减弱。
二 祠堂与义田:族权强化的方式
明嘉靖以降,由于废除了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组织开始民众化,进入一个缓慢发展期,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宗族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纷纷“反攻倒算”:修葺祠庙、厘定族规、完善谱牒、扩张族田、兴建义庄,开始了大规模的族权强化,在原太平天国的占领区尤是如此。清人讲“尊祖敬宗收族”实际上是宗族中的绅衿、富商、地主在宣传尊祖敬宗的同时,经营宗族公共经济,顾恤同宗,使族人服从其管理,以提高其社会地位。
晚清名臣周馥在《续修族谱序》中载:“童年见本村及散居城内外者不及百家,咸丰大乱,奔走流亡,岁丧十之七八……光绪初年,择其少壮者为之婚娶,孤寡月给养赡,迄今三十余年不辍,虽离官亦如之,今丁口已近半百。”可见周氏宗族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凝聚力一般,太平天国运动后更是分崩离析,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族权的措施,周馥本人认为敬先睦族、建祠续谱、厘定族约“乃一大事也”,必须“竭力成之,予曰不可缓也”。 到清末,“乡落者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
到清末,“乡落者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 已经非常常见。国家图书馆所藏的2270种族谱,其中清代所修1160种,
已经非常常见。国家图书馆所藏的2270种族谱,其中清代所修1160种, 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又以太平天国运动后居多,在同光年间达到高潮,反映族权的一个强化过程。
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又以太平天国运动后居多,在同光年间达到高潮,反映族权的一个强化过程。
安徽歙县程氏世忠祠在太平军刚刚退出的1866年就立即重订族规、恢复旧例、议定章程;歙县盐商在致富后多“扩祠寺、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下”,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达到强化族权的目的。河南安阳马氏宗族在1886年厘定东西支祠、祠堂条规,规定一切纠纷由族长裁决,任何人“不可轻易控告,违者以犯规论”;马氏族规还规定:“庶民得安田里,皆官法有以镇抚保护者也,宜何如遵敬奉守。若拖欠钱粮、躲避差徭、匿漏契税,以及贩卖硝磺、私钱、私盐等类,皆为犯规”。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达到强化族权的目的。河南安阳马氏宗族在1886年厘定东西支祠、祠堂条规,规定一切纠纷由族长裁决,任何人“不可轻易控告,违者以犯规论”;马氏族规还规定:“庶民得安田里,皆官法有以镇抚保护者也,宜何如遵敬奉守。若拖欠钱粮、躲避差徭、匿漏契税,以及贩卖硝磺、私钱、私盐等类,皆为犯规”。 可见强化族权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封建剥削,为了保证封建剥削,宗族势力也会千方百计地强化族权,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称其为“宗族地主”,是地主阶级的组成之一,宗族正是地主的社会组织。
可见强化族权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封建剥削,为了保证封建剥削,宗族势力也会千方百计地强化族权,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称其为“宗族地主”,是地主阶级的组成之一,宗族正是地主的社会组织。
安徽怀宁县“乾隆中叶始有葺祠堂、修谱牒者,然不过一二,望族近则比户皆知惇叙,岁以清明冬至,子姓群集宗祠,有不率教者,族尊得施鞭扑,居然为政于家”。 可见怀宁县族权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得到空前加强,在清中期还“不过一二”,到清末已经“比户”如此。浙江永康在康熙年间共有宗祠76座,到了光绪年间已经猛增到348座。
可见怀宁县族权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得到空前加强,在清中期还“不过一二”,到清末已经“比户”如此。浙江永康在康熙年间共有宗祠76座,到了光绪年间已经猛增到348座。 在清代的江南,宗祠不甚兴旺,宗法遭到相当程度的冷遇;相反,人们却热衷崇信其他神灵,
在清代的江南,宗祠不甚兴旺,宗法遭到相当程度的冷遇;相反,人们却热衷崇信其他神灵, 族权式微。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则“乡村皆聚族而居,无族不立宗祠,凡有事故必先祠内理论,方许经官。一村敬礼长,上下不敢轻犯,尊卑秩然”。
族权式微。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则“乡村皆聚族而居,无族不立宗祠,凡有事故必先祠内理论,方许经官。一村敬礼长,上下不敢轻犯,尊卑秩然”。 安徽《桐城麻溪姚氏宗谱》规定:“各处祖茔,无论公私,不许借口倚坟再葬,违者处死”,
安徽《桐城麻溪姚氏宗谱》规定:“各处祖茔,无论公私,不许借口倚坟再葬,违者处死”, 严厉至极,族权威严在战后达到顶峰。有人在战后致富后,马上就将所得资产捐为该族祠产,借以恢复族权。
严厉至极,族权威严在战后达到顶峰。有人在战后致富后,马上就将所得资产捐为该族祠产,借以恢复族权。
封建宗族还打着“扶弱济贫”的旗号通过建立义庄、广置义田的方式来加强族权。义庄义田从来都具有弱化宗族内部矛盾、稳定宗族共同体的作用。沈德潜认为,不设义庄“使其始一人之身分而至涂人而不相顾,先王亲睦之教渐流于衰熄也”, 同时代的方苞也认为:“有义田以养其族人,故宗法常行,无或敢犯”,
同时代的方苞也认为:“有义田以养其族人,故宗法常行,无或敢犯”, “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
“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 凭借义田才能保证“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人”,达到“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⑩的目的。因此义庄义田本身就具有增强族权的作用,是宗法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联系族众的工具,通过兴办宗族共有经济的方式来达到收族的目的。义庄对族权的强化主要体现在:义庄是宗祠经济基础的重要成分,义庄在赈贫同时宣扬亲亲之道和宗法伦理,义庄以附设义塾培养士人、巩固和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
凭借义田才能保证“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人”,达到“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⑩的目的。因此义庄义田本身就具有增强族权的作用,是宗法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联系族众的工具,通过兴办宗族共有经济的方式来达到收族的目的。义庄对族权的强化主要体现在:义庄是宗祠经济基础的重要成分,义庄在赈贫同时宣扬亲亲之道和宗法伦理,义庄以附设义塾培养士人、巩固和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 捐置义田规模增大,尤其是战后商捐义田所占份额的增大,反映了宗族观念、宗法统治越深入人心。
捐置义田规模增大,尤其是战后商捐义田所占份额的增大,反映了宗族观念、宗法统治越深入人心。
太平天国运动后,义田的强化族权作用更加明显,是笼络人心、抵消农民起义的影响、加强对佃农控制的重要手段。说到底,置义田是为了宗族自身的考虑,因为战后很多地区的土地是“无主土地”:要么原主全家灭门、外逃不归,要么地契毁失,要么土地被客民耕种拒不归还,于是宗族将这些可能有产权纠纷的“无主土地”捐作族中义田,以义田的名义勒取地租。而且,义田受到清政府法律的保护,如“苏抚部院挂发藩字第六十八号”明文规定:“倘有不肖子孙投献势要私捏典卖,及富室强宗谋吞受卖,各至十五亩以上者,悉依投献捏卖祖坟山地原例,问发充军,田产收回,卖价入官,不及前数者,即照盗卖官田律治罪。” 义田严禁买卖,可以保证子孙的有效传承,“人情莫不私其所亲,莫不思置美田宅以利其子孙,不数传而荡然无存,而义庄之设往往可久,即其子孙亦往往能自树立以表见于世”,
义田严禁买卖,可以保证子孙的有效传承,“人情莫不私其所亲,莫不思置美田宅以利其子孙,不数传而荡然无存,而义庄之设往往可久,即其子孙亦往往能自树立以表见于世”, 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才会有人发出“使先时有义庄田二三千亩,吾族犹有赖焉,必不至困悴如此”
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才会有人发出“使先时有义庄田二三千亩,吾族犹有赖焉,必不至困悴如此” 的感慨。
的感慨。
太平天国运动后,苏州的义庄义田发展最快。清代苏州共新建立185个义庄,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后就有105个,年代不明12个;新增义田84192亩,占总数的55.66%。 以苏南的常熟、昭文两县为例,两县在1550~1910年三百多年间共建有义庄86处,
以苏南的常熟、昭文两县为例,两县在1550~1910年三百多年间共建有义庄86处, 其中1500~1850年有16处,1851~1863年有11处,1864~1910年有59处,
其中1500~1850年有16处,1851~1863年有11处,1864~1910年有59处, 太平天国运动后的50余年建立的义庄是前300年总数的2.19倍,占总数的68.6%,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50余年,几乎每年都有人设立义庄,而且这些义田面积很广,平均面积为760亩,总面积约为64000亩,两县耕地总数约为175万亩,义田占了耕地总数的3.7%。无锡荡口区的12个义庄,共有土地13751.6亩,占全区耕地总数的9.52%。
太平天国运动后的50余年建立的义庄是前300年总数的2.19倍,占总数的68.6%,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50余年,几乎每年都有人设立义庄,而且这些义田面积很广,平均面积为760亩,总面积约为64000亩,两县耕地总数约为175万亩,义田占了耕地总数的3.7%。无锡荡口区的12个义庄,共有土地13751.6亩,占全区耕地总数的9.52%。 在宗族制度更加盛行的广东、福建,这个比例无疑会更高,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东族田占耕地的30% ~40%,福建更达到一半以上,
在宗族制度更加盛行的广东、福建,这个比例无疑会更高,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东族田占耕地的30% ~40%,福建更达到一半以上, 义田比例自然也更高。
义田比例自然也更高。
苏州汪姓家族“大难既平,仍家居不出,里中义靡役不与,建诵芬义庄,捐田一千余亩”。 无锡的义庄在“前志亦有,不久而废,近鵞湖华氏创行之,踵者遂十数家,敦睦之风,庶几近古”,
无锡的义庄在“前志亦有,不久而废,近鵞湖华氏创行之,踵者遂十数家,敦睦之风,庶几近古”, 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本已废弛的义庄,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重新焕发活力;又如无锡过人秀夫妇“先置田百亩赡族之孤寡老疾者……累垂及千亩”,义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其子过廷栋手中终成大型义庄。⑪宁波“镇海李氏亦有义庄之举……李氏之在镇海,聚族而居者数百家”,先人筹建义庄未果,子孙“承先志卒成之。都凡置田二千亩”,载自光绪时人俞樾的《养正义庄记》,此外还有《宝善义庄记》记载有田1200亩、《候补道叶君墓志铭》记载义田1312亩,均出自俞樾之手,仅俞樾一人就替宁波三家义庄作记。湘潭郭氏家族先后捐田5000余亩,岁租6000余石,来建立义庄。
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本已废弛的义庄,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重新焕发活力;又如无锡过人秀夫妇“先置田百亩赡族之孤寡老疾者……累垂及千亩”,义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其子过廷栋手中终成大型义庄。⑪宁波“镇海李氏亦有义庄之举……李氏之在镇海,聚族而居者数百家”,先人筹建义庄未果,子孙“承先志卒成之。都凡置田二千亩”,载自光绪时人俞樾的《养正义庄记》,此外还有《宝善义庄记》记载有田1200亩、《候补道叶君墓志铭》记载义田1312亩,均出自俞樾之手,仅俞樾一人就替宁波三家义庄作记。湘潭郭氏家族先后捐田5000余亩,岁租6000余石,来建立义庄。 这些都反映了宗族势力卷土重来、族权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这些都反映了宗族势力卷土重来、族权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义田的增加强化了族权,族权强化后可以从义田收租,可谓“良性循环”。义田的收租者是宗族团体,凭借族权可以避免单个地主不易征租的缺陷,将佃户置于族权的管理之下,又可以依仗“公产”“公义”的名义,以官府为后盾,尽情地催租,对抗佃户的欠租和抗租。如江苏吴县潘氏义庄的条规记载得很清楚:“义田与大概私产不同,私产供一家之用,租缺尚可别挪,若义田缺租、钱粮,赒给、公用何从挪补?”苏州彭氏义庄条规口气更加严厉:“国课早完,不可拖欠,粮从租办,庄用全取给于田租,如佃农恃顽,送官立惩。” 范氏义庄族规虽然不依仗官方,但是把催租的责任加到了“勾当人”的身上,“义庄勾当人催米不足,随所欠分数克除请受(谓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请受之类),至纳米足日全给(已克数更不支)”,
范氏义庄族规虽然不依仗官方,但是把催租的责任加到了“勾当人”的身上,“义庄勾当人催米不足,随所欠分数克除请受(谓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请受之类),至纳米足日全给(已克数更不支)”, “勾当人”也是宗族中人,是宗族中相对受压迫的团体,如催租不足额,即在“勾当人”应得的月米内扣除。
“勾当人”也是宗族中人,是宗族中相对受压迫的团体,如催租不足额,即在“勾当人”应得的月米内扣除。
此外,太平天国失败后,招佃招垦变得十分苦难,田园荒芜、人口大量死亡,成分复杂、流动性大的客籍佃农(外族佃农)大大增加,以义田的名义进行招佃招垦,能够掩盖土地兼并的事实和地租剥削的本质,无疑能够让农民更加容易来承佃承垦,从而瓦解农民的反抗。虽然义庄义田在激增,但实际上救助的范围、救助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真正用来赡养族人的比例是很低的,义庄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落入建庄者和义庄的管理人员手中。外族佃农数量增加,宗族用族权来约束外族佃农,贯彻对土地的占有,却不会将义米用于救助外族佃农,通过剥削外族佃农来维护本族的利益,满足一己之私,可谓义田不义。
义庄义田对族权的强化还主要体现在兴义学、设庄塾、开展宗族教育上。义庄希冀通过普及教育以雍睦化族,培植家族人才,既光门第又庇宗族。 江西新城的“世家巨族……俱设有学田,随其士之多寡而分之,至已仕乃止,鼓读书而养廉”;
江西新城的“世家巨族……俱设有学田,随其士之多寡而分之,至已仕乃止,鼓读书而养廉”; 常熟杨氏敦本义庄“别置田一千余亩,转给本支读书应试之费”。
常熟杨氏敦本义庄“别置田一千余亩,转给本支读书应试之费”。 义庄部分承担了国家的教育职能,望族通过义学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必然怀着感恩之心,致仕后进一步支持宗族的兴旺。
义庄部分承担了国家的教育职能,望族通过义学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必然怀着感恩之心,致仕后进一步支持宗族的兴旺。
总之,建义庄、置义田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盛极一时,特别在那些受影响较深、地权纠纷比较激烈、农民反抗精神较强的地区,如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等省,无论是财力雄厚的强宗大姓,还是家资未丰的素族之门都争先恐后地捐置义田,动辄成百上千亩,以“敬宗睦族”的名义,公然强化族权,的确是“敬宗收族之良法”,缓和了宗族内部的矛盾,得以联宗联族共同压迫佃农。
三 余论
宗族具有天然权威,“缙绅之强大者,平素指挥其族人,皆如奴隶……愚民不畏官府,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 加之对知识文化的占有,决定了封建国家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更需借助地方宗族势力来进行太平天国运动后重建和约束基层社会。清政府虽然希望建立“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
加之对知识文化的占有,决定了封建国家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更需借助地方宗族势力来进行太平天国运动后重建和约束基层社会。清政府虽然希望建立“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 的理想社会,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后族权的空前强化,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族势力各行其是,权力高过地方政府,在地方统治中占主导地位,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宗族掌握生杀大权,族规大于法律,破坏了司法的完整性;部分宗族称霸一方,造成乡村社会的不稳定,逃避和抗拒赋税,扰乱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秩序等。
的理想社会,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后族权的空前强化,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族势力各行其是,权力高过地方政府,在地方统治中占主导地位,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宗族掌握生杀大权,族规大于法律,破坏了司法的完整性;部分宗族称霸一方,造成乡村社会的不稳定,逃避和抗拒赋税,扰乱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秩序等。
其实,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近代城市的迅速发展等,宗族制度必然会衰落,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是潜移默化、无力挽回的。然而,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反而引起了宗族势力的“警觉”,采取一切手段强化族权,封建国家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族权以维护统治,宗族势力不仅不遗余力地帮助清王朝镇压了农民革命,还通过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挑动家族的械斗转移农民的斗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等手段,保住了封建专制统治,助其实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造成了历史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的作用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