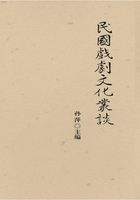
王(瑶卿)批《伶史》辑录考略[1]
钮骠
在一个半世纪的京剧艺术发展史中,一代大师王瑶卿先生以其赫赫功绩,完成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他在表演、编剧、导演、创腔、教学诸方面有着全智全能的卓越成就,贡献宏巨。并且,由于他出身梨园世家,广为交游,又亲身经历了京剧历史的开创期和繁盛期,见博识广。他以非凡的记忆力熟知京剧界的轶闻、掌故和同行们的家世、生平。为后世的戏曲研究工作提供了他耳闻目睹的许多第一手史料,洵足珍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做学生的时候,常到前门外大马神庙——我们这位老校长的寓所去上课受教。课前课后,闲话之中常常听到老人家滔滔不绝地讲起那些有趣的菊坛掌故、剧人逸事,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可惜的是,当时自己年少无心,还不懂得应该“有闻必录”。虽然灌到耳朵里不少,年深日久,有些在记忆中渐渐淡薄;有些简直忘得一干二净。而今怎能不深感悔憾无及呢!
幸者,一九六二年晚秋,一日,往访荣增学兄(瑶翁之四孙)于大马神庙旧古瑁轩,彼以近人穆辰公所著《伶史第一辑》一册惠赠。同时,示以另册内有瑶翁朱笔眉批者见览。我奉读批语,内容丰富,涉及的许多史料都是现行于世的文字记载中所不见的,殊觉贵重。这是瑶翁留下的有关剧作、题跋、后记等文字手迹之外的一份难得的遗稿。承荣增兄慨然允借,遂以蝇头楷书,一一过录于所得之册,并加点读,奉若家珍。十年乱中,几经隐存,又随身携之寄旅武林,最后总算保留下来未受损毁。今谨与《伶史》原文有关章句对照录之,并略事稽考,以供海内外的戏曲研究家和读者们探讨。
《伶史第一辑》(下简称《伶史》),著者穆辰公。全书正文以四号宋体铅字竖排,筒子页线装本,封面由王凤卿先生以隶书题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初版,由北京汉英图书馆发行。这是一部流传甚广的纪传体近代戏曲史料书籍,影响较大,其内容常为研究者所征引。书中所修近代京剧名伶传略者凡三十二人:以“本纪”体写十二人,“世家”体写二十人。作者在书前的“凡例”中虽有所申述,“名伶事迹多湮灭无征,非取材耆老之口碑不可,其无事可传者,则略之,绝不为之穿凿附会”,“惟外间传说,鲜能征实,出于臆造者犹不遑枚举。本书择其信而可征者著之。其荒唐无稽之谈,则概付阙如,用昭信史”;但也承认“其间尤不免鲁鱼亥豕之误。……此辑不过先事求教阅者,幸赐珠玉,以匡不逮”。看来,作者正是抱着这种“求教阅者”的意愿,将这部作品赠与王瑶卿先生的。赠书时间当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天。瑶翁对这部书的批点,估计不出一九一七年后的一两年内,也就是说在一九二〇年前,瑶卿正当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从笔迹上辨认,与同时期瑶翁手抄剧本中的笔迹相对照,也可以测定,这是瑶翁中年时期的手笔。作如上分析,无非是为了把批点的年代,有个大致地认定。
在十二“本纪”中,除对何桂山、金秀山、郭宝臣、德珺如各章未作详批外,余者均批之甚详;二十“世家”中,只批点了前十一人,后九人只字未批。可以看得出,批点至此中辍,没有再继续下去。剩下的九人是罗巧福(即“嘎嘎旦”,寿山、福山之父)、张云亭(昆旦,芷荃之父,文斌之祖父)、陆长林(昆老生,连桂、金桂之父,凤琴之祖父)、李寿峰(即李六、李成林,寿山、寿安、鑫甫之兄)、陆玉凤(工正旦,小芬、华云之父)、叶中定(工净,中兴之兄,春善之父)、姚增禄(工武生,杨小楼、余叔岩之师)、刘永春(即刘春,工净,何桂山弟子)、许荫棠(工王帽老生,德义之父)。这些都是梨园名家,关于他们的史料,瑶翁必深有所知,可惜未作批点,没有留下片言只字,实在是莫大的憾事!
《伶史》作者虽在书的“凡例”中有“绝不穿凿附会”之类的申述,但一经瑶翁过目,择拣出来的“鲁鱼亥豕之误”,为数还真是不少的。尽管如此,今天我们还是应该感谢这位作者。如果不是由于有了他撰述上的舛误,也不会引出瑶翁这位知情者的匡正,从而为后世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记载。
下面,对照录之:
一、《伶史》一页:“程长庚者,字玉珊,号四箴堂。”
王批:“号玉山,住百顺胡同,四箴堂乃门前之堂号,非号也。”
按:这在瑶翁同曹心泉、陈墨香、刘守鹤合写的《程长庚专记》(一九三二年一月《剧学月刊》创刊号)中,也有所记述:“长庚寓大百顺胡同西头路南,门榜曰‘四箴堂’。他有一副清音灯担,却又起名为‘椿寿堂’。心泉说:大老板名椿,长庚是他的小字,所以清音灯担上挂了‘椿寿’的字样。”
一九七九年秋,笔者与苏移同志得京剧音乐名宿迟景荣先生的领引,曾寻访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俞润仙、杨月楼、谭鑫培……诸京剧开宗大师的故居,百顺胡同路南“四箴堂”旧址,今已作街道工厂,新门牌为三十四号,比邻三十六号为杨月楼故居,四十号为俞润仙故居。
二、《伶史》三页:“长庚有子名章甫,善鼓板;有侄名章善。有孙二:少棠、继仙。”
王批:“有子二人,一名章弧,一名章甫。少棠兄弟四人;继先兄弟二人,一名招官,均是章甫子。”
按:这在《程长庚专记》中亦有记述:“他有两个嗣子:一是养子章甫,一是从子章瑚。”
近人张次溪撰《程长庚传》(一九三一年五月《戏剧月刊》一卷三期)中也说:“长曰章甫,次曰章瑚。章甫有子继先、招官。”
显然,瑶翁所书的“章弧”即音同字不同的“章瑚”。此曾询及迟景荣先生,也说章甫(一作章圃)是抱养子,章瑚是过继子,无误。至于章瑚的儿子少棠兄弟四人,只知少棠通德文,一九〇一年八国侵华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时,少棠曾被聘作与联军统帅瓦德西谈判的译员。李鸿章允诺以上海道职位相酬。但由于他是梨园艺人子弟不能入官,而被地方官员参劾未成,所以少棠不愿提及祖上长庚。兄弟中另三人,均不业梨园,名字未见传世。
综上所引,当可肯定,有些记述程长庚的文字中,把章甫说成“生子”、章瑚说成“章善”和说长庚只有“两个孙子”,都是失实的。
三、《伶史》三页:“孙菊仙者,津人也……锐意于武举业,刀马之暇,酷好声曲。”
王批:“菊仙乃是天津一锯碗匠出身,并非应武试者”,“孝钦皇后(引者按:即慈禧)曾着伊唱《百草山》耍笑他。”
按:世传记述有关孙菊仙的文字资料,大多是说孙为武举出身,曾任武职,如沈宗畸《便佳簃杂钞·孙伶传》中说他“少娴音律,富膂力,习武。……清中叶东南多事,从提督陈国瑞转战有年。”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说他:“十八岁戊午中武秀才;二十一岁辛酉投军陈国瑞麾下,受伤二次,改派管理右路军械所差使;二十七岁丁卯改投英西林宫保军营,时已由军功保至花翎三品衔,候补都司;……二十八岁戊辰随至两广总督任,充武巡捕。”后世介绍孙氏生平者,基本上都是以上述说法为据,何况更有《伶史》在先,又因周说较为详尽,故一直为研究者所采用沿袭至今,连新版《辞海》和《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的“孙菊仙”条目释文中,也有“原系武秀才”的字样。尽管王梦生《梨园佳话》中只提到“其先本为商”,小织帘馆主《名伶小纪》(二)中也只说其“初业粮食商”(一九二八年七月《戏剧月刊》一卷二期),然而均未被征引,影响不广。瑶翁所批孙为手工业工匠出身,并举慈禧故意让孙演唱《锯大缸》加以揶揄一事为佐证,看来并非毫无所据。这个与众不同的提法,很值得研究家们进一步稽考。
另,《伶史》二页中,记有程长庚婉劝孙菊仙弃功名而业梨园的一段对话,瑶翁也批道:“程素最轻视孙处,曾用足踢过。菊仙如何能与伊若此之近?”可见,程、孙的关系并不融洽。
《伶史》九页,关于程长庚评谭鑫培的声音“太甘,近于柔靡,亡国之音也”,评孙菊仙的声音“固壮,然其味苦。味之苦者,难适人口”的记述。瑶翁也批道:“苦甘之论,乃孙处在上海时人所说之话,程大老板并未说过此话。”
四、《伶史》四页:“时(引者按: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后)菊仙亡在沪,太监不敢以实报,因以其名列死籍中。由是菊仙不敢回京师,且不敢以实名问世,号为‘老乡亲’。”
王批:“在庚子后,菊仙并未报死。‘老乡亲’三字并非不敢露真名时所改,实天津同乡之本行人恭维他所起也。”
按:《便佳簃杂钞·孙伶传》中说:“伶人老乡亲,天津善歌者也,津人以同里故,以此呼之。”
张伯驹先生曾说过:孙系天津人,天津好戏剧者皆以“老乡亲”称之。这个名号的由来,有段故事:当年,凡外地演员去烟台演唱者,务须先去票房拜客送礼,演出始能顺利;否则,或终场无一好声,或票友手提一灯,将灯点着而去,观众即尾随而出,至空场停演。孙去烟台演出,对票房疏于礼节,首场演出《空城计》,自出场至城楼,台下默默不睬,孙唱至“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一句,改为了“我面前只可惜对牛弹琴”,于是,台下大哗,令其停演,并要在台上磕头赔礼。当时烟台有一班在当地经商任职的天津人,也在观剧,乃起而抗言,谓孙改唱戏词,固为非礼,但孙为天津人,是我们老乡亲,票房如此待他,便是藐视天津人。双方要打群架,互相僵持不下。另有观戏者,从旁调停,认为双方各有失礼之处,应该言归于好,双方始罢。次日,仍由孙重演《空城计》,自始至终彩声不绝。此后,即将孙菊仙名,易为“老乡亲”。
五、《伶史》十一页:记清末,谭鑫培赴庆王(奕劻)府堂会“庆王因语鑫培曰:‘鑫翁此来为寒宅光,良感。然必看薄面,为众宾演剧两出。’鑫培曰:‘不难,惟我疾新愈,不敢应命。’固强之,鑫培曰:‘王爷必欲使我歌两出,能使一军机大臣跪我,则必应命。’庆王有难色,忽一人已匍匐于鑫培脚下矣。视之则军机大臣那桐也。鑫培见而大笑,几绝其缨。是日果歌两出,其傲慢不羁如此。”
王批:“鑫培虽有自傲之名,也绝不能如此。此说未免太过。”
按:此则轶事,为近代多种戏曲史料所记述,而情节各异,大有径庭。如日人辻听花《书谭鑫培遗事》中载:“光绪戊申年,项城五十生辰。……(端方)戏谓谭曰:‘今日宫保寿诞,君能连唱两出,为我辈增色乎?’谭不欲,曰:‘除非中堂为我请安耳。’那桐大喜,乃屈一膝,向谭曰:‘老板赏脸!’谭无奈,是日竟演四出。”日人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伶界大王谭鑫培》节中则记:“一日,庆王府邸为其福晋大开寿筵。……庆王曰:‘今日特烦演双出。’谭首肯之。然要求军机大巨中之一人跪请彼前,则可应命。……忽一人趋至,不待谭之言终,曰:‘老板赏脸!’哀求长跽于谭之前。彼何人斯?军机大臣那桐也!谭呵呵大笑,遂演两出。”近人刘守鹤《谭鑫培专记》中也谓:“光、宣间庆亲王为妾做寿,邀谭唱两出。谭说‘我的病刚好一点,恐怕不便遵命。如果是要我唱两出,便是军机大臣下命令也不行。除非那军机大臣向我跪求,面子碍住了,我就只好不顾性命,唱两出。’话犹未完,已有一位朝衣朝冠者,向伊跪下,即军机大臣那桐是。是夕,谭始勉强唱两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剧学月刊》一卷十二期)近人远生《小叫天小传》又云:“肃王耆善家唱戏,军机大臣那桐为戏提调。叫天已唱两出矣。座人欲叫天更唱一出,莫敢言者。那率尔言之,叫天固持不可。那乃长揖而向之曰:‘老大哥赏我一个脸罢。’叫天无奈,乃勉强更唱一出。”(《娱闻录》九册、《梨园丛录》)另,日人独石马的《清季轶闻》、裘毓麐的《清代轶闻》中对此事亦有记述。
将以上几种不同的记述相较,当能看出,记载的乃是同一事件,主要人物也是谭鑫培和那桐。但又不难发觉,由于辗转传闻,各加润衍,其说不一,已现失实之弊。据说,按清制,大臣只向贝勒、郡王、亲王行请安礼。谭鑫培有“谭贝勒”的外号,即是因为这次偶受那桐一礼而得。但并未曾以“必欲使我歌两出,能使一军机大臣跪我,则必应命”之词要挟,更不是那桐“匍匐于鑫培脚下,……鑫培见而大笑,几绝其缨”。如果说这确是发生在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的事,是时瑶翁已经二十八岁,已与谭老合作多年,朝夕与共,对其性情当是深有所知的。况且,若实有如上情况,剧界内必有传闻,不胫而走,瑶翁绝对不会毫无所知,所以他认为《伶史》上的说法不足取信是有根据的。
六、《伶史》十一页:“鑫培家居,似已无心世事,然家无余财,其子五人……”
王批:“谭有八子二女。”
按:《伶史》所述,确属舛误。老谭确有八子:长子嘉善,原唱武生,后改经励科;次子嘉瑞,人称“谭二”,先演武丑,后业操琴;三子嘉祥,习武旦,兼青衣,后改小生;四子嘉荣,演武生;五子嘉宾,即小培,工老生;六子嘉乐,未入梨园;七子嘉祜,称“八爷”,系武行;八子嘉禄,称“九爷”,从文;二女:长女适上海著名武生夏月润,次女适著名须生王又宸。这在谭富英《我的祖父谭鑫培》(一九八一年第二期《戏剧论丛》)一文中,亦有记述。
七、《伶史》十一页:言谭鑫培“比来,年事愈增,而精神矍标,不类七旬之人,所演之戏,皆其壮年时物,精粹不减于畴昔。”
王批:“此数语是实在情形。”
按:瑶翁自青年时代,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夏搭入同庆班,就与谭老同台献艺,在台上铢两悉称,相得益彰。合演的《汾河湾》、《南天门》、《打渔杀家》、《桑园会》、《宝莲灯》、《武家坡》、《御碑亭》、《珠帘寨》、《法门寺》、《战蒲关》、《牧羊卷》、《三娘教子》、《四郎探母》等剧,红极一时,有的被誉为“戏中神品”,可见他们二位默契相知的程度。瑶翁赞同《伶史》中之所述,是从与谭老多年合作的舞台实践中切身体会到的,说来中肯,非同一般旁观者的评议。
八、《伶史》十二页:“郭宝臣本纪”一节,瑶翁批有:“别号小元红”字样。
按:清末北京山陕梆子的名须生郭宝臣,其艺名有多种叫法:如“元元红”、“元儿红”、“老元元红”和“小元红”,颇使后世莫衷一是,常出张冠李戴之误。按瑶翁批语,称“小元红”是妥切的。在齐如山《京剧之变迁》中有云:“十年前,梆子班唱老生的有‘小元红’名郭宝臣。……从前另有一位‘老元红’,所以大家管郭宝臣叫‘小元红’。”考梆子演员中以“元元红”为艺名者先后共有三人:最早的“元元红”名张四喜,蒲州梆子演员,郭宝臣之师;嗣后的“元元红”即郭宝臣。为了加以区别,便呼张为“老元元红”,郭为“小元红”;再后又有一“元元红”,乃天津的魏连升(一作魏联生),则冠之以“小”,即“小元元红”,以示区分。
九、《伶史》十四页:谈侯俊山“角为小旦,十三岁即有声于时,号曰‘十三旦’;或曰旦角为类十有三,俊山兼能之,故名。”
王批:“实是十三岁出台,号‘十三旦’。”
按:瑶翁肯定其前说,意兼否定其后说。后说确与事实不符。侯俊山本工梆子花旦,兼能武小生戏,如《英杰烈》、《辛安驿》、《花田错》、《七星庙》、《双锁山》、《翠屏山》、《小放牛》和《伐子都》、《八大锤》等均为拿手。从他所擅长的这些剧目上,已反映出了他的戏路子,后说显然不能成立。齐如山《京剧之变迁》中也说:“又比方十三旦,也因为才十三岁就出名了,所以叫十三旦。”
十、《伶史》十五页:记“德宗(引者按:即光绪帝)尝自命题,使俊山破之,亦通顺类秀才文”。
王批:“俊山更目不识丁。”
按:侯俊山出身于农民家庭,幼而失学,九岁即人科班学戏,“目不识丁”乃是常情。光绪末叶,瑶翁经常与侯俊山一同参加“传差”或堂会演出,互不陌生,对侯的文化程度有所体察了解,是不难做到的。说侯“目不识丁”当是实情。《伶史》写侯能够破题作文,达到秀才的水平,是不符事实的。
十一、《伶史》十七页:记刘鸿升“拜常二庄为师,入庆春班,……初演黑净剧,以新进无凭假,名不甚彰。……后以与谭鑫培配《失街亭》,佣资始渐增。寻患足疾,需人而行。……有外馆商人李三者,怜之,为延医。鸿升感激父之。老伶俞润仙亦悯其穷,饭之于家,且曰:鸿升有喉,当不久居人下,足疾非害也。鸿升居润仙家数年,足不出户。”
王批:“刘拜二庄后,出台唱二路花脸。在四喜班时,因秀山、永春二人脱离后,有素云、二立、三宝诸人大捧之下,声名日起。天乐园陪谭君演戏增份之事,实在无有。李玉臣代他医病是实。俞润仙与他素无交际。”
按:批语中的“秀山”即金秀山、“永春”即刘永春(亦名刘春),都是当时的名净。“素云”即朱素云(小生),“二立”即胡素仙(旦,二立为其乳名),“三宝”即路三宝(旦,名玉珊,三宝为别人所赠之名,并用作艺名)。“李玉臣”也有写作“李豫臣”或“李翼臣”的。
刘鸿升的成名曾得力于朱、胡、路的推重,这是未见记载的。“鸿升居润仙家数年”则属子虚乌有。
十二、《伶史》二十页:记黄润甫“尝供奉内廷,……一日与孙菊仙合演《逍遥津》。润甫状曹操,狠厉越常度,借以讽谏太后,勿进奸臣,为子孙忧。太后怒其过狠,罚其与金秀山演《双摇会》。”
王批:“孙处庚子后到上海才演《逍遥津》一剧。菊仙在京里时,未演过《逍遥津》。黄君一生就未唱过此戏。”此前并有:润甫“官名祥瑛,在内务府灯笼库当差,先走票,后入梁园,搭三庆班唱《三国志》本戏而得名。”
按:据清廷升平署档案所载:孙菊仙入宫充当教习是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走失,共历十六年。孙南下赴沪是在此之后,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起,才先后与潘月樵、李春来、夏月恒共开天仙茶园、春仙茶园和新舞台。瑶翁即指一九〇二年后这段时间内,孙菊仙才演了《逍遥津》。当然不是在京中,更非在宫内。查王芷章先生《清代伶官传》中所录:孙菊仙入宫后,自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所演剧目中,确无《逍遥津》一剧。因此,“讽谏太后”、“太后怒其过狠”之说也当然不复存在了。查孙菊仙演《逍遥津》见于记载者,最早是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民国八年戊午腊月二十六)夜场,育化会义务戏大轴,与高庆奎合演。再一次是同年九月三十日(民国八年己未八月初七)夜场,在第一舞台,义务戏压轴。(见《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况且,瑶翁还指出黄润甫一生中,非但未与孙合演过此剧,即使与别人,也并未唱过。
查黄卒于一九一六年六月(民国五年丙辰五月),《伶史》出版于一九一七年五月,正好黄已去世一年。故此,瑶翁笔下才概括言之“黄君一生……”,毫不模棱。瑶翁年事虽低于黄老,但他们都曾同期活跃于舞台之上,谁常演哪些戏、不演哪些戏,都是了然熟知的。瑶翁所批,当是信而可征的。而《伶史》作俑,贻误后人,至今仍常为研究者们所征引,然实属向壁虚造,无中生有。
瑶翁批之“搭三庆班唱《三国志》本戏而得名”,实指黄在《群英会》、《长坂坡》、《阳平关》诸剧中所扮演的曹操而言。黄有“活曹操”之誉,就是因在三庆班同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杨月楼、钱宝峰等合演这些戏而得。另外,他还常与田桂凤、杨小朵等人合演《战宛城》,也是拿手杰作,为后人奉为圭臬。
另,《伶史》记:“润甫以丙辰年五月卒,无葬资,杨小楼买棺敛之。”瑶翁批:“黄君故去,乃是乐宅所赠的棺材。”“乐宅”即北京中药商“乐家老铺”的乐家,通称“同仁堂乐家”。
十三、《伶史》二十二页:“荐德霖于三庆科班,习梨园业。”
王批:“并无三庆科班,乃大老板所立之四箴堂科班。”
按:同、光年间的三庆班为“大小班”,即除有成年演员外,并有童年演员同台演出,类似而今的“剧团带学员”形式。程长庚曾于百顺胡同西口内路南寓所立小班,即瑶翁所说的“四箴堂科班”,后由程子章甫主持,改用“椿寿堂”为名。教师有崇富贵、田宝琳和一位唱武旦的朱先生(名字不详)及本班大师兄殷荣海等。徒弟有陈德霖、钱金福、李顺亭(李五)、张淇林(长保)、李寿峰(成林,即李六)、李寿山(大李七)、陆杏林、侯幼云等。瑶翁与其二弟凤卿和迟月亭、李鑫甫也在这里练过功。
据迟景荣先生述:“百顺胡同院内有三层北房,每层一连五间,外院一层是徒弟们练功学戏的功房。程大老板住中层,最后一层住程氏家眷。徒弟们生活很苦,吃焦丁米(呈黑褐色的老米)饭,清水熬白菜。李五在菜汤里放点芝麻酱和醋,用以泡饭,吃得香极了!每日程大老板盥洗已毕,吃过早点,便把徒弟们集合一起,站成一排,逐人询问学戏情况:‘你学什么戏了?’徒弟答后,便令徒弟背诵一遍,如有错误,为之教正,背不出者受罚。当时由李顺亭经管发点心钱,每人一份,共六十二份,由此推测出当时有徒弟六十二名。”这个科班是历史最早的京剧科班,造就了许多优秀人才,因为它附属于三庆班,又是由程家主持,所以近代戏曲史料中多以“三庆科班”记之。而当时实无此名称,只冠以堂号,正如瑶翁所批。
十四、《伶史》二十二页:记陈德霖“光绪中叶,为其全盛之时,尝供奉内廷。”
王批:“德霖在少年时,并未有多大名望,民国以来入老年,名始大噪。”
按:光绪中叶,有时小福、余紫云、吴顺林(蔼仙)在前,陈德霖多演昆腔折子戏,如《出塞》、《刺虎》、《琴挑》、《写状三拉》等,近人罗瘿公《鞠部丛谭》中云:“德霖昆曲功力最深。及光绪中叶,昆曲极衰,无人过问,其时德霖乱弹功力尚浅,歌台之上,黯然无色,及他日锐进,至登峰造极。”此说可为王批佐证。陈德霖平生善自调摄,潜心练嗓,终年不辍,所以他年岁愈老,韵调愈高,五十岁后演出《祭江》、《祭塔》、《孝义节》诸剧,被推为一时绝唱。他性格温厚慈祥,待人诚挚,其艺其德,颇得后辈尊仰。瑶翁与王蕙芳、姜妙香、王琴侬、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诸位均从其问艺,尊称之为“老夫子”,由是陈老名声更显。
陈老生于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壬戌),正是他五十岁的时候,一九一二年进入民国,所以瑶翁批作:“民国以来入老年,名始大噪”是确切无误的。
十五、《伶史》二十三页:记龚云甫“初师刘桂庆,学老生,尝演于津门,未能红也。及回京,值孙菊仙掌四喜部,乏老旦,菊仙令云甫改习老旦,使熊连喜为之师。”
王批:“云甫初出台在陈丹仙所称(成)之鸿奎班,后来才拜熊连喜,搭四喜班始成名。”
按:据《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载:龚云甫“入南官园孙华亭之华兰习韵票房学老生戏,后经果桐来(名武丑)、迟韵卿约入小洪奎班,唱三月余,由孙华亭介绍拜孙菊仙为师,改搭四喜,……在四喜班改老旦。”这与瑶翁批语正相吻合。瑶翁青年时代,与陈七十合演《五花洞》,以假金莲胜过真金莲,从此假金莲为观众视作“头路活儿”就是在小鸿奎班的事。对本班的情况,瑶翁自然有所知闻,言之当会无误。
另,《伶史》记“云甫略通文义,能读书史,故其说白清晰,无讹字。”瑶翁批日:“无讹字,纯用京腔大字。”这正是龚云甫能够压倒当时的老旦谢宝云,俨然居为老旦之首的重要因素之一。龚不但在唱工中揉进了绵邈清新、纡徐妩媚的青衣腔,而且大胆采用了京音京字,使听者耳目一新,又加之他那肖似老妪的扮相,吸收了旦角身段的做派、塑造了各不雷同的形象,必然为人所喜闻乐见。
十六、《伶史》二十五页:《梅巧玲世家》一节中记:“光绪初,巧玲卒于家,有子两人,伯曰大琐,仲曰二琐。二琐……唱青衣,不亚于巧玲,且承父业。……二琐有遗孤名裙姊者。……裙姊者即梅兰芳也。……清季大琐益窘,乃以裙姊拜于朱小芬之门。”
王批:“梅君曾为四喜班主,余紫云、朱霞芬皆出其门下。”“二琐名肖芬,唱小生兼花旦,名不甚彰。兰芳乳名群儿,并不叫裙姊。雨田因云和堂主人朱霞芬与伊是师兄弟,才将兰芳送去门下为徒,霞芬虽早死,有师母照管。小霞、小芬、幼芬均是霞芬子,与兰芳系师兄弟,并非是伊师父。”
按:清同、光年间名旦梅巧玲门下弟子皆以“云”字排名,如余紫云、刘倩云、陈啸云、郑燕云、朱霭云等。霭云即霞芬。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也记有“朱霞芬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小霞,老二叫小芬,是梅先生的姐夫,老三叫幼芬”,与瑶翁所批相符。
据《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梅巧玲》一章记:“巧玲娶陈金爵之女,生子二,长名雨田,次名肖芬,即世所传大琐、二琐也。”查雨田一名明祥、一名启勋,大琐为其乳名;肖芬即竹芬,一名明瑞、一名启寿,乳名二琐(一说雨田名明瑞、肖芬名明端,似不确)。世传戏曲文字史料中,肖芬多以“竹芬”记之,而内行人则多呼之为“肖芬”。萧(长华)老生前提起梅二先生就总以“肖芬”称之。他曾对笔者说:“梅肖芬与宋万泰老先生合演《探亲家》,一饰亲家太太、一扮乡下妈妈,二人一胖一瘦,被人谓之‘肘子虾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玉成班在湖广馆演出堂会的戏单中,《闺房乐》一剧的演员也是以“肖芬、薇仙”(薇仙即陆小芬)记之(见《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今人有说肖芬名“雨卿”者,则不知何据?
瑶翁所批梅、朱两家的关系,在《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也有记载:“竹芬有子一人,小名群儿,名澜,艺名兰芳,字畹华,自幼由伯父梅雨田抚育,从师伯父云和堂名昆旦朱霭云门下学戏。”两说正好互为印证。
十七、《伶史》二十七页:“第一舞台落成,主其事者,以兰芳能系社会望,罗致之,当获厚利,于是简员卑词厚璧往聘兰芳。兰芳意为之动,受其聘。适为田际云所侦,以为兰芳朝行,天乐园夕倒类。因膝行入兰芳宅,顿首于地,哀其妙行,且曰:君朝行我夕死,君夕行我朝死,恐亦非君之利也。”
王批:“未免骂际云太苦,哀求许有,膝行入宅一事则无。”
按:北京柳树井第一舞台,落成于一九一四年初夏,六月九日开张。是时,梅兰芳先生正搭田际云(即想九霄,亦作响九霄)所组的“翊文社”,原即“玉成班”,经常演唱于前门外鲜鱼口天乐园(即今大众剧场)。因一九一四年春节前,官方下令通知,把所有“班”的名称,一律改为“社”,玉成班才从农历正月初一起,改名“翊文社”的。
梅先生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中,对搭翊文社这段经历,有专门章节叙述。以梅先生的为人、品格,自然不会把田际云曾哀求他的这件事记进去,现已无从核实。但从他所记述的其他情况中,依然可以窥测到,《伶史》对田际云的描述是不足取信的。更难以找到导致“膝行入宅”这一行动的理由。梅先生说:“民国三年翊文社的阵容,老生有孟小如、贾洪林、瑞德宝、高庆奎。武生是田雨农……。旦角有王蕙芳、路三宝、胡素仙跟我。老旦是谢宝云,小生是张宝昆。这台角色,要算整齐了。”(见《舞台生活四十年》)当时梅先生的戏码,大都排在倒第二、三。如与孟小如的《桑园寄子》、《赶三关》,与谢宝云的《母女会》、《孝义节》,与王蕙芳的《樊江关》、《五花洞》等,并不十分吃重,即使梅先生撤出,也绝不会导致“兰芳朝行,天乐园夕倒”的局面。况且从玉成班到翊文社期间,梅先生已曾于一九一三年随王凤卿先生赴沪演唱,一度离去过,先例在前,并未造成《伶史》所述的那种后果。可见瑶翁的批语是以事实为据的,《伶史》未免过于夸张失实。
《伶史》三十页中有对梅先生伯母的许多微词,瑶翁也批曰“未免冤枉人”。
十八、《伶史》三十一页:述俞润仙(菊笙)“清时,尝供奉内廷,深荷孝钦太后宠。”
王批:“润仙生平未入内廷当差,只随外班演过戏而矣。”
按:据清廷升平署档案所载,自一八八三年起至一九一一年止(光绪九年至宣统三年),先后挑选的民籍教习,演员一项共八十余人,以武生行当挑进的有杨隆寿、瑞德宝、周如奎(周瑞安之父)、杨小楼、董生(即董凤岩)、杨长福(即杨长喜,杨隆寿之次子)六人,并无俞润仙在内。可见俞确未以“供奉”身份演唱于内廷,至于随外班“传差”演出而进宫则会有的。
十九、《伶史》三十四页:“俞赞庭者,润仙之第三子也,行九,人以‘老九’呼之……;俞华庭者,润仙之妾腹子也……;润仙尚有一弟,……人呼之为‘俞二爷’……;孙棣棠者,字藕香,润仙婿也。”
王批:“老九乃俞之第一妾所生,老九还有一弟,在幼时亡去,华庭乃第二妾所生,俞二名光辉。孙藕香乃均春堂姜俪云之徒,妙香之师兄也。”
按:一般都说俞润仙共有四子,据瑶翁所批,实为五子:长子占鳌,不业梨园,次子振庭,人呼“俞五”,三子赞庭,人呼“老九”,四子华庭。弟兄三人,均工武生。另有一子,即赞庭之弟,幼时夭亡。五人乃为三母所生。婿孙棣棠,即武生孙毓堃之父,系小生姜妙香先生之父姜俪云(双喜)的门人,故以“香”字排名,名藕香。与诸如香、陈葵香、王兰香、何薇香、李桂香等为师兄弟。
二十、《伶史》三十五页:“(余)三胜皖人,……顾家贫无力就外傅,业贾复无资,以梨园为能治生,遂入伶籍。”
王批:“三胜乃安徽某科班出身,以黄忠戏得名,《珠帘寨》一剧乃伊所编。”
按:几十年来,戏曲研究者们无不说余三胜为鄂人,似乎已成毋庸置疑的定论。只有《伶史》和后来天柱外史氏所撰的《皖优谱》中云为“皖人”。值得思考的是,瑶翁对《伶史》所述不仅未作批驳,进而更说“三胜乃安徽某科班出身”。当然,外乡人也可能到安徽去坐科,何况安徽与湖北接壤,相隔不远。然而有一点不知是否可以作如下推测:即余所入的科班,不是以唱楚调为主的汉班,而是以唱徽调为主的徽班的可能性相当之大。与余叔岩相交甚厚的老顾曲家张伯驹先生也说过余三胜是徽派老生,并说他唱的二黄戏《上天台》、《宫门带》,西皮戏《长亭》、《天水关》、《火焚纪信》、《凤鸣关》、《摘缨会》皆为徽派之戏。循着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只言片语”所提供的线索,若能进一步追根寻源找出更充分的论据,那么许多行之数十年的旧论,恐怕就大有值得重新探究的必要了。笔者愿在这里提起研究家们的注意。
瑶翁所批“以黄忠戏得名”,言之实确。据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刊本《都门纪略·词场门》所载各班主要角色及他们擅场的剧目,春台班余三胜名下的第一出戏就是《定军山》黄忠。陈彦衡《旧剧丛谭》也说谭鑫培的《定军山》就是学余三胜的。足见余的黄忠戏堪称一时之冠,为后人所师法。
《珠帘寨》原为净角戏《沙陀国》,李克用一角是由花脸扮演的。自余三胜开始才由老生应工,剧本也随之有所变易。齐如山《京剧之变迁》的开宗第一条就说:“《珠帘寨》的李克用,原来本系染脸,自春台班朱大麻子扮演,才勾大花脸。余三胜去李克用,又用本色脸,谭鑫培宗之,现在都用本色脸了”。吴焘《梨园旧话》中也把《珠帘寨》列为余三胜的杰出佳剧,评为“独出冠时,观之令人神旺。”萧老生前也常说,余三胜的靠功戏是最著名的。
《定军山》、《珠帘寨》均为谭(鑫培)派及至后来的余(叔岩)派的看家戏,实一脉相承于余三胜。
二十一、《伶史》三十五页:“余砚芬者,字紫云,三胜子也。”二十六页:“小余三胜者,紫云子而三胜孙也,无字,名叔岩。”
王批:“紫云乃三胜承继子。”“叔岩有二兄一弟,兄学胡琴,其二皆无名声。”
按:余紫云名金梁,字砚芬,入景和堂梅巧玲门下。因梅氏弟子皆以“云”字排名,又取名紫云。从瑶翁的批语中,始知紫云非三胜亲生,实为承继子。叔岩幼时演唱贴名“小小余三胜”,而非“小余三胜”。按程(砚秋)夫人果素瑛先生说:余紫云则有过“小余三胜”之称。
紫云有四子二女:长子第福,字伯钦,绰号余瞎子,从孙老瘪学操胡琴;次子第禄,乳名大禄,不务剧业;三子第祺,字小云,乳名二禄,即叔岩,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老生艺术又一高峰的代表人物;四子第祉,一名卓夫,即须生余胜荪(“三胜之孙”意),艺宗程(长庚)派,后患精神病而终;长女素霞,叔岩之姊,适果湘林(仲莲),即程砚秋先生的岳丈;次女因病早亡。
二十二、《伶史》三十七页:“杨月楼者……父某为江湖上刺枪棒者。咸丰中,来京师卖艺于天桥下,名伶张二奎,奇其技,收养于家,俾为拳棒师。后遂业伶。时杨月楼方十余岁,善拳勇,而喉音殊洪亮,二奎因录为弟子,职为老生”。
王批:“月楼乃张二奎所立私寓徒弟,幼时学武生。(杨父)为拳棒师实系讹传。(月楼)中年始改老生。”
按:杨月楼的父亲名杨二喜,是唱武旦的,并非拳棒师。月楼幼入忠恕堂张二奎门墙,排名玉楼,与俞玉笙(即俞菊笙、润仙)、陆玉凤(旦)、沈玉莲(老生)为同辈,后改名月楼,艺兼文武而又能演猴儿戏。文戏《四郎探母》、《打金枝》、《五雷阵》、《牧羊卷》等,足传二奎衣钵。武戏中的短打戏《恶虎村》、《连环套》之黄天霸,长靠戏《贾家楼》之唐璧、《昊天关》之赵义均为拿手,尤以《长坂坡》之赵云名传遐迩,有“活赵云”之誉。《梨园旧话》中也说:“杨本以武生著名,后始兼演须生,二者并负盛誉”,与瑶翁所批吻合。
二十三、《伶史》三十八页:“杨小楼,……童时隶小荣春科班,学老生,以身体健硕,改业武生,所工剧为《长坂坡》、《战宛城》、《冀州城》、《艳阳楼》、《恶虎村》、《落马湖》、《连环套》诸剧”。
王批:“小楼在科班时,就学武生,演《陈塘关》、《莲花塘》诸剧。月楼故后,伊每搭班演戏必砸,有‘象牙饭桶’之别号。庚子以后,入‘宝胜和’,又去天津,名才渐渐而起。”
按:杨小楼是小荣椿科班二科的学生,入科后即从杨隆寿、姚增禄等学武生。梅(兰芳)先生说:“杨老板从小在小荣椿坐科,入手就学武生。我外祖(引者按:指杨隆寿)给他开蒙,第一出戏教的是《淮安府》。”(见《舞台生活四十年》)《伶史》中说“学老生”,显然有一误。所列举诸剧也都是杨氏中、晚年时期所常演的剧目,非幼时所能为。坐科时则常在《陈塘关》、《莲花塘》等群戏中扮演角色。《陈》剧系演《封神演义》中哪吒出世的一段故事;《莲》剧系演虬龙兴水作怪,天庭擒拿龙族的故事,一名《拿火龙》,后又改名《庆安澜》;都是神话题材的“灯彩戏”,或称“砌末戏”。《莲》剧先由四大徽班中的和春班排演,后为小荣椿科班所常演,又为小天仙科班所赓续。向年杨当是扮演《陈》剧中的哪吒、《莲》剧中的小龙,此二角都是由娃娃武生应工的。
据徐兰沅先生说:“杨老板在‘荣椿’出科之后搭班,不但派不上正戏,而且连配角都当不上。”扮个《挑华车》的岳帅,还被撤换下来。(见《舞台生活四十年》)迟景荣先生转述乃翁迟月亭老先生说过的:“小楼刚出科班后,到天津搭班,只应武行(行话俗谓‘打英雄’),才拿十八块钱包银,还是关在他伯岳丈周春奎的面子上。这时候已经二十岁出头了,直到三十岁前后才红的。”(杨的岳父周文乃春奎之弟,故称春奎为伯岳丈。他说有误)。
萧老也说过:“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小楼二十四岁时,初搭‘宝胜和’班在大栅栏庆乐园演唱。先贴名‘杨小楼’打不响,改贴‘小杨猴子’才转微为盛,后来又在天津打响,就渐渐红起来了。”
以上王、迟、萧、徐诸家,与杨氏均非一般关系,素常过从甚密,又是多年的舞台搭档,诸说一致,当是实确情况。
二十四、《伶史》三十九页:“甲午和局方成,国力渐蹙,太后(引者按:指慈禧)见小楼剧,不禁有感,须顾德宗,泪为之下。呜呼!闻鼓鼙而思将帅,其是之谓欤!”
王批:“甲午时,小楼正是‘象牙饭桶’之时代,何曾入内廷当差?庚子后始入内承差,乃是从天津归京复搭‘宝胜和’之时代也。”
按:甲午(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时,杨氏年方十七岁,艺能尚未成熟,不可能被挑选入宫,慈禧观其演剧之说自然不能成立。据清廷升平署档案所载:杨小楼的挑进年月是“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即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时年二十九岁。这是与“甲午”相隔十二年以后的事了。
二十五、《伶史》三十九页:“俞菊笙尝微服观其(引者按:指小楼)演剧,叹曰:杨月楼有子矣!因呼小楼至其家,以平生所工剧,举以授之。”
王批:“小楼之戏,乃是聘姚增禄、张长保所学,润仙并未传过一出。”
按:小荣椿科班的老板兼教师中,杨隆寿、姚增禄是教武生的;范福泰、唐玉玺是“看功先生”,担任武功、把子方面的基本训练;万春茂、王求安是“抄功先生”,担任毯子功长短筋斗方面的训练。杨小楼在科班里所打下的技艺基础,自然是受益于这些师辈。至于学戏方面,尽管曾以“俞(润仙)派门人”标榜,而实际上他曾从之受业的名师不下十来位,兹分述如下:
(一)坐科时期除从杨隆寿、姚增禄学《淮安府》、《八大锤》一类的基础戏外,同时还从杨万清那儿学了不少戏。唐伯弢《富连成三十年史》中述:“杨(万清)君昔充‘小荣椿’之武戏教员,于武生戏,极有心得,小楼从之学艺,获益不浅。”萧老也曾说过:“小楼的能耐,一半是跟杨万清学的。”杨后来曾任教于“喜连成”科班,康喜寿、何连涛、金连寿、骆连翔、王连平都曾从其受业。
(二)承继家学也是杨小楼师承的一个重要方面。《长坂坡》就是学乃父杨月楼。如俞润仙演赵云头上是打扎巾,杨月楼则是戴白夫子盔;俞演此剧,有“问军”一场(赵云在寻找糜夫人的途中,遇一军卒,询问主母的下落,然后直奔西南而去),杨演则无有此场。杨小楼演唱此剧,在扮相、场子、表演各方面均循自家路数。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至二十年代期间,杨氏在北京还曾多次反串老生戏,如《探母》(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第一舞台)、《大登殿》(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均在第一舞台)、《法门寺》(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在开明戏院)、《战太平》(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第一舞台)。其中的前三出就都是当年杨月楼常演的“奎派”佳剧。
(三)据迟景荣先生述:杨小楼的《安天会》、《武文华》、《状元印》和《宁武关》、《麒麟阁》都是向张淇林(长保)学戏。查《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载,以上出戏的初次贴演日期连续集中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转年八月期间。想来,这段时间正是杨向张学戏期间。《蜈蚣岭》是由范福泰教的。《林冲夜奔》、《武松打虎》是一九二二年杨小楼到上海演出时,经名净李连仲介绍向牛松山(长宝)学的。
(四)据萧老述:一九〇一年,杨氏二十四岁那年,经他介绍,曾正式拜了王福寿(绰号“红眼王四”)为师,学了《赵家楼》,还有《恶虎村》的李五。
(五)谭鑫培是杨的干爹,在艺术上时常对其指教。曾给杨说过《战宛城》,指点过《铁笼山》、《状元印》等剧。
(六)王楞仙、钱金福、鲍吉祥、俞振庭几位在念白、身段、把子方面也都对杨氏有过帮助和影响。杨氏对黄月山、王益友的戏也都有过借鉴。
(七)最后要提到俞润仙了。史家们和老观众无不知道杨小楼是俞润仙的及门弟子,杨也确实是宗法俞派的,演唱过许多俞派名作。人们自然以为俞向杨传授了不少的戏,《伶史》上也说俞“以平生所工剧,举以授之”。其实,宗俞的三大家:杨小楼、尚和玉、俞振庭,都不是经老俞一招一式、一字一板地教过的。尚、俞(振庭)是由老俞的内弟张玉贵(别号张老,钱金福的姐夫、武生张增明之父)为之说戏,然后经老俞指点的。杨也是以自己所会的戏去求教老俞,请其加以指拨。迟景荣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轶事:庚子后,杨小楼在天津唱红了,返京时带回来了特产酥糖,让管事的给余(玉琴)老板送一份去。管事的也没问是哪位yu老板,便送到俞润仙俞老板家了。俞非常高兴,说:“我这个师侄还真惦记着我这个师叔!”(因与月楼是师兄弟)感动之下,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他,哪些戏有不明白的地方,尽管来找我,我给他说。”杨听说后,喜出望外,随即到俞家请益,头一出便给他“归着”(整理加工的意思)了《挑华车》,告诉他“大战”一场,高宠该怎样摔叉、怎样捋马鬃等等。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之前,俞没有给杨说过戏。这种“画龙点睛”式的指授,与姚增禄、张长保、杨万青那种手把手地“细抠”(精雕细琢)是不一样的。所以瑶翁批作“润仙并未传过一出”是不无道理的。梅(兰芳)先生对此,也讲得极有分寸,他说:“(杨)出了科,正赶上俞菊笙的极盛时代。他看到了俞的这种有创造性的艺术,不肯轻易放过。一面用心观摩,一面认真学习。结果就把俞老先生最擅长的靠把戏《铁笼山》、《挑华车》等的技巧尽量吸收过来,丰富了他自己的艺术。”(见《舞台生活四十年》)这与后来宗杨(小楼)派艺术的人,并不一定就都直接受到过杨老的亲传是同等情况。
看杨小楼的师承,可以说他是艺宗俞杨(月楼、隆寿)、博学众家。这说明了他本着“做多师之徒,读诸家之书”的求学方法。这为他后来取得超凡的造诣、成就为一代宗师,把京剧武生艺术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二十六、《伶史》四十一页:“杨桂云者,字朵仙,皖北人也。父某,旧隶四喜部,职为武旦,兼昆乱,人呼为‘武旦杨二’。”
王批:“桂云之父名杨五,唱小花脸,搭四喜班,立德春堂私寓,罗百岁乃是伊门下弟子。因老而无子,桂云亦是伊之徒弟,本姓阎,自幼父母双亡,杨五认为己子,随改杨姓。不知武旦杨二从何处得来传闻?”“杨五还有一子,亦幼时抱养者,乳名四儿,唱武生,名不甚彰。”“幼朵还有一弟,名连官,幼时已亡去。”
按:世传史料中,多把杨桂云(朵仙)父亲(实为师父)的名字记作“杨桂庆”,行当写为“花旦”,按瑶翁所批,看来世说不实。况且,无论是师徒,或是父子,名字中同排一“桂”字,也难免让人产生疑窦。罗寿山早年师事杨五,与杨桂云配演了许多玩笑戏,因常随桂云车后步行入园,故有“跟车丑”的外号。桂云姓阎,《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有录载。《梨园旧话》中也说:“杨桂云为德春堂弟子,本阎姓,后为堂主杨五义子。”杨五的另一子,乳名四儿,唱武生者,即杨德云(见《皖优谱》)。
《伶史》四十二页,记杨小朵同一江南人合拍一照而被诈骗的事,瑶翁亦批:“同人照相被骗一事实无。”瑶翁是杨桂云的女婿,批语中所述的情况当是翔实无差的。
二十七、《伶史》四十三页:“余玉琴者,……父大海,……致玉琴于梨园,倩人代觅名师,师度其材,可为文武花旦。”
王批:“余大海天津科班打上手者,后入北京春台班。玉琴幼时被其父典与上海冯某为徒,与学武旦。”“余玉琴本姓于,因大海不识字,入春台班时,写人名牌者误写此‘余’字,至今未改回来。”
按:戏曲史料中,关于余玉琴先辈的记述,颇不一致,有说“(余)父得海,与四川道台某,有金兰契,尝随之入蜀,掌文书之事”(见《清代伶官传》),有说,“(余)祖余江伯候补知府”(见《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若按瑶翁所批,上述二说则可置疑。另如,对余玉琴的师承,说法也各不相同,都值得进一步稽考。
二十八、《伶史》四十五页:“余润华者,玉琴兄也,字春芳。”
王批:“春芳幼时亦是四箴堂后科之徒弟,曾习武旦,因其相貌太粗,改学武二花脸。……春芳尚有二子,长名三元,唱武旦,辛亥年亡故,次名八万,习老旦。”
按:关于余春芳,《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记载:“武净余春芳,名润华,……九岁投入四箴堂三庆科班,名余起林。”《皖优谱》亦载:“余春芳,字润华,一名起林,……年九岁,入四箴堂三庆科班,工武净。”均与瑶翁所述相符。
二十九、《伶史》四十六页:“(王)聚玉,幼师花脸朱春升,尽得其传,隶四喜、春台等班,一时之名角也。……子一名葵芳。”“聚宝字怀卿,幼从武花张大四学武生,隶四喜,继走津沪。……子三:蓉芳、蕙芳、菊芳。蓉芳一名永利,幼习武生,艺承家学。”
王批:“聚翁只演花面而矣,名角二字不敢恭维。聚玉之子名蓉芳,行六。槐卿入京搭‘嵩祝成’,与黄月山齐名。嫡妻华氏,生子三人:长名大立,性痴傻,幼年亡去;次名二立,又名葵芳,即现在上海的武花脸王永立是也;三名三立,因得疯病而亡。继配梅氏,乃雨田之妹,生子二人。长名蕙芳,按次第排行在四;次子名菊芳,行五。”
按:王聚宝,字槐卿(一作怀卿),即武生王八十,名旦王蕙芳之父、梅兰芳之姑丈。史料中关于蕙芳弟兄一辈的记载,常有讹误,《伶史》即是一例。瑶翁所批甚详,蕙芳弟兄辈按大排行顺次实为:(一)长子大立,早亡;(二)次子二立,名葵芳,即永立(一作永利),工武净,久居上海,辛亥革命时在上海曾随潘月樵、夏氏弟兄参加过陈其美组织的攻取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三)三子三立,病死;(四)四子蕙芳,工旦,善绘事,曾与梅兰芳齐名,世谓“兰蕙齐芳”;(五)五子菊芳,一名玉文,小玉成班坐科,习武生(以上均为槐卿子,嫡妻华氏生三子,续室梅氏生二子);(六)蓉芳,学文场,聚宝的哥哥聚玉之子,大排行六。同辈姊妹几人,《伶史》未提及,故瑶翁未批。据考一适姜妙香、一适迟景昆(世恭父)、一适田雨农(际云子)、一适黄润卿(楚宝父)、一适尚小云。
三十、《伶史》四十八页:“蕙芳字湘浦,小字四利子,幼隶云和堂习花旦,师秦稚芬,世所呼为‘秦五九’者是也。”“受第一舞台之聘,与王风卿合演《武家坡》、《汾河湾》诸剧。”
王批:“蕙芳在云和堂并未学得一出戏,出师后始受其姨夫秦五九教授花旦戏。玉珊、德霖均系拜门之师,此二位一教半出《红霓关》,一教一出《银空山》而矣。蕙芳从未唱过《武家坡》,大概是近来听戏之人与《汾河湾》分不清楚之故,把两出全写上,免得阅书人挑眼耳。”
按:《伶史》作者把“云和堂”与“秦稚芬”说在一起,显然不对。云和堂主人是朱霭云(霞芬),而秦稚芬是“国兴堂”主人。瑶翁批作“出师后……”便择清了前后两段时期上的混淆。从瑶翁批语中还使我们知道,王蕙芳虽为路三宝、陈德霖的门人,而所获甚少。其实,给予蕙芳教益最多的倒是瑶翁本人,然他出于自谦,只字未提。《古瑁轩弟子记》中就说:“王蕙芳从瑶卿请益最多,亦不在弟子之列,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瑶卿盛时,蕙芳屡与同班。”(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卷七期《剧学月刊》)查《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自一九一四年六月第一舞台建成开业以来,王蕙芳在这里所演唱的剧目中,《汾河湾》是有的,而《武家坡》确无。王在其他戏园,也未贴演过此剧。瑶翁所批实确。
三十一、《伶史》四十九页:“田际云者,高阳人也,名瑞麟,别号‘想九霄’。”
王批:“田际云原名麟瑞,后改瑞麟,将两字颠倒着用,不知何用意?”
按:世传戏曲史料中,均记田际云名为“瑞麟”,据瑶翁所批,此名已非最早的原名了。“将两字颠倒着用”始于何时、原因何在?待考。对《伶史》此节中所记田际云幼时学艺及身世情况,瑶翁批曰:“出身来历无错乱处。”
三十二、《伶史》五十页:“际云十五岁,已飞(蜚)声沪上矣,金桂茶园遣人来邀。际云因之沪,月得包银百两,最受欢迎之戏,为全本《春秋配》、《蝴蝶杯》、《凤连山》。”
王批:“《春秋配》系伊得意之戏,《蝴蝶杯》等无听说过,《凤连山》戏名太冷,有无错误不敢胡说。”
按:田际云生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十五岁时当为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本年赴沪同往者还有黄月山、达子红、孙彩珠、陆小芬、谭鑫培等,合演于金桂园。《凤连山》实为黄月山主演的《凤凰山》之误。或为《伶史》作者记错,或为书中误植。
三十三、《伶史》五十一页:“《斗牛宫》剧,脚末中有画一帧,绘九天仙女像,际云每饰此角,画上置一额,文为‘想九霄’。想九霄者,沪人赠际云之绰号也。”
王批:“‘想九霄’际云之别号,《斗牛宫》画上横匾亦用此三字,可见其不通之处。”
按:这里,瑶翁对演员脱离剧情进行自我宣传的做法是鄙薄的,可见其对艺术严肃认真的态度。
三十四、《伶史》五十三页,记述田际云之子田雨农的一节,瑶翁在上批曰:“雨农为人甚好,《伶史》出版之期,即是雨农去世之月,可惨享年二十三岁!”
按:《伶史》出版之期为一九一七年五月,适逢田雨农逝世,瑶翁深为悼惜!
田雨农幼从茹莱卿、董凤岩学武生,能戏颇多,常演《恶虎村》、《连环套》、《英雄义》、《战宛城》、《冀州城》、《铁公鸡》、《金钱豹》诸剧,是民初玉成班、翊文社的台柱,常年露演于大乐园,在津沪各地也负声誉,与韩长宝、小宝义(即曹宝义、曹艺斌之父)齐名。关于田雨农,梅(兰芳)先生介绍说:“他唱武生,扮相英俊,武功纯熟,学的是俞五(振庭)一派。”“我同他合演过《长坂坡》,是贾洪林的刘备、郝寿臣的曹操、王蕙芳的甘夫人、我的糜夫人。糜夫人‘跳井’一场,他做得很认真,一点不肯偷懒。……就凭他这一身本领,要不是死得早,到他的晚年,也一定可以有很大的成就的。”(见《舞台生活四十年》)。
三十五、《伶史》五十三页:“汪桂芬世家”一章中,提到汪父“连宝职为武生,以《独木关》、《英雄义》诸剧,能见其长。”
王批:“《独木关》一戏来路甚低,汪君并未演过。”
按:汪父“连宝”实为“年宝(一作年保)”之误。据《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记:桂芬“父为四喜部著名武老生,后掌春台部,名年保,号雨楼”,与任七十、杨月楼、俞润仙为同时人物。考《独木关》一剧,最早见于高腔班和梆子班剧目中,二黄班首演此剧者为黄月山。黄享名于光宣、民初时期,而汪早于咸同年间就献艺菊坛了。瑶翁批作“汪君并未演过”当是实情。从《京剧之变迁》所记“汪年宝系大头(引者按:即汪桂芬)之父,唱武生,极有名。当年《打虎》、《夜奔》等戏,身段姿势异常之好,极能叫座”数语中,可见汪之所擅。曹心泉也说:汪年宝的《打虎》、《夜奔》最著名。
三十六、《伶史》五十三页:“桂芬幼隶陈丹仙所营之春茂私寓。”
王批:“桂芬与陈丹仙系师兄弟。”
按:汪桂芬幼入春茂堂陈天全(兰笙,号星垣,丹仙之父)门下。同门师兄弟均以“桂”字排名、“仙”字排号。如陈桂宝,号丹仙,习武生;韩桂喜,号凤仙,习青衣兼武旦,陈桂寿,号蟾仙,习花旦兼小生,注桂芬,号美仙,初学旦兼老生,曾改老旦,又学操琴。入陈丹仙门下的乃是后来的老生贾洪林。《伶史》作者张冠李戴,所云实误。
三十七、《伶史》五十一页:记述田际云在沪时,曾与汪桂芬、潘月樵往普陀山进香受戒,各取法名,田为德音、汪为德砚、潘为德文。
王批:“际云的记载说桂芬法名德砚错矣!伊名德声。”
按:田、汪、潘各取法名之事,虽与其艺事无干,然而却常见于史料之中。有说汪称“德生道人”的,也有说称“德心大师”的,均不确。稍细心些便不难看出,其法名的末一字“音、声、文”都是从职业特点取意的。瑶翁此批,免再讹传。
三十八、《伶史》五十五页:“会内廷传差,值大雨,桂芬以为必中止矣,竟不到差。翌日,升平署即传桂芬去,大加申斥。桂芬虽心不悦,而无可如何,遂蹒跚一破庙中,坐化而去。”
王批:“桂芬死于嗜欲,并非气死的。”
按:查清廷升平署档案载:汪桂芬病故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一九〇八年六月)。这年,汪四十九岁,与“年四十九,以病瘵死”(曹惆生《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词典》)之说是一致的,可见汪桂芬是因染痨病致死,正如瑶翁所批“并非气死的”。
三十九、《伶史》五十六页:“朱文英者,……拿手戏为《打瓜园》、《蟠桃会》、《取金陵》、《盘丝洞》。”
王批:“《盘丝洞》为梅慧仙之绝戏,朱四十何尝演过。再者,非武旦之戏。”
按:萧老说过:“朱文英素有‘横(读去声)武旦’之称,在台上火勃勇猛,少妩媚气态,不常演文戏。偶尔扮演《翠屏山》的莺儿,也非所长。”而《盘丝洞》的蜘蛛精是花旦的本工,为梅巧玲所演红。当时,凡专工武旦者,不仅朱文英一人,其他人也不搬演。
四十、《伶史》五十七页:“阎金福,顺天人,幼走津沪,职为皮黄青衣,成名后,来京师。”
王批:“金福唱扫边青衣,非名角也。”
按:阎金福即著名武旦九阵风(阎岚秋)的父亲,一生主要是为人配戏,名不甚彰。
笔者不揣学识谫陋,辑录王瑶卿先生生前为《伶史》所作的眉批四十条,略事补证,不妥之处谅必难免,敬祈读者、专家们不吝指谬。
一九八二年孟春于佳黍楼
[1] 本文连载发表于《戏曲艺术》198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