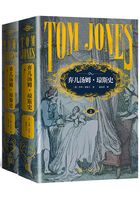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敬献于钦委财政委员会之一员乔治·李特勒屯大人
财政委员会委员执事台前:
我请执事许我将大名题于本献词之端,其事虽始终遭执事之拒绝,而我仍坚决认为,我愿执事之护持此书,绝非分外之想。
首先,此书所以能有开始之一日,即须归功于执事。我最初念及从事此种写作,实出于执事之意愿。此事已逾多年,或早已为执事所遗忘;但在我视之,则执事之意愿即性同诰谕,我一旦铭之于心,即永无磨灭之时。
其次,此书苟非出于执事之助,则将永无完成之日。执事闻吾此言,且请无须惊异。我决无意使执事蒙从事稗官小说家言之嫌。我所以称此书出于执事之助者,只欲说明,我在写此书之绝大部分岁月中,衣食之费多赖执事之资助:此又一事须我提醒执事者;因执事对某类情事特易遗忘,而我则希望对此类情事之记忆永胜于执事也。
最后,此书之所以得有今日,亦出于执事之赐。如在此书中,曾经写出一颗仁爱之心,如人所乐于称道者,而此仁爱之鲜明强烈,又远胜他书所写,则凡执事之友朋中特别深知执事者之一, 谁复一见此书而不知其中所写之仁爱从何处模拟而来者?我可自信,世间绝无人谬加恭维,以其所模拟者为我自身。但此并非我所计者;我只愿世人皆能承认,我所模拟之二人(亦即世上最仁爱善良、最应受景仰之二人),皆为对我忠贞坚定、热诚护持之良友是也。我有此二良友,本可心惬意足,但我之虚荣使我欲在二友之外复增一友。其人不仅在阀阅方面,且在为公为私、对内对外之道德方面,均极伟大高尚,其人即白德弗得公爵
谁复一见此书而不知其中所写之仁爱从何处模拟而来者?我可自信,世间绝无人谬加恭维,以其所模拟者为我自身。但此并非我所计者;我只愿世人皆能承认,我所模拟之二人(亦即世上最仁爱善良、最应受景仰之二人),皆为对我忠贞坚定、热诚护持之良友是也。我有此二良友,本可心惬意足,但我之虚荣使我欲在二友之外复增一友。其人不仅在阀阅方面,且在为公为私、对内对外之道德方面,均极伟大高尚,其人即白德弗得公爵 。我于此处,一方对公爵之隆遇优宠,满腹洋溢,铭肌镂骨,另一方又须请执事见谅,因我又须提醒执事,我所以邀公爵之青睐,实由于执事之推举也。
。我于此处,一方对公爵之隆遇优宠,满腹洋溢,铭肌镂骨,另一方又须请执事见谅,因我又须提醒执事,我所以邀公爵之青睐,实由于执事之推举也。
我现仍欲一明究竟者,即我恳执事假以大名,以光耀此书,为何遭到拒绝?噫,执事对此书奖誉称扬,过甚过汰,因使执事羞见大名于献词之端也。然而,苟此书使执事不羞于赞扬之,则我此处所言者,亦无可且不宜有使执事以之为羞者。我决不能因此书曾受执事之称扬而即放弃此书应受执事提携奖掖之惠。因我虽应自承受恩实多,但执事对此书奖掖提携之惠,却不在我所受恩之数。盖我深信,此所恳请与友谊无甚关联,以其既不能左右执事之明断,亦不能有伤执事之正直也。执事之仇,如应称赞,执事亦必不论何时皆称赞之,而执事之友,如有过失,执事亦必不谬加称赞,至多亦不过不加可否而已;即或友人过受苛责,执事亦不过轻为缓颊,不能反加称赞也。
以此,我颇疑执事之所以拒我所请,实以执事有美行而不欲为人称誉之故。我固尝留意矣,执事与吾其他二友,有一共同之点:即己之善行,虽有人轻微道及,亦均非所乐闻。执事诚有如彼伟大诗人对执事三人中之一所称道者(彼虽只称道一人,实可同样用于三人而无愧):汝
为善不使人知,见誉面红耳赤。
执事恶人之誉,既如世人恶人之毁,则执事见我深知执事之品德而生畏心,固应然矣。盖所惧在毁,则受害者所受之害愈大,其毁愈甚,其可畏亦愈甚;执事既惧誉如惧毁,则受恩者所受之恩愈大,其誉亦愈甚,其可畏亦愈甚。是执事畏我之誉,正与他人畏人之毁相同也。
且此惧毁之心,势必与其人取毁之道俱增,其人有以取毁之道愈多,其所受之毁亦愈多,其惧毁之心亦愈甚。如其人终生皆为受毁之的,而一旦为发怒之毁谤者所乘,则其战栗也固宜。以此理推之,执事既见誉而生厌,则我使执事生厌,事固甚明。
然而我有下忱,如执事信之,则我之所欲,即可得满足而无疑,此下忱亦即,我将永以执事性之所喜者置于我心之所欲者之上是也。我于此献词中即可以此意之明显实例置于台前,因我于此献词中,决取一切献词为范本,其所著笔非施惠之人所极应身受者,而为其人所最喜瞩目者。
以此,我无须更有赘言,而径将数年辛勤所获献于台前可也。此辛勤所获究竟有无可取之处,执事已所深知。 苟由执事对此书加以称赞,我径亦认为其尚可见重于世,则我此种尚可见重决不能谓之为虚荣;因执事如对任何他人之所作有所赞扬,我亦毫无保留而唯执事之意见是从也。自其消极方面言之,我至少可得而陈者,即我苟明知此书有重大缺陷,则绝不敢觍颜求执事对此书加以奖掖护持也。
苟由执事对此书加以称赞,我径亦认为其尚可见重于世,则我此种尚可见重决不能谓之为虚荣;因执事如对任何他人之所作有所赞扬,我亦毫无保留而唯执事之意见是从也。自其消极方面言之,我至少可得而陈者,即我苟明知此书有重大缺陷,则绝不敢觍颜求执事对此书加以奖掖护持也。
我所希望者为:读者见施惠于我者之大名,即可于开卷之时深信不疑,在全书中定无有害宗教、有伤道德之处,决无不合严格礼教风化之点,即最纯洁贞正之人读之,亦决不至刺目而忤意。不但此也,我且于此处郑重宣称,我在此书中全力以赴者,端在善良与天真之阐扬。此真诚之目的,曾谬蒙执事认为已经达到,实则此种目的,在此类著作中为最易达到者。因一副榜样即一幅图形,在此图形中,道德即成为有目共睹之实物,且于其玉体莹然裸露之中,使人起明艳耀眼之感,如柏拉图之所称道者。
除阐扬道德之美以使人仰慕敬爱而外,我并使人深信,人之真正利益端在追求道德,以此试图诱人以道德为动机而行动。欲达此目的,我并表明:内心之平静为道德及天真之伴侣,罪恶之所得,永不能偿内心平静之所失。且平静一失,罪恶于其空处引入吾人之胸中者即为恐怖与焦虑,即使罪恶有所得,亦不能与恐怖及焦虑相抵。再者,此种所得之本身既概无价值可言,且其达此种目的所假之手段,非但卑鄙而可耻,甚而其至佳者亦均不能稳定,或更往往充满危险。最后,我亦力图使人相信,道德与天真,除缺乏审慎而外,几无其他可使之受到损害;唯有缺乏审慎,始往往使之误陷欺骗及邪恶为之所设之牢笼圈套中,我所最致力者即在于此。因此事之教育为一切教育中最易有成功之望者。盖化贤人为哲人易,化恶人为贤人难,此我所深信者。
为达到此种目的,我于此书中用尽我所善为之“谐”与“谑” ,以喜怒笑骂鞭策人类,使之鉴于己身所习之愚昧与邪恶而改之。我于此善意之企图究成功几许,只有全凭坦率读者之评定。我所要求于读者仅有二事:(一)读者不能于此书求全责备;(二)苟此书某部或有优点,而其他部分则无之,亦请读者见谅。
,以喜怒笑骂鞭策人类,使之鉴于己身所习之愚昧与邪恶而改之。我于此善意之企图究成功几许,只有全凭坦率读者之评定。我所要求于读者仅有二事:(一)读者不能于此书求全责备;(二)苟此书某部或有优点,而其他部分则无之,亦请读者见谅。
属笔至此,应即毋庸再向执事喋喋矣。我本欲写献词,而实则献词已衍而为序言矣。然我又有何术能使其不如此乎?称扬执事我所不敢,而避而不为之方,我所知者,亦只有二途:即执事在我意念中之时,我或则完全缄默无言,或则一心转入其他意念也。
我在此札中所陈述者,非但未得执事之同意,且皆违拗执事之所欲,此我应请执事见谅者。又有恳者,我谨请执事,至少许我以此公开形式宣而称之曰,我即对执事最景仰、最感戴之
鞠躬匍匐、
犬马厮养
亨利·菲尔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