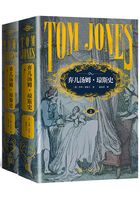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十章
奥维资先生殷勤好客;概述兄弟二人——一医生、一上尉——的性格,他们都是奥维资先生的座上客。
不管是奥维资先生的宅第,也不管是他的心胸,对于不论哪类人,都没有拒绝接纳的,但是对于有道之人和有识之士,更特别敞朗开阔。实在说起来,应该受到款待的人,一定能做座上食客的,在全英国,只有这一家。
但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比别类人,在他的恩赐中,更占主要地位。对于这两方面,他有极强大的鉴别力。因为他虽然不幸,没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但是既然承老天的德泽,生来就具有巨大的能力,而长大了以后,在学问方面,着意致力,又多和名人接触,所以,他获得很大的益处,能使他对于各种学问,绝大多数都善于判断。
在一个时代里,这样的长处毫不时兴,这样的人得到的待遇又非常菲薄;那么,如果有一个地方,对于有这种长处的人以礼接待,那他们一定要趋赴奔走,唯恐不及,这原不足怪。实在说起来,他们这种人在奥维资先生宅里,能享受到巨富所能供给的一切,几乎就和这份财产是他们自己名下所有一样。有一种慷慨好施的阔人,对于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供给饮食、住处,慷慨大方,他们不希冀别的,只希冀食客能给他们消闲解闷,指迷解疑,对他们奉承阿谀,供他们驱使奔走。简单地说,只希冀那班人身列仆人之中,不过不穿主人的号衣 、不拿主人的工资就是了。奥维资先生却绝不是这样施惠的人。
、不拿主人的工资就是了。奥维资先生却绝不是这样施惠的人。
不但不是,而且每个寄食他门下的人,都完全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且可以随心所欲,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要不犯法律,不违道德,不背宗教就成。所以,如果有的人,出于健康的需要,或者出于自身的节制,不喝酒,甚至不吃饭,那只要他高兴那样,就可在开饭的时候缺席或者退席,绝没人死乞白赖敦促劝诱,使他们非吃非喝不可。因为,说实在的,这种敦促劝诱,出之于在上者之口,永远含有命令的意味。但是在这儿,不论对什么人,一概没有这种轻蔑侮慢,不但对那班同样有财富、在所有别的地方都认为他们大驾光临能使宴席生辉的人,没有这种轻蔑侮慢,就是对那班家道寒微,因而这种白吃白住对他们是方便之门的人,对那班因为正需要筵席而反倒在阔人的席上不受欢迎的人,也都没有这种轻蔑侮慢。
在这种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卜利福大夫。这位绅士很不幸,因为他虽然天生有些才能,却没能受到才能的益处,只由于他有个脾气很犟的父亲,非要他学一种他不喜欢的职业不可。为了服从这种倔强,他年轻的时候,不得不做一个学医的;也可以说,不得不自称是一个学医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医学书几乎是他唯一不熟悉的;而且,这位大夫还真倒霉,对于一切别的学问,几乎没有一样不精通的,唯有他得用以挣面包的,却一窍不通。这样一来,这位大夫年交四十,却连面包也混不上了。
这样一个人一定会在奥维资先生的饭桌上受到欢迎,因为对于奥维资先生这个人,他的不幸遭遇,如果是由于别人的愚昧或奸邪引起的,而不是由于这个不幸的人自己,就永远是一种应受照顾的资格。这位大夫,除了这种消极方面的资格而外,还有积极方面应受照顾的资格——这就是对宗教虔诚的表现。至于这种虔诚是真的还是只是装模作样,我不必冒昧叙说,因为我没有任何能分辨真假的试金石。
他这种品性,不用说让奥维资先生觉得可喜,更让白蕊姞小姐觉得大乐。她多次和他辩论宗教问题,每辩论一次,她都认为这位大夫很有学问,因而满心欢喜。他也不示弱,屡屡对她表示敬意的时候,喜欢的程度也并不比她差。说实在的,她念了好多英国神学书,这方近左右的副牧师叫她难倒了的,并不止一个。一点儿不错,她的行为那样纯正,她的仪容那样庄重,她整个的态度和举动,就那样严肃神圣,因而她和她同名的女圣人 或者任何名载罗马历书上面的女性一样
或者任何名载罗马历书上面的女性一样 ,足以当得女圣人的称号。
,足以当得女圣人的称号。
既然是各种同情心都能生出爱情来,所以经验告诉我们,最能生出爱情来的同情心,莫过于男女二人之间的宗教同情。这位大夫既是看出来,白蕊姞小姐那样喜欢他,但因为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不幸,开始自悲自伤起来:这就是说,他跟另一个女人结过婚了,这个女人,不但现在仍旧健在,而且,更坏的情况是,这件事还是奥维资先生所知道的。这是一种要命的障碍,使他得不到幸福;要不是这样,那他十有八九,可以和那位年轻的小姐,共效于飞之乐了。因为他对于犯罪性的纵容恣睢,毫无疑问,绝没想过。这种情况,是由于他对宗教之笃诚(这是最有可能的),但是也可能是由于他对用情之纯洁,使他只能把情用在唯有婚姻才能使之有权实际拥有或者使之有权自称拥有的事物上,而不是男女之间犯罪性的关系。
他对于这件事并没琢磨多久,就想起来,他有个弟弟,并没因为有这种不幸而弄得对这件事无能为力。他认为,这个弟弟一定可以成功,因为他看出来,像他想的那样,这位小姐自己,也颇有意于结婚。读者诸公,要是听到这位弟弟所有的资格,大概不会因为他那样有把握、相信他弟弟能成功,而说他不对。
这位绅士年纪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而且是通常所说的肢体匀称。他的前额上有一块疤,但是那不但无损于他的秀美,反倒表示他的勇敢(因为他是一个支领津贴 的军官)。他的牙齿很整齐,高兴的时候,笑容里也露出一些彬彬有礼的样子,虽然他的面貌,还有他的神态和嗓音,天生地不免有些粗野,但是他有一种本领,能在任何时候把这类神色形貌收敛不露,而显出一片柔和,满身温良。他并非不够文雅,也不是完全缺乏风趣,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欢笑活泼;虽然他近来变得沉稳严肃,但是一旦高兴起来,仍旧能顿复旧观。
的军官)。他的牙齿很整齐,高兴的时候,笑容里也露出一些彬彬有礼的样子,虽然他的面貌,还有他的神态和嗓音,天生地不免有些粗野,但是他有一种本领,能在任何时候把这类神色形貌收敛不露,而显出一片柔和,满身温良。他并非不够文雅,也不是完全缺乏风趣,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欢笑活泼;虽然他近来变得沉稳严肃,但是一旦高兴起来,仍旧能顿复旧观。
他和那位大夫一样,受过大学教育,因为他父亲,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对他也和对他哥哥相同,行使父权,谕令他将来要担任圣职;但是那位老绅士在他儿子还没受任为牧师以前,就与世长辞了,因此他儿子就选择了以战斗为务的队伍, 宁愿接受国王的委派,而不愿接受主教的任命。
宁愿接受国王的委派,而不愿接受主教的任命。
他买了一个龙骑兵队 中尉的缺,
中尉的缺, 后来升到上尉;但是因为和上校闹翻了,没有前途,不得不把缺卖掉。从那时以后,他完全退隐乡居,日以诵习《圣经》为事,所以有人有些疑心,认为他颇有想当一名美以美会信徒之意
后来升到上尉;但是因为和上校闹翻了,没有前途,不得不把缺卖掉。从那时以后,他完全退隐乡居,日以诵习《圣经》为事,所以有人有些疑心,认为他颇有想当一名美以美会信徒之意 。
。
一个老处女,性行那样像一个圣人,心里又没有别的事情,只想能享到一般的家室之乐,遇到像卜利福上尉这样的男子,婚事成功,好像并非不近情理。但是这位大夫,毫无疑问,对他这个弟弟并无友爱之情。那他为什么却要为了他弟弟,竟对奥维资先生的豢养之恩,以这样的恶行相报呢?这是一件令人不易解释的勾当。
是不是有的人生来就以作恶为乐,就像有些人,人家以为他们生来就以行善为乐一样呢?是不是自己不便做贼,而帮人做贼,盗窃得遂,其中也有乐趣呢?最后(这是由于经验,可以认为很有可能的),是不是即使我们对于家里的人,一点儿也没有亲爱之心或者敬重之意,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家能发家致富,还是觉得心满意足呢?
是否有任何这类动机支配了这位大夫,我们不必肯定;但是事实却是如此。他把他弟弟叫来,很容易就找到借口,把他介绍到奥维资先生宅里。他说,他弟弟只打算来看一看他,暂住一时。
这位上尉来到奥维资先生宅里不到一星期,大夫就自庆眼力不错。这位上尉,确实是爱之艺术的大师,和古代的奥维得一样 。这还不算,他还从他哥哥那儿得到应有的启发,对这种启发,他毫不怠慢,加以改进,使之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
。这还不算,他还从他哥哥那儿得到应有的启发,对这种启发,他毫不怠慢,加以改进,使之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