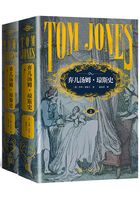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二章
这部伟大史书的主人公,以极不吉祥的朕兆出现。一件非常猥陋的琐事,有的读者也许要认为不值一顾。关于一个乡绅的一言半语,关于一个猎守和一个塾师的三言五语。
在我们刚坐下动笔写这部史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不对任何人奉承阿谀,而只一律按事实之所趋,挥笔前进;既然如此,所以我们导引我们的主人公出场登台的时候,就不能不使他显出远非我们愿意的那种没出息的样子来。我们还得在他刚一露面儿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当众宣布,说奥维资先生的宅子里所有的人全都认为,他毫无疑问,生来就是强盗坯子囚徒命 。
。
说实在的,这种揣测,有十二分充足的理由,这是我深为惆怅的。这个小子,从他最年轻的时候起,就露出好干各种坏事的苗头了,而更特别好干的那种坏事,是直接使之遭到我们刚说的那种命运的,也就是有先见之明的人对他谴责的:因为他确实已经犯过三回明夺暗窃的罪行了,那就是,在人家的果园里强摘过一回果子,在一家农舍的场院里偷过一只鸭子,在卜利福少爷的口袋儿里扒过一个球。
同时,这个小伙子这些罪过,和他的同伴卜利福少爷那样规矩正派对比起来,使他本来就显得处于不利的地位更加严重。因为卜利福少爷这个青年的性格,和小琼斯的完全相反;因此,不但在奥维资先生全家人中间,而且在所有邻近一带的人中间,都对他赞声四起。他的性格,实在得说有过人之处:稳重冷静,会见机而作,而且虔诚笃实,都不是他那样年轻的人就能做得到的。凡是认识他的人看到他这些品性,没有不喜欢他的,而汤姆·琼斯则到处惹人厌恶。好多人还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奥维资先生会让这样一个小伙子,和他外甥忝列同一门墙,因为他们恐怕,他外甥看到汤姆的榜样,会受到腐蚀。
在这个时期前后,发生了一件事,可以在有明鉴的读者面前,把他们两个的品格,更明显地摆出来,其说服力之强,远远胜过一篇最长的文章。
汤姆·琼斯(尽管是个坏小子,却当定了这部史书的主角)在这一家的全部仆人中,只有一个朋友。因为说到维勒钦阿姨,她早就认定了他是“没治”的了,所以和她的女主人完全站在一条线儿上。汤姆这个朋友是一个猎守,他是个大大咧咧、马虎随便的家伙,对于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这种分别, 也不比这个年轻的绅士自己有更不严格的看法儿。因此他们的友谊,在仆人中间,引起了许多冷嘲热讽;这些嘲讽,多数从前就是格言,或者说,至少现在变成了格言;所以它们的精义,都可以用那句简短的拉丁文概括,Noscitur a socio
也不比这个年轻的绅士自己有更不严格的看法儿。因此他们的友谊,在仆人中间,引起了许多冷嘲热讽;这些嘲讽,多数从前就是格言,或者说,至少现在变成了格言;所以它们的精义,都可以用那句简短的拉丁文概括,Noscitur a socio ;这句拉丁文,我认为,可用这句通行文表达,“观其友而知其人”。
;这句拉丁文,我认为,可用这句通行文表达,“观其友而知其人”。
要说实在的,琼斯所做的一些罪大恶极的坏事(我们已经刚刚举过三个例子了),有些大概可以说是受了这个家伙的鼓励,才干出来的。在那三回劣迹中,他都是法律上叫作是事后的从犯 ,因为那整只鸭子和大部分苹果,都归了猎守和他家里的人享用;虽然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但单独受到了全部的体罚,还单独受到了全部的谴责,因为就他一个人被发现。这两种处罚,在下面所说的场合下,又落到他身上。
,因为那整只鸭子和大部分苹果,都归了猎守和他家里的人享用;虽然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但单独受到了全部的体罚,还单独受到了全部的谴责,因为就他一个人被发现。这两种处罚,在下面所说的场合下,又落到他身上。
和奥维资先生的田产紧紧相邻的,是一位叫作蓄养狩猎物 那些绅士中间之一的庄园。看到这种人,因为一只兔子或者松鸡的死亡而采取的报复手段那种严厉劲儿,可以认为他们和印度的班尼安
那些绅士中间之一的庄园。看到这种人,因为一只兔子或者松鸡的死亡而采取的报复手段那种严厉劲儿,可以认为他们和印度的班尼安 奉行同一迷信的道门儿;据有人说,这个道门儿中间有许多人,一生之中,全都专以保全和护持某些种动物的生命为务。不过,我们英国这些班尼安,一方面保全这些动物,使它们不受别的敌人伤害,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又毫不仁慈,一驮子一驮子地屠杀这些动物;因此他们显然完全没犯印度那种异教迷信的罪行。
奉行同一迷信的道门儿;据有人说,这个道门儿中间有许多人,一生之中,全都专以保全和护持某些种动物的生命为务。不过,我们英国这些班尼安,一方面保全这些动物,使它们不受别的敌人伤害,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又毫不仁慈,一驮子一驮子地屠杀这些动物;因此他们显然完全没犯印度那种异教迷信的罪行。
我对这般人,以比对别的人更宽容的态度看待,因为我认为,他们只是在比许多别的人更广的范围内,奉行自然的命令,执行自然的告谕,以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良好目的。现在,既然贺拉斯告诉我们,说有一类人,
Fruges consumere nati,
“生来就要享受地上的果实”;所以我就一点儿也不怀疑,另有一类人
Feras consumere nati,
“就生来要享受野外的走兽”,或者像平常的叫法那样称作野味。因此我相信,没有人能否认,说那些乡绅们,只不过是要满足老天生他们的目的就是了。
小汤姆有一天,和那个猎守一块儿去打鸟儿,碰巧轰起一群松鸡来。这群松鸡所到的地方,靠近一所庄园,在这个庄园上,命运为了达到自然的圣哲目的,安插了一个专嗜野味的人。当时那些松鸡就飞到他的庄园以内一片常青棘灌木丛里,叫这两个猎人把它们落的地方“号”下来了(像他们的术语说的那样)。离奥维资先生的领域以外大概有二三百码。
奥维资先生曾严格地吩咐过这个猎守,叫他千万不要侵犯任何一家邻居,他要不听,就得把猎守的地位赔进去;不要说对这个邻居,即便对在这方面不那么严格的邻居,都不要侵犯。实在说起来,对于别的邻居,奥维资先生吩咐的这番话,并没非常严格地遵守;但是现在这些松鸡所托身投靠的绅士什么脾气,是大家都熟知的,所以那个猎守从来也没企图侵入他的领土。本来这一回他也没企图侵犯;但是那个年纪更轻的猎人,却特别想要追那些飞走了的野鸟儿,就尽力想说服他;琼斯极力怂恿,另外那个猎人,本来自己也很想追这些野鸟儿,可就听了他的劝说,进了那片庄园,把那群松鸡打死了一只。
庄园主自己那时正骑在马上,离他们不远;他听到枪声一响,马上往那个地点跑去,把可怜的汤姆抓住了;但是那个猎守却跳到灌木丛最密的地方,侥幸在那儿把身子隐住。
那位绅士把那个小伙子身上一搜,搜出了那只松鸡,扬言要报复,赌咒发誓,非告诉奥维资先生不可。他怎么说还是就怎么办;因为他马上就骑着马来到奥维资先生宅里,用顶愤怒的话语、顶尖刻的词句,大叫不该侵犯他的庄园,好像明火执仗,把他的宅子冲开,把他顶值钱的家具都抢走了似的。他还说,另外一个人,和汤姆在一块儿,不过他没抓住他;因为有两杆枪,几乎同时响起来。他又说,“我们只找到这一只松鸡,但是他们究竟闯了多大祸害,只有上帝知道罢了。”
汤姆刚一回到家里,马上就被传到奥维资先生面前。他承认了这件事实,也没有别的辩解,只把实情说了,那就是,那群松鸡,本来是在奥维资先生的庄园上轰起来的。
奥维资先生跟着就追问汤姆,和他在一块儿的是谁?他说,他非得追问出这个人来不可;他把当时有两下枪声的话,都对那个罪犯说了,这是那位乡绅自己和他的两个仆人,都这样证实出来的。但是汤姆却顽固地坚持就他一个人的说法儿;不过,要说实在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却稍为犹豫了一下;这种情况,本来就可以肯定奥维资先生之所信,如果在那位绅士和他的仆人所证明的以外,还需要别的情况进一步证实的话。
猎守既有嫌疑,现在奥维资先生就立刻把他传来,把同样的问题对他提出;但是汤姆已经答应过他,说一切都要由汤姆自己承担,他就凭这种答应的话,坚决否认他和那位年轻的绅士在一块儿,还说,他整个下午,连见都没见到汤姆。
奥维资先生于是脸上露出比平素更生气的样子来,转向汤姆,教他说实话,把那个人是谁说出来;同时把他一定非要知道和他在一块儿的是谁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但是那个小伙子,仍旧坚持他的老主意;奥维资先生于是很生气的样子把他打发走了,走的时候告诉他,教他顶到明天早晨,都要好好地考虑考虑,到了明天早晨,就另有人审问他了,而且用不同的方式来审问。
可怜的汤姆可真过了一个很不好受的晚上;再加上他平常的同伴不在跟前,更加使他难过;因为卜利福少爷和他妈一块儿往外国游历去了。害怕受惩罚,是这次这件事里他顶不在乎的,他主要忧虑的是害怕不能坚持到底,而没法子不得不把那个猎守出卖了。他知道,他一出卖那个猎守,猎守就得彻底完蛋。这是一定的后果。
那个猎守那一晚上,也同样地不舒服。他和那个小伙子有同样的顾虑;他对那个小伙子的荣誉,比对他的皮肉儿更爱护,更关心。
第二天早晨,汤姆来到道貌岸然的斯威克姆先生 跟前;奥维资先生就是把那两个孩子的教育委之于他的。现在这位塾师,把头天晚上那位绅士问汤姆的问题,又照样提出,汤姆对那些问题,又用昨晚同样的话回答。这番一问一答的结果是一顿鞭笞,抽得好不厉害,绝不下于有的国家用来逼问罪人的口供时所用的刑罚。
跟前;奥维资先生就是把那两个孩子的教育委之于他的。现在这位塾师,把头天晚上那位绅士问汤姆的问题,又照样提出,汤姆对那些问题,又用昨晚同样的话回答。这番一问一答的结果是一顿鞭笞,抽得好不厉害,绝不下于有的国家用来逼问罪人的口供时所用的刑罚。
汤姆对于这番惩罚,咬牙忍受,虽然他的老师每抽一下,都问一句,他说实话不说;他却都豁出去抽得皮开肉绽,也不肯出卖他的朋友,或者破坏他的诺言。
猎守现在放开心怀,不用焦虑了。奥维资先生就为汤姆受的刑罚难过起来;因为,斯威克姆先生,由于没能让这孩子说出他想要他说的话来,大为震怒,可就严酷得超过了那位善人所想要他做的了;除此而外,那位善人还疑惑起来,不知道他那位邻居乡绅是不是弄错了;因为那位邻居当时极端焦急,极端愤怒,很有可能是他弄错了。至于那两个仆人肯定他们的主人而说的话,他并没看得多么有分量。现在,既然残酷和诬陷这两种情况的存在,都是奥维资先生一时一刻都绝对受不了的,所以他就把汤姆叫到跟前,先说了许多仁爱和友好的劝诫之词,跟着又说,“我深信不疑,我亲爱的孩子,因为我疑心,教你受了委屈了;你为此受到很严厉的惩罚,我很难过。”最后给了他一匹小马,作为给他的补偿;同时又把自己为了刚才那些事难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现在汤姆犯的罪,使他痛切地自责,连他受的严厉惩罚,都不能使他那样。斯威克姆先生的鞭笞,他可以很容易地忍受,奥维资先生的宽容,他却难忍难受。他泪如泉涌,跪在地上,大声说道,“啊,义父啊,您对我太好了。一点儿不错,太好了。我实在不配受您这样的待遇。”他在那一会儿的工夫里,由于满怀真情激动,几乎要把实话说了出来;但是猎守的保护神灵,却对他示意,说他说了实话,会对那个可怜的猎守有什么后果,这种考虑,把他的嘴封住了。
斯威克姆尽其所能,想要说服奥维资先生,叫他不要对这孩子表示任何同情或者慈爱;他说,“他一口咬定,这一定是撒谎。”同时,透露出一种意思来,说再来一次鞭笞,大概十有八九,准能叫这孩子吐露真情。
但是奥维资先生却坚决不答应他作这种试图。他说,这孩子即便真有错儿,那他为了不肯说实话,也已经受够了惩罚了,因为他不会有别的动机,他这样做,也只不过是他对怎么样是荣誉,看得不对罢了。
“荣誉!”斯威克姆先生气愤地说,“这不过是顽梗固执!荣誉能叫人撒谎吗?任何荣誉能离开宗教而单独存在吗?”
这番议论,是刚刚吃完饭在饭桌上发生的;那时候坐在饭桌前的,有奥维资先生、斯威克姆先生,还有第三位绅士;这第三位绅士现在也参加了这场辩论;不过在我们再往下叙说的时候,我们得先简短地把他介绍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