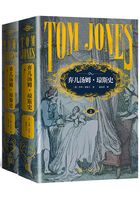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三章
哲学家斯侩厄先生和神学家斯威克姆先生的品格,兼及关于……的辩论。
这位绅士那时已经在奥维资先生宅里住了一些时候了,他姓斯侩厄。他天生的才能并不能算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却致力学问,以自策励,所以使原来的天赋大有进益。他深深沉酣于古代学者之中,并且公然自称精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得的全部著作。他就拿这两个伟人作榜样以培育自己,有时以此人之意见为归,又有时以彼人之意见为法;在道德方面,他自称为柏拉图的忠实信徒,在宗教方面,他倾向于做亚里士多得的私淑弟子。 但是,他虽然像我们说的那样,在道德方面,以柏拉图为楷模,而他在见解方面,却完全同意亚里士多得的看法儿,因为他有些以一个哲学家或思考家的性质看待那位伟人,而不是以立法家的性质看待他。
但是,他虽然像我们说的那样,在道德方面,以柏拉图为楷模,而他在见解方面,却完全同意亚里士多得的看法儿,因为他有些以一个哲学家或思考家的性质看待那位伟人,而不是以立法家的性质看待他。 他把这种思想感情推而广之,达到极远的地域,说实在的,及于非常远的地域,因而他竟认为,一切道德,都只是理论方面的事情
他把这种思想感情推而广之,达到极远的地域,说实在的,及于非常远的地域,因而他竟认为,一切道德,都只是理论方面的事情 。这一点,固然不错,据我所闻,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但是,只要对他的行动稍加一丁点儿注意,我就不能不认为,那是他的真正意见,因为这种意见,可以把他的品德中一些矛盾调和弥合,要不这样,矛盾就要冒出来了。
。这一点,固然不错,据我所闻,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但是,只要对他的行动稍加一丁点儿注意,我就不能不认为,那是他的真正意见,因为这种意见,可以把他的品德中一些矛盾调和弥合,要不这样,矛盾就要冒出来了。
这位绅士,只要和斯威克姆先生一见面儿,就很少不来一场舌剑唇枪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所信奉的主义,可以说像冰炭那样绝不相容。斯侩厄认为,人性本身就是一切道德最完美的结晶,罪恶只是人性脱轨离辙、旁行斜出,就像身体方面的骈拇枝指、驼背腆胸一样。斯威克姆和他正相反:他认为,人类的心灵,自从亚当堕落 以后,只是一个罪恶的秽薮污池,受了上帝的恩典,才能得到净化和解救。只在一点上,他们二人相同,那就是,他们在所有关于道德的长篇大论中,从来都不提一个善字。斯侩厄先生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类道德的自然美丽,斯威克姆先生所最喜欢的则是上帝恩典的神圣威力。斯侩厄先生老用一成不变的是之准则和永久长存的物之适宜,来衡量所有的行为
以后,只是一个罪恶的秽薮污池,受了上帝的恩典,才能得到净化和解救。只在一点上,他们二人相同,那就是,他们在所有关于道德的长篇大论中,从来都不提一个善字。斯侩厄先生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类道德的自然美丽,斯威克姆先生所最喜欢的则是上帝恩典的神圣威力。斯侩厄先生老用一成不变的是之准则和永久长存的物之适宜,来衡量所有的行为 ;斯威克姆则以权威,来判断一切事物;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却老引用《圣经》和《圣经》的注释,就像法学界对待扣克注利特勒屯
;斯威克姆则以权威,来判断一切事物;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却老引用《圣经》和《圣经》的注释,就像法学界对待扣克注利特勒屯 一样,注释和正文,有同样的权威。
一样,注释和正文,有同样的权威。
我作了这样简短的介绍以后,读者总会记得,那位牧师曾扬扬得意地用一句话,结束了他那篇演讲,荣誉能离开宗教而单独存在吗?他认为,这句话一定要问得人人张口结舌。
但是对于这句话,斯侩厄却作了回答;他说,总得先把所用的词语是什么意思确切地定下来,才能用之作哲学的讨论;他说,斯威克姆所用的那两个词语,在意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别的词语,能更含混、更模糊的了;因为关于荣誉,不同的意见之多,也几乎和关于宗教一样。“但是,”他说,“如果你把荣誉一词,当作真正道德的自然之美来讲,那我就可以主张,它可以脱离不管什么宗教,而独立存在。”“不但如此,”他又找补了一句说,“你自己就得承认,除了一种宗教而外,它可以脱离任何别的宗教而单独存在。这也是每一个伊斯兰教教徒、每一个犹太教教徒和世界上一切信仰各种教派的教徒,都要这样承认的。”
斯威克姆回答说,所有的敌人攻击货真价实之教会的时候,一般都怀着忌恨仇视之心。斯侩厄这种辩论,也是出于这种忌恨仇视之心的。他说,他不怀疑,认为世界上所有信异教的匪徒、持邪说的恶棍,如果他们能做得到,都要把荣誉限制在他们自己那种荒谬绝伦的错误和该遭天报的骗局之中;“但是,”他说,“荣誉可决不能因为人们对它有许多荒谬的意见,而就变得复杂多样,宗教也不能因为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教派和异端,就变得复杂多样。我说的宗教,是指着基督教说的;不但是基督教,是指着新教说的;不但是新教,是指着英国国教说的 。我说的荣誉,是指着那种不但和这种宗教一致,而且和这种宗教相依的神圣恩典说的。它和任何别的宗教都不一致,都无依赖。现在如果说我所指的这种荣誉,那也就是人们认为我可以认以为是的一切荣誉,会支持维护虚伪,那简直就是坚持一种使人惊讶得不可想象的荒谬见解,更不用说荣誉会扶持树立虚伪了。”
。我说的荣誉,是指着那种不但和这种宗教一致,而且和这种宗教相依的神圣恩典说的。它和任何别的宗教都不一致,都无依赖。现在如果说我所指的这种荣誉,那也就是人们认为我可以认以为是的一切荣誉,会支持维护虚伪,那简直就是坚持一种使人惊讶得不可想象的荒谬见解,更不用说荣誉会扶持树立虚伪了。”
“从我已经说的话里,结论是什么,明明白白地可以看得出来,”斯侩厄说,“所以我有意避免下结论。不过,如果你也看出了它的结论是什么,你可没打算对这个结论作答复。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先把宗教撂开,那我就认为,从我所说的话里,明显地可以看出来,我们对于荣誉,有不同的概念;不然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解释它的时候,不能使用同样的字眼儿呢?我坚持说,真正的荣誉和真正的道德,几乎是同义词,它们二者,都是基于一成不变的是之准则和永久长存的物之适宜的;虚伪和这二者是完全敌对的,完全相反的,因此毫无疑问,真正的荣誉是不能支持维护虚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两个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如果能说,这种荣誉是基于宗教之上的,那就不对了,因为荣誉实在是先于宗教的;如果说宗教可以说是任何积极性的法则——”
“我跟一个,”斯威克姆怒气冲冲地说,“说荣誉先于宗教的人意见相同!奥维资先生,你说我同意来着吗?”
他还要说下去,但是奥维资先生却拦住了他,很冷静地对他们说,他们两个都把他的意思误会了;因为他一直没提过真正的荣誉。但是,很有可能,他很难把他们两个的争论平息,因为他们现在都同样激动起来,如果不是现在发生了一件事,使他们把当时的谈话最后结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