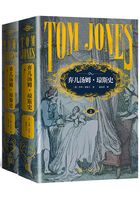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四章
包括的事件,道理深奥、情势严重,有的读者也许不能深得其味。
斯侩厄刚把他的烟斗点着了,马上就对奥维资先生开始如下的发言:“先生,我非得跟你道喜不可,养了这么个好外甥。像他这样的年纪,别的小伙子,绝大多数,除了耳闻目见才可得知的东西而外,别的一概不懂;他居然就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把任何东西拘禁起来,据我看,好像是违反自然的法则,因为按照自然的法则,每一样东西,都有享受自由的权利。这就是他说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是我永远也不能抉而去之的。任何人,还能更透彻地懂得是之准则和物之适合吗?我不能不对自己夸下海口,认为这个小伙子的一生,有这样的开端——破晓——那他一生的盛年——中午——一定要和老布鲁特斯或者少布鲁特斯 的盛年,并驾媲美。”
的盛年,并驾媲美。”
他说到这儿,斯威克姆连忙插上嘴去,因为慌张,把酒洒了好些,他把剩下的酒匆匆忙忙咽了下去,才开口说,“从他说的另一句话看,那我就可以希望,他能像更好得多的大人物。所谓自然的法则,只是几个叫人不懂的字眼儿凑在一起,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不知道,有任何自然的法则,也不知道,有任何是非,是依据于自然的法则而来。以欲人之施于己者施于人,一点儿不错,是基督教的出发点,像这孩子善说会道表示的那样。我看到我的教导结了这样的果实,实在高兴。”
“如果我们可以说虚荣算得一件有适合性的事,”斯侩厄说,“那我这一次就要以虚荣自居;因为他的是非观念,是从哪儿学来的,我认为很清楚。如果没有自然的法则,就不会有是非的分别。”
“怎么会是这样?”牧师说,“那么你这是连神的启示都取消了?我这是跟一个自然神论者谈话,还是跟一个无神论者谈话哪?”
“咱们传杯喝酒好啦!”威斯屯先生说,“又什么自然的法则啦,叫它见鬼去吧!你们俩胡吣的什么是啦非啦,咱可没听说过。据咱看,把我闺女的鸟儿弄飞了,就是不对,就是‘非’。我这位邻居奥维资先生可以照着他自己的意思,爱咋样就咋样。但是鼓励小伙子们干这种事儿,只能把他们教得走上绞刑台。”
奥维资先生回答说,他外甥做了这件事,他只有抱歉,但是要对他外甥加以惩罚,他可不能同意;因为他所以做了这件事,只是出于侠义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卑鄙的用意。他说,“如果这孩子偷了这只鸟儿,那我决不会后于任何人,一定主张要严厉地惩罚他一顿;但是事实分明,他并没有那种企图;并且,实在说起来也显而易见,这孩子除了自己承认的那种用意,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目的。”(因为像苏菲娅所疑心的那种成心冒坏,奥维资先生的脑子里,压根儿就连一次都没想过。)他后来结束他这番话说,这样的事只能埋怨他,说他想得不周到,还是只有小孩子做了这样的事,才可以饶恕。
斯侩厄刚才把话说得太绝了,所以如果现在他不再开口,那就等于承认,他的评判应该受到谴责了。因此他带着愠怒之情说,“奥维资先生对于财产权这种肮脏东西,考虑得太多了。我们对伟大、英勇的举动下判断的时候,一切细事末节,都得置之一旁;因为,要是固执坚守那类狭隘的法则,那小布鲁特斯就得被判为忘恩负义,老布鲁特斯就得被认为忍心杀子了。”
“要是他们因为那类罪行受到绞刑,”斯威克姆喊着说,“他们那只是罪有应得。他们是一对异教的恶棍。现在不出布鲁特斯这类的人,我们只有感谢上帝。我但愿,斯侩厄先生,你不要再往我这学生的脑子里灌输这种反基督教的胡言乱语了吧:因为他们在我的管教之下,我一定要把这类东西从他们的脑子里用鞭子抽出去。这个汤姆受了你的熏陶,已经惯得不像样儿了。我前几天,曾偶然听到,他对只有信心而没有行为、上帝就不施恩加惠 这句话,和卜利福少爷争论起来。我知道那是你的教旨之一,我认为那是他从你那儿学来的。”
这句话,和卜利福少爷争论起来。我知道那是你的教旨之一,我认为那是他从你那儿学来的。”
“你不要冤屈我,说我把他教坏了,”斯侩厄说,“教给他,教他笑话事物本性中一切合于道德、合于礼仪的道理的,是谁?教他笑话物性中的适合性、合理性的,是谁?他是你一手教出来的。我不承认他是我的学生。不错,不错,卜利福少爷才是我真正的门徒。他虽然年纪很轻,我可敢向你挑战,看你能不能把他对道德方面的正直看法,给他铲除了。”
斯威克姆对这句话,嗤之以鼻,表示鄙夷,同时回答说,“好啦,好啦,我一定敢把他交给你。他的善恶之念,已经扎根很深了,绝不是你那种哲学性的谎言假语所能影响的。不错,不错,我已经用心在意,给他灌输了那种原则了。”“我也曾把原则灌输给他,”斯侩厄喊道,“除了道德的崇高观念,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激发一个人慷慨的心胸,叫他给动物自由?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如果骄傲 可以算是物之适合的东西,那我就可以自认为我有灌输那种观念给他的光荣。”
可以算是物之适合的东西,那我就可以自认为我有灌输那种观念给他的光荣。”
“如果骄傲不是受到禁止的话,”斯威克姆说,“那我就可以自夸,说他自己承认的那种动机,就都是我教给他应尽的职责。”
“这样说来,是你们俩串通一气,”那个乡绅说,“教给那位年轻的绅士,叫他把我闺女的鸟儿给她弄飞了的了。我看我可得留神注意,好好看着我那养松鸡的笼子。要不价,就非有几个讲道德、信宗教的人什么的,把我的松鸡都给我放跑了哪。”于是他对当时在场的一个法界绅士背上一拍,喊着说,“大律师先生,你对这件事怎么个说法儿?难道这件事不算犯法吗?”
这位法界中人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如下发表了他的意见:
“如此案以松鸡之故,提起诉讼,则其受诉而得支持,当无疑问;因松鸡虽本只为ferae naturae ,但为人蓄养,使之驯化,则其物即变而为有人对之有权之产了。现此案只关一鸣禽,那就虽经人蓄养,且已驯化,但彼物既只属性质卑下,即须仅认为Nullius in bonis
,但为人蓄养,使之驯化,则其物即变而为有人对之有权之产了。现此案只关一鸣禽,那就虽经人蓄养,且已驯化,但彼物既只属性质卑下,即须仅认为Nullius in bonis 。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原告之控诉,可因不能构成诉讼而遭驳斥,以此我得建议,毋庸提起诉讼。”
。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原告之控诉,可因不能构成诉讼而遭驳斥,以此我得建议,毋庸提起诉讼。”
“好啦,”那位绅士说,“既然那是nullus bonus ,那咱们传杯喝酒,谈一谈国家大事,再不就谈一些咱们大家都懂得的话;因为你们这阵儿谈的,一点儿不错,是擀面杖吹火。我只晓得,那也许是学问,是知识,但是你们永远可不要劝我谈那个。哼!真正遭瘟!你们俩没有一个提到那个可怜的小伙子的,他才真叫是好样儿的哪。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帮我闺女,那才是侠义心肠的行为:我这点儿学问虽然不大,我可能看出来。他妈的!我这儿给汤姆祝寿啦!不管我活到多大年纪,我都要喜欢这个小伙子的。”
,那咱们传杯喝酒,谈一谈国家大事,再不就谈一些咱们大家都懂得的话;因为你们这阵儿谈的,一点儿不错,是擀面杖吹火。我只晓得,那也许是学问,是知识,但是你们永远可不要劝我谈那个。哼!真正遭瘟!你们俩没有一个提到那个可怜的小伙子的,他才真叫是好样儿的哪。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帮我闺女,那才是侠义心肠的行为:我这点儿学问虽然不大,我可能看出来。他妈的!我这儿给汤姆祝寿啦!不管我活到多大年纪,我都要喜欢这个小伙子的。”
当时的辩论,就这样中止。本来他们两个十有八九要马上又辩论起来的,但是奥维资先生却立刻吩咐套车,把这两位战士拥载而去。
这一只鸟儿的事件和鸟儿引起的一番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虽然是在我们这部史书现在达到的阶段,或者达到的时期以前好几年发生的,但是我却不能不对读者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