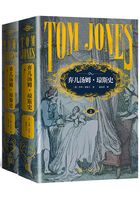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五章
包括一桩人人都可赏识的事件。
Parva leves capiunt animos——细微之行即足以动细人之心, 这是爱这种感情的大师
这是爱这种感情的大师 所表示的想法儿。而且还是一点儿不错,从那一天起,苏菲娅就开始对汤姆·琼斯生出一种由微而渐的友好之情,而对他的伙伴卜利福少爷,则生出一种绝不算小的厌恶之感。
所表示的想法儿。而且还是一点儿不错,从那一天起,苏菲娅就开始对汤姆·琼斯生出一种由微而渐的友好之情,而对他的伙伴卜利福少爷,则生出一种绝不算小的厌恶之感。
从此以后,不时地发生了许多琐事,都使她胸中这两种感情,有增无减。我们前此曾透露过,说这两个小伙子的性格如何不同,其中之一比那另一个如何和苏菲娅的心意更投机;从这些方面看,读者不用我说,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来。说实在的,苏菲娅在很小的时候,就辨别了出来,汤姆虽然是个心性散漫、胸无城府、举止轻率的小淘气鬼儿,但是除了和自己作对,却对任何别人都无敌意。 而卜利福少爷呢,虽然是一个审慎谨饬、见机识窍、稳健沉着的年轻绅士,却同时坚强不移地只顾单单一个人的利益。至于这一个人是谁,我想读者不用我们帮忙,就能揣测出来。
而卜利福少爷呢,虽然是一个审慎谨饬、见机识窍、稳健沉着的年轻绅士,却同时坚强不移地只顾单单一个人的利益。至于这一个人是谁,我想读者不用我们帮忙,就能揣测出来。
这两种性格不同的人,在世界上,各自应得的待遇,好像应该不同;人们为自己的利害起见,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好像应该不一样:但是事实却并非永远如此。不过这也许是运用手腕,不得不然;因为,人们找到一个真正以行善为乐的人,我们很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他们就如获至宝,也像对别的至宝一样,愿意留为己用。因此他们可以觉得,老夸扬称赞这样一个人,就等于俗语说的“高喊烤肉”, 而把打算自己专一使用的人,招来一些共同使用的人。如果这种解释不能使读者满意,那我们看一看,一个真正使人性大增光荣的人,或者一个真正对社会最有作为的人,一般人为什么对他绝少表示敬意?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但是苏菲娅却不像世上一般人那样。自从她懂得敬爱和鄙夷这两个词儿是什么意思那时候起,她就敬爱汤姆·琼斯,而鄙夷卜利福少爷。
而把打算自己专一使用的人,招来一些共同使用的人。如果这种解释不能使读者满意,那我们看一看,一个真正使人性大增光荣的人,或者一个真正对社会最有作为的人,一般人为什么对他绝少表示敬意?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但是苏菲娅却不像世上一般人那样。自从她懂得敬爱和鄙夷这两个词儿是什么意思那时候起,她就敬爱汤姆·琼斯,而鄙夷卜利福少爷。
苏菲娅有三年还多的工夫,离开了家,和她姑母住在一起;在这三年多里,这两位年轻的绅士,都很少和她见面。不过,有一次,她和她姑母都在奥维资先生家里做客赴宴。这时候离以前说过的那只松鸡事件刚刚发生了不几天。苏菲娅在席上听到全部的故事,当时并没说什么。实在说起来,连她回到家里,她姑母也没能从她嘴里听到多少话。但是她的女仆伺候她换衣服的时候,却碰巧说了一句,“我说,小姐,我想您今天看到卜利福少爷了吧?”她一听这话,带出气愤愤的样子说,“我连卜利福少爷这个名字都讨厌,就跟我讨厌不论什么卑鄙无耻、忘恩负义的事物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奥维资先生会让那个野蛮人一样的老塾师,那样残酷地惩罚一个可怜的孩子,只是因为他的心眼儿好,才做出那样一件事来。”她于是把始末根由,都对她的女仆说了,最后说,“难道你不认为,他是一个心胸高尚的孩子吗?”
这位年轻的小姐,现在回到了她父亲跟前;他在这一家里,叫她主持掌管一切,在他的宴席上,坐在宴席的上手, 在这种宴席上,汤姆(因为他爱好追猎,所以成了这位乡绅的爱宠)是常常参与的人。胸襟开朗、性情侠义的青年,往往有容易对妇女尽殷勤的天性,这种青年如果懂得情理,像汤姆确实不错地那样,对于一般妇女,都要以讨好于人、顺适其所欲的行动,表现这种殷勤。这一点,一方面使汤姆和那班言谈闹闹吵吵、举动粗俗野蛮的乡间绅士,显然有别;另一方面,也和卜利福少爷那样十分严肃、有些乖戾的态度,更不相同。他现在二十岁,开始在邻近一带的妇女中间,享有是个英俊秀美青年的声誉。
在这种宴席上,汤姆(因为他爱好追猎,所以成了这位乡绅的爱宠)是常常参与的人。胸襟开朗、性情侠义的青年,往往有容易对妇女尽殷勤的天性,这种青年如果懂得情理,像汤姆确实不错地那样,对于一般妇女,都要以讨好于人、顺适其所欲的行动,表现这种殷勤。这一点,一方面使汤姆和那班言谈闹闹吵吵、举动粗俗野蛮的乡间绅士,显然有别;另一方面,也和卜利福少爷那样十分严肃、有些乖戾的态度,更不相同。他现在二十岁,开始在邻近一带的妇女中间,享有是个英俊秀美青年的声誉。
汤姆对待苏菲娅,除了比对别的人更加敬重而外,并没有其他特殊之处。这种敬重,是她那样地美貌、富有、有卓越的见识、有和蔼的态度,本来应该受之无愧的;但是说到他在她身上转她的念头,他却决无此心。对于这一点,现在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读者贬抑他,说这是他太迟钝了;不过我们以后也许可以把这种情况,不卑不亢地解释一下。
苏菲娅是最天真烂漫、最谦虚恭谨的,但是在她的性格里,生动活泼之气,却极显著。这种情况,只要她和汤姆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更特别有增无减;如果不是因为汤姆年纪太轻,胸无城府,那他本来可以早就看出这一点来的;要不是威斯屯先生的心思,一般都贯注在田野、马棚或者狗窝上面,那这种情况也许会引起他的嫉妒的。但是那位好心的绅士,不但丝毫没有嫉妒之意,反倒给了汤姆一切和他女儿见面的机会,这种机会,无论哪一个讲爱情的人,都求之唯恐不得。这种情况,汤姆只凭他天生的那种义侠心肝和善良性格,在两小无猜的情况下,使之发展为良好作用;如果他对那位年轻的小姐,在脑子里深谋远虑地打她的主意,转她的念头,反倒不会做到那样了。
但是实说起来,这种情况逃出一般人的眼光,却并不足怪,因为可怜的苏菲娅自己,就从来没注意到这种情况;她那一颗心还没疑虑到自己身临危崖,就已经坠入了爱情的深渊,不能自拔了。
情势就处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一天下午,汤姆看到苏菲娅一个人在那儿,就先说了短短几句客气抱歉的话,然后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他有一件事,请她垂爱见怜,他希望,她那样仁爱,一定会答应他。
这个青年,无论在举动上,也无论在开始这件事的态度上,都没露出丝毫理由,可以让她疑心,说他打算对她求爱。但是自然是不是在她耳边上喳喳了几句什么话,还是另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不敢说一定;反正确实不错,那一类的念头,一定涌上了她的心头:因为她脸上失色,四肢发颤,并且她如果说话,舌头一定要嗫嚅难言。幸而汤姆的动作阻止了她,叫她先不必回答,因为他接着把他的请求提出来,才解脱了她的惶惑。他的请求是:求她关心一下那个猎守。他说,威斯屯先生要是继续下去告那个猎守的状,那个猎守自己和他那一大家子人,都非同归于尽不可。
苏菲娅马上由错乱中恢复了镇定,带着满是甜蜜的微笑说,“你那样郑重其事地要我开大恩、施厚惠的,就是这个吗?我一定用心尽力,替你办这件事。我自己就真正怜悯这个可怜的人;不多几天,就是昨天,还送了他太太一点儿小小的东西。”这点儿小小的东西,是她的一件长袍,几件内衣,还有十先令现钱。这件事汤姆先前已经知道了;实在说起来,就因为他知道了这件事,他才起意想到求她帮忙。
我们这位青年,现在看到事情这样顺利,更鼓起勇气,决定把事情更往前推进一步,就冒昧地求她把那个猎守推荐到她父亲名下;嘴里声称,他认为这个猎守,是这一带乡间最忠诚可靠的人中之一,做猎守的工作特别合适。那时很侥幸,威斯屯先生家的猎守,恰好出缺。
苏菲娅说,“好吧,这个我也诚心诚意替你办;不过我可不能答应你,说这个可以和头一件事,同样地成功。关于头一件事,我对你担保,我要老追我父亲,不满足要求,就没个完。不过,反正我要对这个可怜的人,尽力帮忙;因为我真心地把这个人和他家的人,都看作是该怜悯的对象。现在,琼斯先生,我也有一件事,要求你帮忙。”
“求我帮忙,小姐!”汤姆喊着说,“您要是知道,我从您那儿听到吩咐我的话,我是感到多大快乐,那您就会觉得,您只要说出来,那就是对我施了最大的恩惠了;因为,我指着这只亲爱的手起誓,我能牺牲我的性命,来为您效劳。”
他于是抓住了她的手,热烈地吻了一下;这是他的嘴唇头一次接触到她。她的血液,刚才离她而去,现在却足以补偿所失而有余,因为血液现在冲到她全部的脸上和脖子上,非常猛烈,因此她的脸和脖子,都显出一片鲜明的猩红。她现在第一次感到她以前还很生疏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她空闲的时候回忆起来,开始使她懂得了一些秘密;这些秘密,如果读者现在还没猜出来,那他们以后到了相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苏菲娅刚一到了能够说话的时候(这并不是立刻就能办得到的),就告诉他,说她求他帮忙的事是:她但愿他在逐猎的时候,不要把她父亲领到那么多的危险里去;因为,从她所听到的话里,他们每次一块儿出去逐猎的时候,她都十二分担心,唯恐不定哪一天,看到她父亲折腿断胳膊的,抬回家来。因此她求他,看在她的面上,要更小心,并且他既然知道威斯屯先生要跟在他后面,那请他以后,不要像疯了似的那样骑马,也不要做那样的跳篱越堑 。
。
汤姆答应了她,忠诚老实地遵守她的吩咐;跟着先对她答应帮他忙,表示了谢意,向她告别;心里因为这番成功,带着最大的欢欣喜悦离开了她。
可怜的苏菲娅,也感到极大的欢欣喜悦,不过她的欢欣喜悦,却是另外的一种。但是她那初恋所感受的新鲜奇异滋味,读者自己的心(如果读者的他或她有一颗心的话),能比我更好地表现出来,即便我有诗人曾经愿有的那么多的嘴,也说不过他们,至于诗人要那么多的嘴,我想,为的是能吃到供应给他的丰富多样的珍馐美味吧。
威斯屯先生的习惯是,每天下午,刚喝得醉醺醺的,马上就要他女儿弹拨弦钢琴给他听,因为他是一个大大的音乐爱好者,并且,如果他住在城里,那他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音乐鉴赏家了;因为他老反对汉得勒先生 最精妙的乐曲。他除了轻松、肤浅的音乐,任何别的音乐都不得其味;实在说起来,他最喜爱的曲调,就是《老赛门爵士》
最精妙的乐曲。他除了轻松、肤浅的音乐,任何别的音乐都不得其味;实在说起来,他最喜爱的曲调,就是《老赛门爵士》 、《圣乔治为英国》
、《圣乔治为英国》 、《蹦蹦跳跳的昭安》
、《蹦蹦跳跳的昭安》 ,还有一些别的。
,还有一些别的。
他女儿虽然十二分精于音乐,而且永远只喜欢演奏汉得勒先生的曲谱,而不喜欢任何别的,但是对她父亲,却曲意承欢,尽力投其所好。所以她学会了所有前面所举的那些曲调,以博其欢心。但是,她有的时候,却也尽力诱导她父亲,听一听她之所好;并且,她父亲要是叫她重复演奏那些民间歌曲的时候,她往往回答说,“别价,亲爱的爸爸”,而常常求他允许她演奏另外的曲调。
但是今天晚上,在这位绅士酒酣兴畅以后,她却没经她父亲恳请,就把所有他爱听的曲调,每样演奏了三遍。这样一来,把这位善良的乡绅,乐得不知所以,因此他从榻上跳起来,吻了他女儿一下,并且起誓赌咒地说,她演奏的技巧,大大地进步了。她就趁着这个机会,把她答应汤姆的事办了;她办这件事,非常成功,把那位乡绅支使得当时就说,她要是再给他奏一回《老赛门爵士》,那他第二天早晨就给那个猎守下委任。于是《老赛门爵士》奏了又奏,一直奏到音乐的魔力把那位绅士引进了睡乡。第二天早晨,苏菲娅决没忘记,提醒她爸爸答应她的话;他马上把他的代讼师叫来,吩咐他中止一切诉讼程序,同时拟好了一份委任书。
汤姆这件事的成功,不久就在乡间到处传扬开了;对于这件事的批评,各式各样全有。有人大大赞扬这件事,说那是义行善举;另有人就嗤之以鼻,并且说,“鱼结鱼,虾结虾,二流子交结二流子,何足为怪。”年轻的卜利福对这件事就大发雷霆。他一向就很恨黑乔治,他讨厌这个猎守,就像汤姆喜欢他一样。他所以恨他,并非由于乔治曾在任何方面得罪过他,而是出于他卫护宗教和爱护道德的诚心;——因为黑乔治有吊儿郎当、流里流气的名声。因此,卜利福少爷把这件事看作是当面给了奥维资先生一记耳光一样,并且咬牙切齿地声扬,对这样一个可恶的家伙做好事,不可能找出任何别的动机来。
斯威克姆和斯侩厄也随声附和,同唱一个调子。他们中,特别是斯侩厄,因为那个寡妇的关系,更加嫉妒起年轻的汤姆来;因为汤姆现在已经年近二十,真正是一个清秀俊俏的青年,而那位女士,看她给他鼓励那个劲儿,好像一天比一天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个清秀俊俏的青年。
奥维资先生呢,却一点儿也不为这类蜚言恶意所动。他声称,他自己对汤姆的行为举动,非常满意。他说,汤姆对朋友忠心耿耿,始终不变,直道而行,不屈不挠,大大地值得称赞。他但愿能多看到这种道德的事例才好。
但是命运却并不是永远赏识像汤姆这样嬉笑愉快的青年的(这也许是因为,这种青年,对命运并不特别热心讨好吧),现在它对汤姆的一切行为,都来了一个扭转,使那位善心的奥维资先生,远远不像从前那样,以可心的眼光,看待他的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