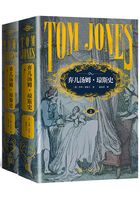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十一章
媢丽险中逃脱,同时我们做了一些深入人性的观察。
汤姆·琼斯那天早晨逐猎的时候,骑的是威斯屯先生的马,所以既然他在那个乡绅的马棚里没有自己的马,他只得步行回家;他这趟归程,走得仓皇急促,在半个钟头里,就跑了三英里多路。
他刚刚跑到奥维资先生外院大门前的时候,就碰到了保安吏和他那一伙人,要把媢丽押解到一个地方去;在那儿,低级人物可以学到一种教训,那就是说,他们对于比他们好的人,必须恭敬尊重;因为这个地方一定会明白指示出来,有两种人,一种得受矫正,一种则不用受矫正,而命运在这两种人之间,划分了绝不相同的区别。 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学不到,那我恐怕,他们在矫正所里,就很少能学到任何其他有益的东西,或者改善他们的道德。
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学不到,那我恐怕,他们在矫正所里,就很少能学到任何其他有益的东西,或者改善他们的道德。
一个法学家也许可以认为,奥维资先生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有一点儿越权逾分。要说实话,我也怀疑,他的处理,是否严格合于常规,因为在他面前,并没有正式的报告。但是,既然他的用意是真正刚正不阿,他应该在foro conscientiae 前面受到宽恕。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治安法官,随心所欲,胡乱判决案件,而他们并没有这种可受宽恕的情况,为他们辩护。
前面受到宽恕。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治安法官,随心所欲,胡乱判决案件,而他们并没有这种可受宽恕的情况,为他们辩护。
汤姆刚一听到保安吏告诉他,说他们要往哪儿去(其实他自己早就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马上就把媢丽搂在怀里,当着众人的面儿,温柔地把她紧紧拥抱,起咒赌誓地说,谁要是敢动手碰她一下,他就要了谁的命。他告诉她,叫她把眼泪擦干,把心怀放开;因为,不论她到哪儿去,他都要伴随她,跟她一块儿去。跟着他转到那个保安吏那面(保安吏正把帽子摘了,哆嗦着站在那儿),用一种柔和的声音跟保安吏说,他想要保安吏同他一块儿回到他父亲面前去一下(他现在就这样称呼奥维资先生了),因为他敢大胆地说,只要把他想替这个女孩子求情的话说了出来,那这个女孩子就可以无罪得释。
这个保安吏,我毫无疑问敢说,即使汤姆要求他把犯人交到汤姆手里,他也要照办不误的,所以一听现在这种要求,马上就答应了。于是他们就一块儿来到奥维资先生的厅堂里,汤姆告诉保安吏那一班人,叫他们在那儿先等一下,等他回来,跟着他自己就找那位善人去了。汤姆刚一找到他,就在他面前跪下,先求奥维资先生容许自己说一句话,跟着就承认,他自己就是媢丽肚子里那个孩子的爸爸。他求告奥维资先生,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发一下恻隐之心,同时请他考虑,如果这件事里,有犯罪的人,那主要承担这个罪名的,就得是汤姆自己。
“如果这件事里有犯罪的人!”奥维资先生有些愤然地说,“难道你已经成了一个放荡纵欲、淫秽成性的浪子,竟至于对犯了上帝和人类的法条,毁坏、糟蹋了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还怀疑是否有罪无罪不成?我毫不怀疑,认为这个罪名,主要应该由你承担,你犯的罪非常重,重到你得把它看作能够把你压成肉泥烂酱才对。”
“我不管自己的命运可以是什么样子,”汤姆说,“我只求替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求情能够成功。我承认,我糟蹋了她,但是她是否得受到毁灭,完全只凭您一句话。看在老天的面子上,爸爸,您收回成命,别把她送到一个无可避免地非把她一毁到底不可的地方去。”
奥维资先生叫他马上叫一个仆人来。汤姆说,没有叫仆人的必要;因为他侥幸碰到他们,现在他们都在厅堂里,专等听他老人家最后的裁决;他现在跪在地上,求他老人家给那个女孩子手下留情。他求奥维资先生把这女孩子放回家去,待在他父母身边,不要叫她再受更多不必要的耻辱和轻藐。“我知道,”他说,“我这是要求得太过分了。我知道,我是这场灾祸的根由。我要努力补过,如果可能的话;要是您能从此以后宽恕了我,我想我一定能不辜负您的好意。”
奥维资先生迟疑了半晌,后来到底说,“好吧,我把我下的逮捕状取消了。——你叫保安吏到我这儿来。”汤姆马上把保安吏叫来,奥维资先生把他打发走了,也把那女孩子打发回家去了。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奥维资先生一定不会不因为这件事而严厉地训斥汤姆一番的。但是我们无须把这番训斥之词写在这儿,因为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卷里把他训责珍妮·琼斯那番话,如实地记录下来了。那番话的绝大部分,可以应用到女人身上,也同样可以应用到男人身上。这番训斥,对那个青年,起了强烈的作用,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所以他回到自己屋里,独自一夜未眠,极尽抑郁地琢磨这件事。
琼斯做了这回罪犯,把奥维资先生气得很可以了;因为,虽然威斯屯先生说了奥维资先生那番话,毫无疑问,奥维资先生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却从来没跟女人有过任何放荡的行为,同时对于这种放情纵欲的人,极为痛恨。说实在的,很有理由想象威斯屯先生所说的话,没有一丁点儿是真的,特别是他把他们非礼失德的地方,说成是在大学里,而奥维资先生从来没上过大学。事实是,那位善良的乡绅未免有些好作一般叫作是悠谬之说、荒唐之言、无端之辞,海阔天空、云山雾罩地开一回玩笑;不过这个悠谬、荒唐,也可以极合适地用一个简短的词儿表示。 我们也许得说,我们用别的说法儿,来代替这个短词的时候,可就太多了;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往往被认为工于戏谑,速于应对的警策隽语、敏捷谐词,如果用严格纯洁的语言表达,就都应该使用一个简单的字
我们也许得说,我们用别的说法儿,来代替这个短词的时候,可就太多了;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往往被认为工于戏谑,速于应对的警策隽语、敏捷谐词,如果用严格纯洁的语言表达,就都应该使用一个简单的字 就成;不过,这个字我在这儿,按照娴文识礼的习惯,略而不书。
就成;不过,这个字我在这儿,按照娴文识礼的习惯,略而不书。
但是尽管奥维资先生对于这件坏事,或者对于任何别的坏事,极端厌恶,他的眼睛却并没因此而瞎到一种程度,竟至于连这个罪人的长处一无所见,也就和他对这个人的坏处,并不至于一无所见一样。因此一方面,他对琼斯的淫荡放浪,非常生气;另一方面,又因为他那样讲荣誉,爱诚实,作自我控诉,又同样地喜欢他。现在他心里对这个青年的意见,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能想象得出来,在衡量他的功过优劣的时候,功与优好像更有分量。
因此,斯威克姆听到卜利福少爷马上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他以后,虽然把深恨毒怨,一齐向汤姆发作,但是并无效果;奥维资先生很耐心地听了他们所有的控诉,听完了冷静地回答说,像汤姆这种脾气的年轻人,一般都非常容易犯这种毛病;但是他相信,这个青年,听到训他的这次话,会真正受到感动。他只希望,汤姆不会再犯这种罪过。这样一来,既然执行鞭笞的日子已经结束,那位塾师除了嘴而外,就没有别的出路,可以发泄他的怨气,而嘴则是无能为力的报复平常的归宿。
但是斯侩厄,虽然不像斯威克姆那样性情暴虐,却更工于心计;同时,因为他恨琼斯,也许比斯威克姆更厉害,所以他想方设法,在奥维资先生心里,给他酿成更多的祸殃。
读者一定还记得那几件小事,像打松鸡、卖马、卖《圣经》等等,这都在本书第二卷里说过了。琼斯由于这些事件,在奥维资先生对他喜欢加以疼爱那方面,不但无所损失,反倒有所增长。我相信,任何别的人,只要懂得什么是友谊、侠义、高尚,那也就是说,只要心里有半颗善良的种子,奥维资先生也都要给以同样的待遇。
斯侩厄也知道,这几种优点,在奥维资先生那颗善良的心里,都印上了什么真正的印象;因为这个哲学家很懂得什么是道德,虽然他也许追求道德不太坚定。但是斯威克姆的脑子里,却从来没这样想过,至于为什么,我先不必说明;他完全从阴暗的角度看待琼斯,他认为奥维资先生,也从同样的角度看待他,而只是由于心地骄傲、心性顽固,才下决心,不要把他一度爱护的孩子,一下甩开;因为他要是不那样,那就等于暗中承认,他从前对他的疼爱,都是错误的了。
斯侩厄因此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琼斯最易受害的方面,设法儿把他中伤,把从前说过的那几件事,一律说成了是出于坏心恶意。“我很难过,先生,”他说,“不得不承认,我也和您一样,都受了欺骗。我得承认,我对于我认为凡是出于友谊的动机而作的一切行为,都不由得要感到高兴,虽然那种行为太过分了;不论什么事,只要一过分,就都是有错误、有毛病的: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因为有这种行为的人年纪还轻,所以加以原谅。我一点儿也没料到,原来那一次那小伙子以牺牲真相为代价,我们两个同样都认为是出于友谊,可实在是滥用友谊的名义,以实行败坏、淫乱的嗜欲。您现在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出来,这个青年,对那个猎守一家好像侠义的行为,都是从何而来?他救济父亲,以便腐蚀女儿;他使这一家人免于饥寒,可使其中之一陷于耻辱和毁灭。这就是友谊!这就是侠义!理查·斯梯勒爵士说得好,饕餮出高价买精肴美食,真足以称得起是侠义慷慨! 一句话,我见到这件事例,就下定决心,在人性中的弱点面前,永远不再退却让步;对于一切事物,凡是不完全合乎天经地义的是之准则的,也永远不以道德视之。”
一句话,我见到这件事例,就下定决心,在人性中的弱点面前,永远不再退却让步;对于一切事物,凡是不完全合乎天经地义的是之准则的,也永远不以道德视之。”
奥维资先生因为心肠太好了,自己不会有这类考虑;但是有别人在他面前摆出道理来,那这种考虑就理由太充足了,不应该不经细想,就完全加以排斥,居然加以拒绝。说实在的,斯侩厄这番话深深地印入他的内心,他心里由这番话引起的踧踖忸怩,对那另一个人明显可见。但是那个善良的人,却没承认这一点,只对那个人的话,非常轻描淡写地做了唯唯否否的答复,硬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这类提示,并不是在汤姆受到宽恕以前做出来的,这是可怜的汤姆侥幸的地方;因为这番提示,一点儿不错,使奥维资先生心里第一次印上了琼斯的坏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