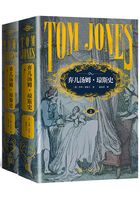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十章
副牧师色浦勒说的故事。威斯屯乡绅的明鉴。他对女儿的疼爱,他女儿对他的回报。
第二天早晨,汤姆·琼斯和威斯屯先生一块儿追逐狩猎,猎毕归来,那位绅士邀请琼斯同进正餐。
可爱的苏菲娅那一天比平素更艳光辉耀,显出欢愉活泼的丰姿。她摆下的柳营花阵,毫无疑问,都是要围攻我们这位男主角的,虽然,我相信,她自己的用意所在,她几乎还茫然昧然;但是,如果她有任何意图,想要使他心迷意惑,那她这次取得了成功。
色浦勒,奥维资先生那个教区上的副牧师,也是正餐在座的人之一。他这个人,脾气和善,品格端方,但是他在宴席之上,却以特别缄默为其主要特点,虽然他在那儿,他那张嘴绝无投闲置散的时候。一句话,他身居世界上口腹之欲最为强烈的人之列。但是,桌布刚一撤走,他就立刻把刚才所保持的缄默急忙打破,以作补救;因为他的为人,嘻嘻哈哈,兴致勃勃,他谈的话总是引人入胜,从不出口伤人。
他的大驾刚一光临的时候,恰好在烤牛肉端到席上之前,他曾当众公布他带来了新闻,还正要开口说他怎样刚从奥维资先生那儿来;但他看见烤牛肉一端上来,就一下呆住,口不能言,只给了自己做饭前祈祷的工夫;同时说,他得先对“牛立即”先生立即光顾,因为他就这样称呼牛里脊。
正餐吃完了以后,苏菲娅提醒他,问他的新闻到底是什么,他就开口如下说道:“我相信,小姐,您昨日在教堂做礼拜晚祷的时候,一定见到一个青年女子,身着您赠她的一件稀奇服装;我记得我曾看见小姐您穿过那样一件衣服。不过,在乡野之地,那样的服装是
Rara avis in terris,nigroque simillima Cygno,
这就等于说,小姐,
世上稀见之鸟,直如黑色天鹅。
此诗见于朱芬奈勒。不过,我现在得闲话少叙,言归正传。我刚才正说到,此种服装,在乡曲之地,直属罕见;而且他们再一看,着此服装者究为何人,则或有人认为更加稀罕。他们告诉我,此女青年为黑乔治之次女;黑乔治为老爷您的猎守,我窃认为,彼人既受到那样苦难,极应从中吸取教训,更明事达理,而不应把他的丫头,用如此炫耀之服装,修饰装扮,才合情理。他这个闺女,在会众中间,惹起那样一番骚乱,苟非奥维资先生出而震慑压服,礼拜即遭他们搅扰,无法进行;因我作第一段朗读的中间, 确曾一度作要中止礼拜之想。即使如此,在礼拜完毕之时我归家以后,他们在教堂坟地里,仍然大打出手;在这场斗殴中,其他受伤之人暂且勿论,有一穿乡游巷之提琴手,头被打破数处。今日晨间,此提琴手来到乡绅奥维资先生面前,请求发出拘票,因此把那个女人传到。奥维资先生本意想给他们两下和解了事;但未想到,正当其时,那个女的(我请小姐您恕我有渎清听),看样子,打比喻说,正临生私生子的前夕。乡绅问她,何人为此私生子之父。但她咬定牙关,不作任何回答。因此,奥维资先生正欲签令状,送她到布莱得维勒去。此时,我即离他而来此地了。”
确曾一度作要中止礼拜之想。即使如此,在礼拜完毕之时我归家以后,他们在教堂坟地里,仍然大打出手;在这场斗殴中,其他受伤之人暂且勿论,有一穿乡游巷之提琴手,头被打破数处。今日晨间,此提琴手来到乡绅奥维资先生面前,请求发出拘票,因此把那个女人传到。奥维资先生本意想给他们两下和解了事;但未想到,正当其时,那个女的(我请小姐您恕我有渎清听),看样子,打比喻说,正临生私生子的前夕。乡绅问她,何人为此私生子之父。但她咬定牙关,不作任何回答。因此,奥维资先生正欲签令状,送她到布莱得维勒去。此时,我即离他而来此地了。”
“博士,一个女人要养私孩子!你的全部新闻就是这个吗?”威斯屯先生喊道:“我还只当你的新闻是跟大家伙儿的事儿有关系的,是国家大事哪。”
“我只怕国家大事,太属平常,”那位牧师说,“但我认为,此新闻全部颇值一叙。至于国家大事,老爷您知之最详。我所关心者,为不出我教区之事。”
“哦,唉,”那位乡绅说,“我相信,国家大事,我倒是知道一点儿,像你说的那样。不过,汤姆,来呀,传杯呀;怎么酒瓶到你手里就不动窝儿啦?”
汤姆请求先走一步,因为他有点儿特别的事儿,跟着就从桌旁站起;乡绅一把没揪得住他(因为乡绅本来站起来,要拦阻他),他连什么是礼节都不顾,就一溜烟儿走了。
乡绅因为他走了,咒骂了他一句,跟着转身对牧师喊道,“我瞅出门道来了,我瞅出门道来了。汤姆——准是这个私孩子的爹。哼哼!妙哇!牧师,你还记得他怎么把这个丫头的老东西引荐给我的吧。好不要脸的骚货!多有心眼儿的狐狸精。唉,唉,绝没有错儿,绝没有错儿,汤姆不是这个私生子的爹,你就把我揍匾(扁)了。”
“果真如此,我即一心为之难过惆怅。”牧师说。
“这有什么可难过的,”乡绅喊道,“这算得什么不得了天塌下来的大事?你闹什么把戏?我可认为,你这是打马虎眼,假装你从来没生过私孩子啊。算了吧!你那是太走运了!因为我敢保,你说过‘因此’ 等等,绝不止一回两回,而是数不清、道不明的次数了。”
等等,绝不止一回两回,而是数不清、道不明的次数了。”
“老爷您这是戏言吧,”牧师回答说,“不过我不但对此种行为中之罪过错误,大张挞伐,固然那是绝对应谴责的,我还唯恐,他此次丧德违法之行为,要使奥维资先生对之大失欢心。据实而言,此青年虽性格如无笼头之野马,然而我可从未见他做过损人利己之事,也从未闻他做过损人利己之事,除老爷您现在对我说的这一种。我所愿者,是做礼拜之时,他之应答, 能更多少合于规矩;但总而言之,此青年似
能更多少合于规矩;但总而言之,此青年似
Ingenui vultus puer ingenuique pudoris.
此乃一行古诗,小姐,译为英语则其意为:‘此一孺子,有一副天真质朴之面目,兼有一种天真质朴之谦恭。’因此种美德,在罗马人与希腊人中,极受重视。我定须称道者,此年轻绅士,(因其人虽出身微贱,可我以为,仍应以此称之。)此年轻绅士,据我所见,实为一极谦恭而温良之孺子;苟其人在奥维资先生之心中失欢见罪,将不利于此孺子,我唯有为之惆怅。”
“瞎说!”乡绅威斯屯说,“失欢见罪,在奥维资跟前,你说;难道奥维资先生自己就不喜欢女人了吗?不是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汤姆是谁的儿子吗?你只能对别的人说这一套,对我说可不灵。我可记得奥维资上大学那时候的光景。”
“我以为,”牧师说,“他就从未迈过大学之门槛。”
“迈过,迈过,他迈过,”乡绅说,“那时候,有好多小娘们儿,都是我们两个人伙着的哪。在方圆五英里以内,他也跟别人一样,好跟女人胡缠的名儿可大啦。这不算什么,决不算什么。他不会因为这个发火儿,你放心好啦;他对不管什么别的人,也不会因为这个就发火儿。你问问苏菲——你会因为一个小伙子弄出私孩子来,就看不起那个小伙子吗?会吗,孩子?不会吧,不会;女人家有的反倒因为那个,更喜欢那种小伙子哪。”
这个问题,对于可怜的苏菲娅,正是扎耳刺心。牧师说这件事的时候,她曾看到,汤姆脸上吃惊失色,那种情况,再加上他突然匆匆走开,让她想到,很有理由,认为她父亲的疑心,并不是没有根据。这种隐情,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地露出苗头来了。这种隐私,现在一下在她心里豁然呈露;她只觉自己对于这件事,大大地关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她父亲那样粗鲁莽撞地向她提出来的那个问题,蓦然上了她的心头,使她露出一些形迹来,叫一个好生疑心的人看着,一定要大吃一惊。但是,我们对这位乡绅,得说公道话,却并没有这种毛病。因此,她从她坐的椅子那儿站起来,嘴里说,只要她看到他一有叫她离开的意思,那她一定可以退席;所以那时候,他就让她离开那个屋子了;于是他脸上带着郑重其事的样子说,“能看到一个女儿谦虚太过,也别看到一个女儿张狂太过。”——这种思想感情,大受牧师称赞。
现在跟着来的,是乡绅和牧师二人之间一场最精彩的政治评论,从报纸和政论小册子穿插而成;在这番评论中,他们牺牲了四瓶葡萄酒,作为庆祝国家兴盛的贺礼,跟着乡绅就大睡而特睡起来。牧师于是点起烟袋,骑在马上,回家而去。
乡绅那半个钟头的打盹睡足了以后,他叫他女儿来给他弹拨弦钢琴,但是她说那天晚上恕难侍奉,请求免役,因为她的头疼得厉害。这种请求,当然马上得到准许;因为,说实在的,她就很少有作两次请求的时候;本来,他对她热烈疼爱,所以他准许她的请求,使她满意;通常他也从这种满意中,自己大大享受到满意。她实在是他的宝贝疙瘩,像他叫她那样;她也真应该受到这种疼爱,因为她回报他的疼爱,是无边无涯的。她在一切事情上,都把她对她爸爸应尽的一切天职,完全尽到;这种情况,由于她对她爸爸疼爱,她不但很容易就能做到,并且还以此为乐;因此,她有一位朋友笑话她,说她把这样丝毫不苟服从老父这件事(像那个年轻的女士说的那样),看得太重了,苏菲娅回答她说,“如果你认为我因为这个而自鸣得意,那你就把我看错了;因为除了我只是尽我应尽的职分以外,我自己还从这里面感到乐趣。我可以诚恳地说,我没有别的乐趣,能赶得上使我爸爸快活的了。如果我有重视自己的地方,我的亲爱的,那是因为我有以孝父为乐这种能力,而不只是因为我能使这种能力见之实行。”
但是可怜的苏菲娅那天晚上,却不能尝到这种快乐。因为她不但请求她爸爸,不要叫她弹拨弦钢琴,还同样请求允许她,也不要吃晚饭。对于这个请求,那位乡绅也答应了,虽然并非没有略表不愿的意思;因为他很少允许她不在他的眼前,除了他和猎马、猎狗和酒瓶打交道的时候。尽管如此,他还是顺从了她女儿的意愿,虽然那个可怜的人,此时不得不避免和自己做伴(如果我非这样说不可的话),而请了一个邻居农民,来和他同度长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