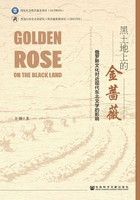
二 东北地区中俄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与俄罗斯文化的传播
中俄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和交往传统。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两国之间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13~14世纪的元朝,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则指出,中俄交往史可能要更早一些。据《元史》记载:至顺三年(1322年)“诸王章吉献斡罗思百七十人,酬以银七十二铤,钞五千锭”。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一词是蒙古人对Poccия一词的翻译,汉语则是借用了蒙古文的译音[12]。根据文化传播学原理,两种文化形态的中心区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差异,而其边界处则大多是模糊的、重叠的。基于这一原理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在东北亚的交界处于两国的文化边疆地区,在这一地区探讨俄罗斯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东北地区虽是中华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带有鲜明的东北区域文化的特色,体现为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兼容并蓄。按照中华文化区的划分,它被称为胡文化区;从经济文化类型说,它属于渔猎、采集、狩猎三位一体的北方新型文化复合体。因此,东北区域文化是一种中华文化的边缘文化类型。这种边缘文化受中原文化发源地的影响较微弱,其对发源地文化的认同感也相对要弱些。与之相应,俄国的远东地区同样也是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的边缘地带,本来俄国就不属于西方文明的成员,其远东地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就更小,这就使得该地区的文化特征较多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本色,这一点与中国东北区域文化十分接近。可以说,“北方游牧民族在不只一个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而文化特征的某一方面比较接近的民族间的融合或地域性融合显然相对要容易”[13]。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东北地区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具有先天的优势的。
不过这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优势由于这一地区的地广人稀、不为统治者所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发挥出来。直到清代中前期,主要是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署以后,双方边贸才逐步发展。在黑龙江地区,俄国不断派商队前来齐齐哈尔从事贸易活动,以双方邻近居民间互通有无为特征的“互市”贸易发展迅速。不过这一时期的中俄文化交流并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如果说《尼布楚条约》尚是一个能让中俄两国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的关于领土划分的平等条约,那么后来的《中俄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让东北的版图发生了令人心痛的变化。从1849年到1852年,在沙俄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沙俄武装分子对阿穆尔河沿岸和阿穆尔河河口实施了武装占领,随后又占据了库页岛。至1858年和1860年英法两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胜中国以后,沙俄政府又趁机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俄国从中国东北地区获取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实际上,这两个条约只是对沙俄武装分子占领这些领土在法律上的确认。
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领地增加了一块像除俄罗斯帝国外的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地盘,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14]沙皇尼古拉二世上台以后,其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日俄战争中的俄军满洲总司令)在日记中说得很露骨:“我们皇上的脑袋里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计划”,沙俄从各方面加紧了准备。而根据中俄两国在1896年签订的《中俄密约》,俄国人将在中国东北地区修筑和经营一条铁路,史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或中东铁路。之后,清政府又和沙俄签订了《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1900年中国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中,俄国获利最多。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俄国占29%,达1.3亿两,比其他列强都多。条约签订后,俄国又趁机派兵入侵中国东北,企图将该地区变成俄国的一部分。当时,部分沙俄人士已狂妄地将中国东北称为“黄俄罗斯”,说俄罗斯既然有“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可以有“黄俄罗斯”。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国东北地区才由俄国独大变成日俄对峙。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十月革命爆发,中俄东部边疆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俄罗斯对中国东北的征服这一形式进行的,带有强制性和不平等的性质。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疏于开发和长期封禁造成该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这给正在努力寻求近代化的俄国提供了一个拓殖领土、掠夺资源、加速原始积累的良机。于是,以《瑷珲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中俄密约》(1895)、日俄战争、中东铁路等为标志的强制性的“文化交流”在中国东北地区全面展开。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的传入主要有三种方式:军事入侵、传教、移民。军事入侵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碰撞,新式教育的创办、新式学堂的发展、边疆文学的产生、文化设施的建立、新闻报业的出现等都是这种碰撞的具体体现。传教士也伴随着军事入侵深入到中国东北地区腹地。中东铁路在东北的修建,使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达到了一个高潮。中东铁路的修建给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决定修筑横贯东北的西伯利亚铁路时,俄财政大臣维特即宣称,该铁路是一项“世界性事件”,它“开创了各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常常引起各国之间既定经济关系的根本变革”[15]。中东铁路的修建使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突然出现了许多俄国人,其中尤以哈尔滨为甚,哈尔滨在短期内迅速发展,甚至一度成为远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毋庸置疑,沙俄修建中东铁路的本质是为其掠夺中国东北的商品和资源提供便利条件,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19世纪90年代,沙俄已经完成了对外战略的转变,确定了向远东扩张的政策,加之俄国在远东缺乏经济竞争能力,生产和贸易水平极为有限,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经济目的是次要的,军事目的才是主要的。中东铁路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末端,其修建完成使得沙俄加强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优势,对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实现了压制。从中东铁路上调运战备物资,远比从海参崴经由日本海进入中国的渤海节约成本。把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延伸,将外贝加尔地区与俄国在远东海参崴的海军基地连接起来,这是沙俄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不可缺少的环节。中东铁路的修筑使俄国在铁路沿线主要是哈尔滨能够建立起一整套殖民体系,给中国的国家主权及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痛苦,其罪行罄竹难书。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深刻揭露和谴责,这也是分析问题时必须明确的前提。
1903年12月26日的《俄事警闻》中有一则信息是这样写的:“华人在哈尔滨者,以山东籍居多。近因屡受俄人压制,负屈含冤,无所控诉,中国官吏,惟知仰俄人鼻息,不能为商民伸冤,故拟设一保会,以期守望互助,不复受俄人之压制云。”[16]《大陆》杂志1905年第7号写道:“近来‘马贼’横行于东三省各处,实足挫俄军之势力,闻有‘马贼’称曰‘爱国马贼’,其中一队横行于新民屯附近,彼自称为东亚爱国马贼之凯旋队,均有新式之枪械,在各处遇见俄人,即袭击之。”[17]从这两则引文可以看出,当时的清朝官吏对俄国人唯唯诺诺,不敢保护本国人民的权益,下层民众饱受欺压,因此民间的反抗运动就必然产生了。
而1904~1905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则是近代中国、近代东北历史上最屈辱的一页。对于日俄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旨在争夺东北的战争,腐朽的清政府竟于1904年2月13日发布所谓“中立”的上谕:“现在日俄两国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又于同日颁布了《日俄战争中国严守局外中立条规》。这种“中立”,无异于卖国。当时的滇督抚即认为:“俄日相持,瞬将开战,中国势处两难,无论俄胜,中国困将不堪;即日胜,中国亦必被侵浊。且俄日即和,而东三省不得主权,亦从此无以立国。”[18]日俄战争使东北人民饱受涂炭。1904年春,库罗帕特金到远东统帅俄军前,曾对清政府驻俄公使声称:“我此去驻军,倘中国官民有犯我军政者,在民即杀无赦,在官则十分钟内必加禁锢。”[19]辽宁是日俄火并的主要战场,仅盖平县受灾就达214村,被毁良田43607垧。据1912年辽宁省档案《关于潘云庆赴俄索款之讯办案》披露:“日俄之战,俄军当败北时,由旅大及东边一带,仓猝之间,沿路所经之地方,无不被其损害。尤有甚者,莫如奉天府、辽中等州县,竟至死亡山积,十室九空。”[20]在旅顺要塞内,东起白银山,北至东鸡冠山,西至水师营,西南至羊头洼,房屋全被扒掉炸毁。其中吴家房村仅剩5间房的残垣,以至当地居民战后将其改名为五间房村。在这场战争中,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被视如草芥。苏联作家斯捷潘诺夫的长篇小说《旅顺口》记录了这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进行的为控制远东战略经济区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小说批判了沙俄政府的腐败、贵族军官的无能,赞扬了俄罗斯士兵的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然而在小说中,作为土地主人的中国人却被无视了,偶有出现,也是充当日军间谍、妓女等角色,这反映了斯捷潘诺夫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侵略思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事实并不是总能让人快乐的,正视历史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胸怀和气魄。这种胸怀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遭受的屈辱和为恢复正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同样我们也要看到,历史进程不是以某些民族的意志为转移的。应该承认,中东铁路工程的进展及随后的经济开发,尤其是因之产生的几次移民浪潮,客观上刺激了东北地区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催生了近代林业、矿业和航运业等,促进了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近代的城市化进程。而在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苏俄人民也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作家白朗曾在日记中提到她流亡关内时遇到两位视察阵地的苏联顾问,她热情地写道:“他们都是苏联有名的军事家。他们到中国来,不避艰险,不辞劳苦,整日在前线出生入死地奔波着,这伟大无私的精神,这真挚崇高的友情,有心人能不铭刻于心吗!”[21]
从传教方面看,一般来说,人们普遍把17世纪雅克萨之战中的俄军战俘的归化,看作俄国东正教传入中国的开端。[22]19世纪末,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经营,东正教传入中国东北。据统计,“从1898年在哈尔滨修建圣尼古拉教堂开始,到1923年,沿中东铁路一线,已有38座东正教教堂”[23]。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沙俄在建设中东铁路期间所进行的宗教活动并不是以传教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俄国信众服务的。在中东铁路修建之初,俄罗斯东正教在东北地区的活动是中东铁路的附带品。而随着大量俄罗斯人流入中国东北,东正教的传播也活跃起来。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在哈尔滨的东正教主教、司祭们依附于塞尔维亚俄国东正教教廷,成立了‘哈尔滨独立教区’。在广建教堂的同时,俄国人还广播教义、广收教徒,东北地区在1898年尚只有几百名教徒,而到1922年哈尔滨教区建立时,骤增到30万人”[24]。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教区升为远东总主教区。1945年10月,东正教哈尔滨教区加入莫斯科全俄正教会。1956年10月,哈尔滨东正教会归属中华东正教会。直到今天,东北境内仍有不少东正教堂遗迹和教徒。
由此可见,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播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东铁路修建时期,神职人员来到东北为铁路员工提供精神抚慰。第二阶段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高尔察克在奥姆斯克政权的崩塌,以及弗兰格尔、邓尼金等势力对红色苏维埃的武装干涉,有大批神职人员随同难民流亡到中国东北。据霍特科夫斯基回忆,来到东北之初,“俄罗斯神父们很少向中国人传教,除了语言不通外,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有自己的崇拜偶像,如极乐寺中的大佛和中国土著宗教的神祇。但中国人会用好奇的目光注视东正教教堂中的俄侨祈祷仪式,有时把上帝和佛祖混为一谈”[25]。但到20世纪30时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侨民的迅速增多使教堂数量也跟着增加了,而教堂的费用除了神职人员自筹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众的供养。对神职人员来说,扩大信众范围本身就是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座教堂成功与否的标志,因此才有了哈尔滨独立教区的都主教涅斯托尔所说的全面发展中国信众的“新思维”。
俄罗斯文化通过移民方式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化现象。谈到文化传播的主体——移民,可以分为两种亚类型,其中一种亚类型的主体是旅俄归国的华侨及其子女,另一种就是来到东北地区的俄罗斯人。[26]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开禁放垦,大批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北上进入这一地区。90年代,伴随着俄罗斯移民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一部分汉族移民继续北上,越过边界,进入俄境。或者从山东乘船直接进入俄罗斯在远东的天然良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27]。像闯关东一样,中国人管进入海参崴叫闯崴子。据统计,1900年海参崴共有旅俄华人36700人。中国人进入俄罗斯还有一种情况,即随着西伯利亚的开发,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俄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仅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中东铁路公司就招募了10万华工。他们除一部分留在中东铁路做工外,大部分人则进入西伯利亚,特别是远东地区。到1910年9月,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工已达111466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政府招募华工迅速升温。到十月革命爆发前夕,旅俄华人已达40万人”[28]。“生活在俄罗斯的华人受周围大文化环境的影响。逐渐学会了俄语,生活习惯也已大半俄罗斯化。他们中的一部分娶俄罗斯女子为妻,所生子女的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十月革命后,旅俄华侨及其子女大部分回到国内,特别是东北地区,由此把俄罗斯文化带入这一地区。”[29]
华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02年,俄罗斯军事记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到海参崴采访,描述了他对中国人的印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群群中国工人在僻静而遥远的街上步履蹒跚,在斯维特兰娜大街,则是买卖人、官员和军官。听得到夹杂着德语和英语的俄语,并被中国人的粗大嗓门所打断。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的‘黑工’和‘百姓’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市场上做生意,中国人在火车站背东西,中国人是马车夫、船工、送水工、面包师、屠夫、厨师、裁缝、鞋匠、装订工、制帽师傅。只有载客马车夫是俄罗斯人。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位女士对我说:‘中国人在这里所做的最大的恶行就是他们一下子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比战争还糟糕,我们会死去。’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的确,娇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女士不得不下厨房,海关官员或其他人不得不自己提水桶、补靴子以及修补办公厅最需要修缮的地方。”[30]正是由于在海参崴的俄罗斯人、中国人以及朝鲜人等的辛勤劳动,海参崴逐渐繁荣起来,由要塞变为城市,成为俄罗斯在远东的重镇。中国人参与建设的许多建筑,诸如1912年竣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成为该城的名片,被命名为俄罗斯联邦级的建筑纪念碑。
中国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许多领域都起了关键作用,在整个沙俄政权时期和苏联时代初期,中国劳动力被广泛使用,直到1938年中国人被大规模驱逐。许多最重要的国家项目的实施常常取决于中国劳动力的参与,而这些项目不但巩固了俄罗斯在东部边疆的实力,而且足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川流不息。中国人特别多,与天朝帝国的子民们相比,俄罗斯人很少,或者几乎看不到。”1897年,Д·И·施罗德在他的著作《我们的远东》中写道:“就在我最初到达我国太平洋边区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听到当地居民描述中国人对于这个年轻的刚开始移民的城市的重要角色和意义的一句话:没有满洲人,我们就会饿死。近距离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后,我确信无疑,这句话实际上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满洲人绝对是欧洲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欧洲人就会没有吃的、喝的和烧的,这是人类生存所最必要和最起码的物品。”[31]19世纪末20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亚洲色调正是由中国人构成的,他们给从俄国西部各地区移居而来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过,这一类移民与自俄国进入东北地区的其他族群相比是少数,在俄罗斯文化的传播上也不如后一类移民作用大。从俄境进入东北地区的族群以俄罗斯人为多,俄罗斯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也主要与他们有关。哈尔滨曾是俄罗斯侨民在东北地区的最大聚居地,曾一度被视为在华俄侨的“首都”,这里自1898年被确定为中东铁路中心枢纽后,在现今的市区内曾有相当部分是类似于租界性质的“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成为当时脱离清廷控制的“国中之国”[32]。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批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和俄罗斯人出于政治原因逃亡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在那时的哈尔滨到处可见白皮肤蓝眼睛的俄国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一些富裕的白俄、犹太人等做起了买卖,也有一些贫穷的俄罗斯人成为苦力甚至乞丐。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俄侨来说,1921年11月3日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苏联政府宣布大赦,有近10万的俄罗斯人经满洲里回国。但在有人归国的同时,又有许多人从俄国不断涌出,“1922年是俄侨在哈人数最多的一年,据统计,高达155402人”[33]。根据列维亚金娜的研究结果,“1930年在中国登记在册的有125000俄罗斯人,大部分居住在满洲里、昂昂溪、富拉尔基等铁路沿线地区,不算哈尔滨的话,人口达110000多人,而当时哈尔滨已登记的俄侨人数为9500多人。”[34]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是俄罗斯侨民在中国的又一大聚居地区,尽管“九一八”事变后俄侨人数大为减少,但到1953年统计时,“当时额尔古纳旗仍有外侨(包括苏侨和无国籍侨民)1805户、8686人”[35]。而唐戈则指出,“除了俄罗斯人,来自俄境的族群还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等等。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本来同俄罗斯人就没有太大的差别,生活在俄境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更多地具有俄罗斯人的特点。犹太人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除保留犹太教信仰和民族认同外,文化的其他方面则与所在国主体民族所共享。生活在俄罗斯的犹太人说俄语,生活习惯基本同于俄罗斯人。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生活在贝加尔湖东部和南部的草原上,本来在文化上与俄罗斯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7世纪以后,由于受俄罗斯人统治和影响,其文化也融进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文化因素。十月革命后,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移居呼伦贝尔草原,由此把他们的文化,连同被整合了的俄罗斯文化带到了这里。在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他们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特别是以蒙古族为主要传播和接受对象时”[36]。
来自俄罗斯的各族群和旅俄归国华侨把俄罗斯文化带到东北各地。俄罗斯文化的传播不仅发生在他们的家庭内部、他们周围的人群里,而且还发生在他们兴办的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中。总的来说,俄罗斯文化通过移民方式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在来自俄罗斯的各族群内部延续,其次是向与上述族群发生直接接触的人或人群中传播,最后主要是通过上述人和人群向他们以外的人群和地区传播。传播方式一个是延续,一个是直接传播,一个是间接传播。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以移民方式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移民数量多、规模大,这一点又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从俄罗斯移民在中国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涉及三个地区,人数最多的就是东北地区,其次是新疆,然后是内地某些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二是与英美、法、德等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这些国家的移民规模都无法和俄罗斯相比,例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据有其市区面积的大部分,但“1925年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不过3.7万人”[37],无法与同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数量相比。在某些地区,俄罗斯移民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数量,在哈尔滨,“1922年共居住有俄罗斯侨民155402人,而那一年该市中国人只有126952人”[38]。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很多地区都存在这种情况。由于在这些地区俄罗斯移民的数量超过了中国人的数量,而且俄罗斯文化在当时又是一种强势文化,所以在这些地区俄罗斯文化必然会对中国文化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第二,移民到东北地区的俄罗斯人,除少数上层人士外,大多数都是贫民(包括一些破落的贵族),特别是农民。十月革命后,大量俄罗斯贫民出现在中东铁路沿线,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移民与中国人之间的通婚现象发生了。由此使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多了一个渠道,即家庭传播的渠道,而这种渠道之于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渠道所无法比拟的。贫民更容易接近其他族群或使其他族群接近,这不仅仅表现在中俄通婚这个问题上,在文化传播中,贫民扮演的角色更为丰满鲜活。
综上可以看出,东北地区具有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先天优势。虽然沙俄的武装侵略给东北人民造成了伤害,但俄罗斯文化通过移民方式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主要是一种自发、自愿的文化交流,这正是俄罗斯文化能够在东北地区传播并融入东北文化之中的基础。而且,这种传播以其平民化的亲和力把俄罗斯文化与东北地区深具大众移民文化色彩的地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东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涂抹上了俄罗斯文化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