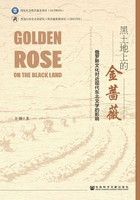
三 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状况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对我国东北地域文化发生影响,与自然环境条件、历史变迁、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对它的考察应该涵盖广义的文化领域,凝聚于自然景观中的人文积淀,区域内文化传播的路径、走向、活动形态,以及民俗风情、城市建筑、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文学艺术等人类的行为系统的演变,都应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本部分主要介绍俄罗斯文化对东北地区生计方式、语言、服饰、饮食、城市建筑、音乐、教育、宗教信仰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方面的影响状况。
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十分广泛,在生计方式、语言、服饰、饮食、民居、卫生习惯等方面都留下了痕迹。俄罗斯文化传入东北地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包括品种、技术、工具在内的一整套庞大的农牧业生产体系。以饲养奶牛为例,东北居民从俄罗斯人那里学到了奶牛饲养和奶制品制作的多种技术,丰富了农牧业生产体系,提高了生活水平。杨利民、王立纯合著的长篇小说《北方故事》中的俄罗斯姑娘叶莲娜来到放马营后,饲养奶牛,制作奶油、奶酪,还把牛奶卖到蓝旗镇,就是一个例证。
在语言方面,很多俄语的音译词被东北人熟练地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喂德罗”(铁皮桶)、“布拉吉”(连衣裙)、“列巴”(大面包)、“热特”(胶轮拖拉机)等等。在东北作家的作品中,这些俄语音译词也经常出现。比如萧军的《下等人》中有唔德克(俄国下级劳动者常饮的酒名)、巴斤克(俄国皮靴);罗烽《狱》中有素波(菜汤的通称),沙巴卡(狗),亚邦斯克(日本人);疑迟的《同心结》中的张绍武“喊着:‘阿鲁布扎,耶希奇聂?’这奇异的外国语言自然又会使茂荣感到惊诧,俄国侍女就毕恭毕敬的答应着”[39]。东北作家笔下的东北人,不仅语言中常夹杂着大量俄文词汇,而且有一些人如张绍武、《混沌》中从上流士绅到普通山民和儿童,都能或多或少地讲一些俄语。
随着俄国侨民的不断涌入,在哈尔滨等城市中国居民与俄侨间的交际活动日益频繁,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上海的“洋泾浜”的边缘语言[40],我们不妨品味一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于哈尔滨的边缘语顺口溜:“哈尔滨一到,说话毛子调儿,握手拿国姆,达拉斯其好。奶油斯米旦,列巴大面包,水桶喂得罗,戈兰拧水到,谢谢斯巴细,把脚抹走掉。大官戈比旦,木什斗克叼,旅馆开孬门儿,玛达姆卖俏。工人老脖带,咕食不老好。骚达子买货,扁唧少两毛,鼻溜儿打歪,笆篱子等着。顶好是上高,捏肚哈拉少。”[41]这就是地道的哈尔滨边缘语的真实写照,没经过特殊文化氛围熏陶的人是很难马上领悟出其所以然。为了交际的需要,许多汉语词及其他外来词亦被俄侨“中为洋用”,纳入其语言中,如房子——фанза(fangzi),炕——кан(kang),高粱——гаолян(gaoliang),豆腐——доуфу(doufu)等。还有俄侨作家用汉语词作为自己的笔名,比如当时深受欢迎的小品文作者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他的笔名是Маманди“慢慢地”[42]。
在服饰方面,东北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着装风格与审美趣味,巧妙地吸收了俄式服饰的某些特点。从男士的呢子大衣、船形毛皮帽及高腰靴子、男式小立领的衬衫,到女士夏季五彩缤纷的连衣裙和秋冬的大围脖与大披肩,包括头巾的系法与前额盘卷的发型,在许多细微之处,都能见到俄罗斯服饰文化的悄然渗透。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的作品中经常描写东北的山民和猎户穿着“巴芹克”(一种俄式皮靴),或者是“俄国式的短外套、哥萨克的衬衫”,孩子们过年得到的新礼物里面有“俄式的小马靴”;李文方《六角街灯》中的工程师穿着的则是“三开领的列宁服”,一些漂亮的女学生穿着“洒花布拉吉”。
在饮食方面,东北人民也从俄罗斯饮食文化中吸收了营养。在哈尔滨,有很多俄式西餐厅,金碧辉煌的华梅西餐厅仍是哈尔滨俄式大餐的招牌餐馆,近年来更有“波特曼”“露西亚”等后起之秀,将俄式美食继续发扬光大。中央大街上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街角,留存着正宗的俄式咖啡屋与冰激凌店,装饰与口味都是别具风情的。俄国人背着啤酒红肠面包酸黄瓜到野外唱歌跳舞的娱乐方式,也为东北居民所接受,啤酒、红肠、面包、黄油、鱼子酱等食品已成为东北居民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烽、舒群笔下的监狱犯人们吵嚷要吃的是“黑列巴”和“苏波汤”;骆宾基《混沌》中的孩子们到商店要买的吃食也是“列巴”;萧军小说中的那些工人和苦力到小酒馆喝的饮品,不是“俄德克”就是“格瓦斯”;阿成《私厨》中那位中俄混血女士点的是“纯俄罗斯面包,纯基辅红菜汤”;刘跃利的《绝境》中地下党接头的地点是米尼阿久尔点心店,“米尼阿久尔是俄语,精美的画框”。此外,啤酒的传入也值得一提,“1900年俄商乌卢布列夫斯基为满足哈尔滨俄侨生活的需要,率先在哈尔滨开办了啤酒厂,这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啤酒厂。啤酒初为国人所不识,但渐渐地人们喜欢上了这种饮料,并效仿俄罗斯式的豪放狂饮,使之成为当地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外地人常用‘喝啤酒,像灌溉’的谐语来形容哈尔滨人的饮酒习惯”[43]。
就民居来说,《混沌》中所写的乡绅家庭在冬天取暖用的火炉是“别列器”(一种俄式的炉台);烧水用的是“红铜的燎水壶”,“那燎水壶是纯粹俄罗斯式的,高装,圆筒形,三只脚,一个带开关的自来水式壶嘴,上端是壶盖打开可以倒水,烟囱里可以装木炭,还有一个汽笛,水滚时就呜呜地尖叫”;交通工具是“俄罗斯式的有布篷的四轮车”。《绝境》中哈尔滨的街头立着图姆贝(圆形广告筒);《西伯利亚蝴蝶》中不少村民嘴里叼着木什都克(烟斗)。根据唐戈的研究,东北解放以后,很多居民“把满汉式上下扇的窗户改为西洋立式合页窗。冬季普遍在室内安置了火炉(红砖砌或洋铁皮制),从而取代了传统的满洲火盆。个别人家在室内铺了地板,地板上刷油漆,用墩布来拖地。甚至冬季室外用于贮菜的地窖也改在了室内地板下面,而且夏季可以当冰箱用”[44]。这都是从俄罗斯人那里学来的。
齐齐哈尔市的昂昂溪区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原因除了这里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文化外,就是此处还有黑龙江省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俄罗斯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但仍能为人们所使用。“据当地有关部门调查,目前昂昂溪站附近遗存俄式住宅共有90多栋,分布在铁路以北近0.3平方公里的狭长区域内。这些房子墙都很厚,窗户基本都开在南面,又高又窄,门前一般连接着一个木结构的外廊式的附属建筑,须登几阶木楼梯才可上去。昂昂溪铁路沿线的俄罗斯建筑在近一公里的直线上绵延,其布局合理、配套齐全。车站、民居、教堂,以及文化、体育、医疗等设施应有尽有。”[45]齐齐哈尔市的文物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些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于2003年颁布了相关保护条例,把昂昂溪区的百年老建筑群列为保护街区。建筑是历史的备忘录,体现了时代的印迹和一个民族对自我历史的认知。东北各地保留的俄罗斯式建筑既表达了俄罗斯人希望在此地长久生活的愿望,更体现了东北人开放的胸襟。
有关城市建筑,哈尔滨和大连这两座城市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两座城市从规划到建筑物都体现了浓郁的俄罗斯文化风味,既洋溢着异域风格的独特魅力,又包含着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演绎了一部东北地区的“双城记”。
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形成处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是在强行介入的外来文化影响下发展的,所以在城市规划、市政设施、城市建筑以及街道名称等方面都体现出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1898年哈尔滨成为中东铁路中心枢纽后,随着铁路的修筑亦开始对城市建设进行规划设计。1900年中东铁路工程局派A·K·列夫杰耶夫为首任工程师,对街市进行设计。最初的城市规划者按其首都莫斯科的规划模式,巧妙地运用城市本身所具有的以及后来人为的区域分隔特点,做了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46]。依据地势北临松花江、南靠马家沟河的天然环境布置街道,利用滨州、滨绥、哈大三条穿越城市的铁道线进行区域分隔。在城市规划中,设计者们还尤为注重对区域功能的布局处理。南岗区居全市最高点,设计者以东正教尼古拉中央教堂(俗称喇嘛台)为中心,向东、西、南、北、西北、东北布置了六条放射路面,而在其周围则安排了一批办公、住宅、商服网点的配套建筑,形成了以中东铁路管理局为中心的行政办公区。而埠头区则规划成店铺紧凑而集中的商业区,在现今的十二道街、中央大街、尚志大街等街道上,昔日分布的几乎全是各式各样的西方古典式或俄罗斯式的商业建筑群。在隔江相望的太阳岛上,则建有许多俄国人的别墅,成为达官显贵的休闲疗养区。经过了如此规划,初步奠定了以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位中心的城市雏形”[47]。在城市建筑方面,哈尔滨显示出强烈的西式风格,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便以“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这种称谓与其城市建筑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建筑设计者们在建筑风格上处处以尖塔、穹顶、帐篷顶、倒悬卷脚、雕花浮雕等俄罗斯传统手法进行设计,营造出浓郁的俄罗斯文化氛围。另外,在以古典的俄罗斯建筑风格为主的同时,还伴有一些法兰西风格的建筑,这是由于19世纪的俄国建筑师吸收了18世纪下半叶在西欧流行起来的古典复兴建筑潮流所致。街道名称的来源和演变除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外,也常为文化的接触变迁所左右。1900年城市规划时,俄国侨民根据一套自己的街道命名方式,使一些带有异国情调和殖民色彩的街道名称出现在哈尔滨。比如罗蒙诺索夫街(今道里区河曲街)、米哈依洛府街(今道里区安定街)、霍尔瓦特大街(今南岗区中山路)、高加索街(今道里区西三道街)、华沙街(今道里区安平街)等。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中国政府对中东铁路各项权利的收回,东省特别区曾对哈尔滨街道名称进行过一次较为普遍的改造,但从语音、含义以及特征方面仍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以至在今天哈尔滨的街道名称中依稀可见这种历史文化的陈迹。
近年来,哈尔滨城市急剧扩张,已经看不清从前的“东方莫斯科”的轮廓了,而20世纪60~80年代,哈尔滨还能体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建筑风格。在后期的城市建设中,哈尔滨逐渐丢掉了自己的本色,这不能不说是遗憾。我们并不是崇洋媚外,只是说外国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应该保留。一个城市一旦沦为火柴盒建筑的大本营,或者一群不伦不类建筑的试验场,那么这个城市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
大连的建设与哈尔滨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它的战略位置以及俄国人占据时期较短,所以表现出来的俄罗斯文化色彩不如哈尔滨浓厚。1898年俄国沙皇政府胁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强行占据了以大连、旅顺为基地的辽东半岛南部,并且开始在这里修建港湾、堡垒和城市,这就是大连城市建设的开端。大连是中国北方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西方人、日本人,特别是整个国土处于寒温带、缺乏不冻港的俄国人眼里,大连天然的不冻港,宜人的气候,连接东亚各国与环太平洋各地优越的地理位置,简直是人间的天堂,从1899年开始俄国人便开始营造他们的“东方巴黎”——美丽的达里尼。俄国人对大连市街的设计完全模仿了巴黎市街的建筑模式,试图把大连理想化为东方的巴黎,同时赋予了它近代殖民文化的特色。初建的达里尼市是一个以直径212米的广场为中心,十条大街向四周辐射,连通一条条环形道路和几个小型广场布局的小城市。城市的中心广场便是完全模仿了巴黎“明星广场”建筑布局的尼古拉广场(今中山广场)。广场周围是殖民者最重要的部门,以及起辅助和烘托作用的坚固高大的西方近代建筑。“从城市的整体布局来看,俄国殖民主义者把城市分成三部分,即俄国人居住区、公园苗圃和隔离华人区、华人居住区。这种布局直接继承了中世纪法兰克福王国形成时期加洛林封建庄园文化和城堡文化”[48],这种布局把高贵与贫贱、征服者与本征服者严格分离,殖民侵略的文化特征一目了然。而且,“由于大连的战略位置,到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人被迫退出大连之前,大连城市的中外居民只有4.4万人,大连、旅顺两地俄国的军人却超过了6万人。所以,尽管俄国殖民者拥有一个‘东方巴黎’的梦想,可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达里尼仍然是一座只有西方文化符号却没有西方或者俄罗斯文化根基的城市,或者说一座缺少文化的兵营”[49]。
俄罗斯音乐及戏剧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那些背井离乡的难民远离故土来到陌生的中国东北时,也带来了他们的艺术,而且其音乐的样式和戏剧的内容都保持着十月革命之前的状态,如经典的歌舞剧、芭蕾舞剧、交响乐等。关于哈尔滨等地俄侨音乐的发展状况,斯拉乌茨卡娅写道:“这里集中了一流的音乐人才。这里有一个极为出色的歌剧团。这个剧团几乎所有成员都是20世纪20年代末,从苏联拉出来的。这个剧团中,有一位后来成为名人的列梅舍夫,当时还称其姓为列梅绍夫。他好像是哈尔滨众多杰出的俄罗斯歌唱家之中,唯一返回苏联的人。一位俄罗斯歌剧女主角达丽雅·斯普丽舍夫斯卡娅也曾经在哈尔滨居住过。曾经登台演出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俄罗斯男中音歌唱家克尼日尼科夫。在铁路员工俱乐部里演出的歌剧,就其舞台布景和演员服装而言,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就是在那个俱乐部,我听了我一生中的第一部歌剧《美人鱼》。”[50]
在哈尔滨共有三所完全按俄罗斯音乐学院的传统教学模式设置课程的初级音乐学校,在这里,中俄两国青少年可以受到正规的俄罗斯音乐教育。这三所学校是第一音乐学校(1921年创办)、格拉祖诺夫高等音乐学校(1924年创办)和哈尔滨音乐专科学校(1929年创办)。哈尔滨音乐专科学校是当时东北最负盛名的艺术学校,为满洲地区培养了大批中外音乐人才。该校校长阿普捷卡廖娃不仅是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著名的歌手和钢琴演奏家,她为音乐教育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热情。[51]经过数年的发展,哈尔滨已经不再是文艺的沙漠,恰恰相反,当时处于中国地理边陲的哈尔滨成为音乐艺术的绿洲。
关于东正教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化的首要特征,俄罗斯人每到一处最先修建的就是教堂。沙俄入侵东北后,在各地修建了许多教堂,大批传教士也陆续来到东北,在这里传播东正教教义。这些传教士一面帮助穷苦的百姓和无助的孩童,一面把这种慈爱的行为归结为上帝的爱,东正教文化也逐渐地为东北的百姓所熟悉。不过,中国民众入教的目的大多是功利的,而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是出自灵魂的信仰。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除家庭、社会影响外,生理疾病是诱发民众加入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当被问及为什么加入东正教这一问题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回答是身体有病,入教是为了祈求平安。另外,由于个人生活中遭遇困难或不幸而寻求精神慰藉也是入教的主要原因之一”[52]。东北地区近代以来动荡的社会环境使这里的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这从客观上为东正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入教是遭遇种种苦难的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途径之一。
中国式的信仰往往目的很明确,祈求平安,求得健康、财富、子嗣等。哪个“庙”灵验,那里的香火就会旺盛,中国人似乎并不太在意本国神与外国神的区别。霍特科夫斯基曾回忆他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在圣尼古拉大教堂进行礼拜活动之前,有一个人在教堂门前大声祈祷,原来是一个中国男子带领自己一大家子人(丈夫、妻子和八个孩子)跪在尼古拉圣像前。他们穿着朴素,甚至有些寒酸,但都非常干净。他们请求教堂的大司祭出来见他们,都主教梅列迪出来接见了这家人,他们跪在梅列迪的脚下,请求都主教允许他们信奉东正教,而且还讲了要入教的理由。这个男人是一名船工,负责把乘客运送到松花江对岸,当时的松花江水面宽阔,风大浪高,特别是在恶劣的天气,江上行船极其危险。一天这个男人刚把船摇到江心,一排大浪就把船打翻了,乘客都落入水中,并迅速沉入江底。这些人大多不识水性,船工自己也不会游泳,船工在水面用最后一口气喊道:“车站老头[53],救命!”突然,船工觉得有一个人用手将他从水中托举出来。等他苏醒时,发现自己躺在江边。从此,他决定皈依东正教,因为他觉得是车站老头救了他的命。[54]可以看出,这个船工想要入教是因为落水获救的“神迹”,而不是对东正教教义的理解或神父们对教义的宣扬。
中俄通婚是东正教传播的另一种途径。在中俄联姻的家庭中,必然会涉及宗教信仰问题。“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东正教是一神教,一神教具有不宽容性和不妥协性。而汉族要么是没有信仰——无神论,要么是多神信仰,包括民间信仰、道教和汉传佛教等。多神信仰是什么神都信,反过来是什么神都不信。在信仰这个文化子系统里面,当一神教与多神教发生冲突时,多神教往往是拱手相让,而由一神教一统天下。这种一神教的强势表现在具有中俄两种血缘关系的家庭中,当最初中国父亲与俄国母亲结合时,没有一位俄国母亲放弃东正教而改信汉族传统的信仰,倒是有许多中国父亲皈依了东正教。”[55]
从现代东北文学对东正教文化的表现来看,多数东北作家对东正教文化不关心或持否定态度,或将俄罗斯东正教与基督教、天主教混为一谈。不过,也有少数几位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精神有较深的理解,并以宗教的终极关怀来考察现实的人生。最早在作品中写到基督徒的小说是金剑啸的《云姑的母亲》。云姑的母亲是位眼科医生,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她没疯的时候,常说:“帮助旁人是最大的快乐。”所以她不时地免去贫穷病人的医药费。但在她带着云姑到哈尔滨寻找她唯一的儿子时,看到哈尔滨大水灾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死尸在水中漂过的惨状,由此发疯。小说表现了那个战乱年代普通民众苦难的人生道路,暗示了基督并不能拯救人们的灵魂,一味软弱忍让只有死路一条。萧红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的主人公全家都是基督徒,马伯乐在逃难的路上不停地祷告说:“主啊,保佑我一路平安。”受时代政治影响,萧红接受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念,因此,马伯乐的信仰在萧红的笔下是荒谬可笑的。而且,马伯乐本就是一个阿Q式的人物,他的信仰更多的是一种崇洋和赶时髦,而不是灵魂的虔敬。不过,萧红对马伯乐基督教信仰的歪曲描写也折射出这一信仰在中国人心中的接受程度。
小松的长篇小说《北归》是一个情节曲折复杂、宗教意味很强的作品。作品以基督徒王权和他的义母老信徒杨菲为线索,围绕他们演绎出刘、杨两家曲折而又充满罪恶的世俗戏剧。刘振邦一生叱咤风云,是城市里的金融巨头。但战争的来临使他首先失去了金钱、权势和妻子杨小蝶,在一无所有、孤苦伶仃的晚年,儿子与女儿又一起被山林大火烧死,他用一生积累的荣耀与胜利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灰烬和绝望。而杨小蝶的兄弟们都在贫困交加中死于非命,她的侄女莎丽带着与集生的私生女跟随王权去北方乡下避难。莎丽对北方大地怀着无穷的梦想,她深深厌倦过去生活所给予她的一切,她热烈地向往与王权在一起的新生活。但三年以后,王权又与一个“下流女人”同居并生下一个男孩。王权虽然皈依了基督,但并不能真正解脱自己。文中写道:“幸福的人一定能生活,能生活的人不一定会幸福,但是幸福与生活是人类最高的本能与希望。社会是常常要抹煞希望与改变本能的。”小说展现了世事的无常,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仇恨与罪恶,横祸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人们头顶随时都可能落下。小说结尾写王权与两个女人两个孩子忧郁而烦躁地活在世上,那两个孩子“很明白的知道了他们的父母,是怎样的度过了一个战争的年代”。作家感慨道:“他们两个背负着罪恶家庭的暗影,来到了人间。好像是有一个新的罪恶,又从这两个青年身上开始。”小说以“新罪”作为最后一节的标题,说明尘世间罪恶的永恒性,新人从其诞生时起便背负了原罪。从《北归》中可以看出,小松从基督信仰的角度观察人世生活,看到了人类的罪恶性和世间万物的不足依恃,表现出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对终极信仰的寻求。
东正教信仰是俄罗斯保持民族精神完整性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途径在中国东北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拓展。而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保持精神完整性的路径——兴办教育——却在东北地区生根发芽,影响绵延至今。在北满俄侨云集之地,为了使族群能够继承文化传统,构建教育体系是一种必然施行的工程。1898年12月6日,对哈尔滨教育史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这一天,哈尔滨市的第一所小学校开始招生。该校由俄侨斯捷潘诺夫(И.С.Стеланов)创办,命名为松花江小学,位于香坊区卫生街。除了松花江小学外,还有1903年开办的位于道里区的盖涅罗佐娃第一女校,1906年开办的埃克沙科夫女子中学和1921年创办的普希金中学等。北满这片土地和关内中原地区相比,在教育上相对落后,而俄罗斯人对教育的投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失。到1931年,俄侨在整个东北地区建有中小学74所,43所在哈尔滨,31所在铁路沿线的中东铁路管理局辖区,学生达18000多人,除了俄罗斯学生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学生,其中中国学生达200多人。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高水平的大学开始在哈尔滨出现。由梁赞诺夫斯基负责的法学院(法政大学)和俄中理工学院(即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不仅享誉远东,在欧美、澳大利亚等地也非常有名。俄中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以严谨的学风、开阔的视野和卓越的才干在世界各地留下了美名。该校发展很快,1925年招收450人,1926年就达到了650人。1928~1929年有815名学生在这所大学里学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学校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和俄罗斯的工程师。[56]那些毕业于该校的中国学生,很多都成为新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骨干。时至今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依然是中国最知名的大学之一。
俄罗斯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还有许多方面,如绘画、电影[57]、新闻出版等,在此不一一列举。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俄罗斯文化渗入、蕴含在东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带有俄罗斯文化色彩的文化氛围必然会对近现代东北文学的萌生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详细分析和探讨俄罗斯文化对近现代东北文学的影响就是下面章节所要解决的问题。
[1]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第2页。
[2] 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4,第1~2页。
[3]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吴学金译,东方出版社,1998,第3页。
[4]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4~45页。
[5] 〔美〕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三联书店,1998,第7页。
[6] 转引自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页。
[7] 〔美〕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6,第151页。
[8]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页。
[9] 冯绍雷:《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4~15页。
[10] 冯绍雷:《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32~33页。
[11]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5页。
[12] 郑永旺认为:“清朝初期,图里琛用满语所著的《满汉异域录》中将俄语‘Рoсcия’翻译成满语‘Oros’,译成当时的汉语就是‘鄂罗斯’。其实,早在《元史·宪宗本纪》中就有‘征斡罗思部,至也烈赞城’之说法。根据时间推算,元朝时期,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基辅罗斯时代,‘斡罗思’应是‘Rus’一词的译音。根据语言学家考证,‘O’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语音上的音素移位和同化。满、蒙语中,辅音【r】从口型定位到舌尖振动的瞬间,会产生一个若有若无的元音‘O’,这很像现在中国人在学习俄语‘Р’的发音时在前面加‘T’的做法,于是在‘Русъ’的‘Р’前便出现了一个‘O’。这大概就是汉语中‘俄罗斯’一词的来源。”参见郑永旺《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90页。
[13] 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第112页。
[14]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7页。
[15]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60》,商务印书馆,1980,第8页。
[16] 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238页。
[17] 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245~246页。
[18]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2848~2849页。
[19] 〔俄〕库罗帕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英〕A·B.林赛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33页。
[20] 〔苏〕阿·斯捷潘诺夫:《旅顺口》,赵毅芳、李世骏、曹峨编注,大连出版社,2000,《出版说明》,第4页。
[21] 白朗:《白朗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125页。
[22] 清康熙十年(1671)俄罗斯伊利姆斯克堡修道院院长叶尔莫根在雅克萨建立了东正教主复活教堂。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不久,叶尔莫根又在离雅克萨不远的一个叫磨刀石的地方建立了仁慈救世主修道院。
[23] 黄心川:《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37页。
[24] 黄心川:《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44页。
[25] Сибирская Лравославная гаэета,No5,2003,转引自郑永旺《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204~205页。
[26] 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主要途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27] 海参崴来自古老的肃慎原住民语言,汉译为“海边渔村”或“海边晒网场”。清朝时闯关东的河北、山东人把这里叫作崴子,因为当地盛产海参,所以汉译为“海参崴”。历史上,海参崴自汉唐时起就有人群活动,由中国历代王朝管辖。1858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海参崴。自此,海参崴被沙俄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成为沙俄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要塞。
[28] 张福山、周淑珍:《哈尔滨与红色之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137~139页。
[29] 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主要途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第121页。
[30] 〔俄〕聂丽·米兹、德米特里·安洽:《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序二》,第2页。
[31] 〔俄〕聂丽·米兹、德米特里·安洽:《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作者的话》,第1~2页。
[32]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1页。
[33] 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37页。
[34] Ревякина Т.В.Проблемы адаптации 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Китае:начало 1920— середина 1940-х гг.М.,2004,стр.41.
[35]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第665页。
[36] 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主要途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第122页。
[37]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271页。
[38] 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7页。
[39] 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中)》,沈阳出版社,1996,第915页。
[40] 边缘语“是出现在世界好多通商口岸的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叶蜚声:《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215页。)两个或几个操不同语言的民族试图进行交流,但由于文化、语言差异过于悬殊,双方很难进行跨文化交际。于是,为了交际的需要,双方或多方以他们本族语言为基础生成一种词项不多、语法规则简单的初等语言。这种语言便是边缘语。
[41] 王忠亮:《哈尔滨地区使用的中俄洋泾浜》,《词库建设通讯》1995年第6期,第16页。
[42] 荣洁:《俄侨与黑龙江文化——俄罗斯侨民对哈尔滨的影响》,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102~103页。
[43]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581页。
[44] 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主要途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第122页。
[45] 郑永旺:《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62页。
[46] 张抗抗在她的《东北文化中的俄罗斯情结》(《作家杂志》2003年第10期)一文中说:“1993年我曾访问俄罗斯,我对莫斯科城的第一印象,竟然觉得如此熟悉,似曾相识。可以说,莫斯科是一个面积被放大了多倍的哈尔滨,但更为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或者说,我曾经十分迷恋与热爱的,具有浓郁的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哈尔滨城,在我亲临莫斯科的时候,忽然觉得哈尔滨很像是莫斯科的复制品,甚至是印刷精良的盗版本图书。东正教大教堂拜占廷风格的大圆顶与拱型穹顶、市区各种公共建筑物米黄色的墙体、建筑物外墙上的浮雕装饰,郊外别墅赭红色或深绿色的铁皮斜屋顶、阿尔巴特街的花岗石路……以至于我回到哈尔滨以后,常常发生幻觉,走在哈尔滨南岗与道里的某些街区,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好像是莫斯科城被整体或局部地搬迁过来。”
[47]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575页。
[48] 许宁、李成:《别样的白山黑水:东北地域文化边缘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400~401页。
[49] 许宁、李成:《别样的白山黑水:东北地域文化边缘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405页。
[50] 〔俄〕斯拉乌茨卡娅:《哈尔滨—东京—莫斯科:一个苏联外交官女儿的回忆》,裴列夫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第35页。
[51] 郑永旺:《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189页。
[52] 陈蒲芳、路宪民:《基督东渐与中国乡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性探析》,《社科纵横》2005年第12期。
[53] “车站老头”是俄语Старик вокзала的汉译,指的是圣尼古拉大教堂里的圣徒尼古拉塑像。
[54] Сибирская Лравославная гаэета,No5,2003,转引自郑永旺《俄罗斯东正教与黑龙江文化》,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210页。
[55] 唐戈:《简论额尔古纳地区东正教的特点》,《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61页。
[56] 参见荣杰《俄侨与黑龙江文化——俄罗斯侨民对哈尔滨的影响》,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89~90页。
[57] 1901年俄国人考布切夫在哈尔滨创办的电影院是全中国的第一座电影院,要比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创办的虹口电影院早6年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