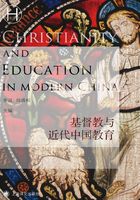
适应与变通:东吴大学的本色化实践(1871—1939)
马光霞(1)
美国监理会在近代来华差会中并不是一个大差会,在教士派遣和经济资助上都远不如美部会、美北长老会、北美美以美会等大差会,但是该会却在近代中国留下深刻的影响。他们创办的晚清最具影响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成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蒙读本,创办了第一流大学(东吴大学)、中学(中西女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流的人才(谢洪赉、宋耀如、宋庆龄、吴经熊、费孝通、赵紫宸等)。一个小教会是如何办成如此有重大影响的大事业的,它的经费来自何处,它的人力支撑是什么?显然,本土社会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本土社会究竟是怎样与教会关联互动的?通过什么机制实现互动的?所有这些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本文试以东吴大学为个案,对此进行探讨。
一、三所源头学校(1871—1900)
甲午之前,监理会在教育方面重点发展了上海中西书院和博习书院两所寄宿学校;甲午之后,一个偶然的时机促成了宫巷中西书院的开办,而就是这个偶然却铸就了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的辉煌,促成了林乐知大学梦想的最终实现。
1.存养—博习书院
蓝柏的传教思路是“向那些易于接近的普通人宣传福音,将皈依者组成教会;提供训练有素的领导以保证教会的未来发展”(2),因此培养和训练当地牧师就成为其主要目标之一。1870年,苏州收到了第一笔学校捐款;(3)1871年,曹子实创办苏州第一所监理会的日校。(4)1875年潘慎文(A. P. Parker)来华,1876年被派来苏与曹子实一同工作,学校开始招收寄宿生。(5)1878年,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位教友Buffington捐资6000美元,用于教堂和该寄宿学校的建设。(6)同年,监理会在天赐庄购地,兴建住宅和校舍。1879年曹子实调往上海,学校改由潘慎文负责,不久学校迁往天赐庄,(7)并改名为存养书院。1884年,改名为博习书院(Buffington School),以纪念Buffington先生。(8)该校宗教气氛浓烈,所有课程都是汉语授课,潘慎文明确表示这所学校的目的有二:第一,为教会工作培训当地代理人——牧师、教师、医生助手等;第二,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教育中国的年轻人。(9)
2.中西书院
与蓝柏不同,随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了解的深入,林乐知意识到要想生存和扩大传教,首先要适应并依赖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林乐知从事世俗工作的经历,不仅使其逐步构建了包括官员、文人、绅商、买办阶层等中上层人士在内的交游网络,而且也使其一改传统的传教思路,由“直接布道”改为“间接布道”,且“兼合中西”“走上层路线”。中西书院学生的积极报名及社会各阶层的踊跃捐款,即可看作是林乐知及其事业楔入主流社会的成功尝试。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他希望通过双语教学培养学生“中西并重”,学贯中西。他批评当时差会所经营的学校,认为“学生来自中国较为低下并毫无希望的阶层”(10),而林乐知的工作经历,使他看到了结交“士”和“官”的好处,从而使他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办学思路。他将中西书院的招生对象指向“上层社会”,当时学校初招学生200余人,据林乐知称,“除一人外,所有学生皆来自上海最优秀的家庭,并且代表了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阶层”(11)。
中西书院的建设费用当时“按林乐知与监理会所定之条款,差会承担购置校舍地皮,支付外籍教师薪水的费用,余者皆从当地筹措,自1881年夏起,林乐知向沪上中外人士筹集资金,迄1882年底,中西书院已获足够‘支付两年的开办费用’”(12),这其中“美国本公会拨洋四万余元,中朝李傅相、王总戎、邵唐诸观察暨中西官绅商富慨分鹤俸、惠赐洋蚨”(13)。1883年,“又蒙粤东徐君雨之观察慨让虹口空地三十六亩,业也备价购就”(14)。由是观之,林乐知与徐润的交情非同一般。
比较上述两所学校,从学生来源看,中西书院学生主要来自上流阶层,而博习书院的学生则多来自社会边缘阶层。从下表关于中西书院及博习书院的学生人数及其财政收支情况(以1895年为例)中可以看出,两校尽管学生人数相差不大,但财政收支状况却大相径庭,上海中西书院已处于自养状态,尽管还收到教会的捐款,但其结余已接近于博习书院的总收入,而博习书院收入大多来自教会拨款,支出大于收入。
中西书院与博习书院学生及财政情况一览(15)

3.甲午战后的三大举措
甲午之后,人们开始了挽救民族危机的尝试。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著名的改良上谕,其中一个就提出了组织全国性现代学校体系的计划。该项计划规定在全国各县、府和省城设立小学、中学和大学,而北京的国立大学为最高学府。于是各地纷纷开始兴办学校。但不久,慈禧太后撤销了皇帝的上谕。(16)监理会的教育工作也顺应时势之变化,迅速作出应对:
首先,更换中西书院掌门。1895年,林乐知辞职,着力于《万国公报》的工作,监理会会督郝德立(E. R. Hendrix)调在博习书院任教的潘慎文执掌上海中西书院。潘慎文“素重实学及传道事业,接办后,即增授算学与自然科学及宗教等课,各种仪器标本,亦岁有增加。一时邮务海关电政路局以及实业界中之桃李,强半出斯校,而学生之受洗进教者,亦与年俱进”(17)。
其次,孙乐文(D. L. Anderson)抓住时机在苏州创办了教授英语的宫巷中西书院。甲午的战败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年轻士子为寻求救国真理,逐渐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5年秋季,苏州人迫切希望当地能有一所英语学校,当时上海方面有人提出为了赚钱应当开设这样一所学校。而孙乐文则认为,“如果对西方教育真正需要的时期已经来临,我们教会就应当满足这种要求,如此控制并引导这场运动,新学就不致是对抗而是有助基督教。”于是“宫巷中西书院”应运而生,学校系试办性质,只收25名学生。大多数学生不只是希望学习几个商务英语句子,他们是真心希望获得真正的教育,因此孙乐文声称,“我们的目的不只是教授英语,而是进行全面的教育”。大部分学生来自富有的家庭,在家有自己的私人教师,有几个还是秀才,有许多都参加过正规的政府考试。(18)
由下表可以看出:
(1)从学生人数上来看,两校的学生人数在甲午战后至维新变法时期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尤其是维新变法高潮时期的1898年,更大幅增加,身处文化重地苏州的宫巷增幅比率更大,接近50%;而变法失败后,宫巷中西书院学生人数暴跌,也是接近50%,而上海中西书院虽然受此影响,学生人数有所减少,但降幅不是很大,保住了200人的出勤数。从表中还可看出,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两校人数继续下跌,苏州跌幅仍然远超上海。另据记载,苏州宫巷中西书院由于义和团运动而被关闭(19),而特殊环境下的上海中西书院学生出勤率依然变动不是很大。
上海中西书院与宫巷中西书院的1895—1899年情况一览

①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September 22-27, 1897, p. 24,华东神学院图书馆藏。
②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September 22-27, 1897, p. 58, 26,华东神学院图书馆藏。
③Minutes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October 20-25, 1898, p. 84,
④Minutes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October 20-25, 1898, p. 56.
⑤Minutes of the fif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November 14-20, 1900, Appendix: Education Statistics; p. 32-33.
(2)从外籍教师和中国当地教师人数的对比看,两校的外籍教师人数相差不是很大,但本地教师的人数悬殊,这说明历史已近20年的中西书院在人员的任用上,本土化色彩已经很浓;而刚刚兴办不久的宫巷中西书院西教士人数一直多于当地教师的人数,说明该校还处于依赖西方传教士的阶段,还没有培植出自己的当地助手。
(3)从两校的财政收入比较看,两校皆已达到自养。从宫巷中西书院的收入中即可看出,学校的一大笔收入来源于学生的学费;而地处上海的中西书院自养程度比宫巷更高一些,不仅能满足自身需要,还经常贷款给其他学校。如1900年年度报告中就记载,该校曾贷款1000美元给东吴大学。(20)宫巷中西书院尽管刚成立不久,但收入很稳定,即使是在社会动荡时期,收入也没有大的起伏。
最后,筹办东吴大学。除却上海中西书院、宫巷中西书院,监理会最早创办且以培养传道人为特色的寄宿学校博习书院也顺应时势,做了一些改进。如1896年春,该校添设英文一班,由韩明德夫人(T. A. Hearn)为主任,教一些有志研究英文之学生。(21)至1898年,英语班学生已达60人,班内还有2名日本学生。(22)然而,1898年年末学期结束时韦理生(Wilson)总督决定关闭博习书院,将学校财产、设备移交宫巷中西书院,而将一部分学生并入中西书院,(23)计划在博习书院原址改建大学。
对于为何选择在苏州而没有在上海办大学,潘慎文指出:第一,苏州是一个文化中心,它的声誉名扬全国,如果大学建在这儿,它必将影响到全国;第二,与上海相比,苏州对年轻人的诱惑较少,而这可以使学生远离赌博、鸦片及嫖娼等社会罪恶;第三,大学的选址必须位于城区,远离拥挤的商业中心地带,这比上海更容易控制学生;第四,苏州还以其丝、棉花、茶、稻米及制药业而出名,更因其高度发达的文化生活及众多的文人墨客名扬天下。这个城市的士绅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的支持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另外,美国监理会在此也因博习书院和宫巷中西书院的发展而为大学的创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校在教育上的经验和名望为东吴大学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24)对于选址天赐庄则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在天赐庄购地要比宫巷容易,二是新校址距离监理会的其他教会工场较近。通过官员的帮助,监理会购得了这块地基。(25)
1899年11月,年议会在苏州召开,由韦理生总督和蓝华德总秘书出席,会议决定在苏州建立一所有文学、神学和医学系的大学,其他各系以后加增。(26)会议赞成制定一个包括在苏州的大学、其他各中心的中学及小学在内的未来教会教育事业发展的计划,并要求所有现存学校都必须朝着实现这一体系目标而努力。(27)母会也赞成该计划,并于1900年5月13日任命林乐知、孙乐文、潘慎文、柏乐文、步惠廉(William B. Burke)、文乃史(Walter B. Nance)及葛莱恩(John W. Cline)为董事会董事,林乐知为主席(28),专门负责东吴大学的筹办事宜。
其实,任何一项教会事业的开展都离不开中国人的认可、官方的支持及财政的援助,监理会创办东吴大学,自然也要过这几关。
当时监理会筹划了一个全教会的“20世纪运动”,林乐知、柏乐文、潘慎文和孙乐文被指定在年议会上发起这一运动。自然,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推动这一大学计划。为此而组建的委员会选派林乐知负责征求当局的同意,柏乐文负责在苏州、无锡、常熟及南浔等地的上流人士中募捐,他们多数是柏乐文的病人,并对他怀有感激之情;潘慎文、孙乐文负责两所学校,与他们合作。(29)
第一关:征求当局同意。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林乐知联名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创办大学的计划,请求总督同意。(30)。林乐知还送去自己的许多著作,刘坤一对此计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不仅建议苏州当局为购地提供便利并在需要时予以合作,还建议学校取名为东吴大学。(31)
第二关:获取经济援助。
为获取援助,监理会先后在苏州和上海组织会议来宣传这一计划。1899年冬,在苏州蓝华德等人假葑门外苏关公署,宴请本城官长、学界人士,美国驻沪总领事也出席了此次会议。林乐知谈了拟在苏州办大学堂之事,结果“合座赞同,并许尽力襄助”(32)。在上海也组织了一次类似的会议,林乐知邀请了许多士绅和商人参加,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与合作,同样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会后,来自苏州、上海、常熟、无锡及南京等地的捐款迅速发起,几周之内捐资就达约20000美元。(33)
在美国,1901年4月,“20世纪运动”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一次传教大会上达到了顶峰。高乐威(Charles B. Galloway)会督的演说,使他很快募集到5万多美元的捐款。(34)
有了官方的许可、当地人的支持及财政的援助,东吴大学的开办计划立即启动。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此时期,东吴大学的源头学校虽因着传教士的办学思路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随着时情变化而迅速做出变通和调整,也因着所汲取的当地资源及与其互动而使其分别具有了苏州和上海的地方特点,更使得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二、西教士执政时期的东吴大学(1901—1927)
“庚子事变”过后,改革成为大势所趋,监理会的教育事业也紧踏革新节奏,与时俱进。
1.孙乐文执掌时期(1901—1911)
进入1901年,当中国的北方还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时候,地处南方的监理会的学生已经入校学习了。当时,监理会在华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除去博习医院所办的医学院校及女子部所办的教育外,监理会男子部所开展的教育工作主要在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两所寄宿学校的工作,除继续中西书院,东吴大学的开办在监理会教育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01年3月8日,宫巷中西书院迁入天赐庄,东吴大学正式开办,苏州的教育工作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当年就注册学生64名。而且学校明确表示,自己的办学目的是利用所发现的最好的方法来给予学生最完全的教育,一种能有助于构建他们纯洁而有用生活的教育。(35)这次监理会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标志着监理会教育重心由上海至苏州的转移,也标志着苏州作为监理会布道工作大本营地位的初步成形。就监理会苏东地区来说,一个新的包括圣约翰教堂(1881年初建,1915年重建,改称圣约翰堂)、博习医院、东吴大学及景海女师(1902年建)等在内的涵盖教会传教、教育及医疗等三大支柱事业的天赐庄基督教社区正式形成。二是主日学校及日校的工作。如1901年监理会有8所日校153名学生,学校董事部被建议准备一个年级课程的学习,以便使他们能转变成真正的预科学校的学生,然后再依次进入高年级的学校。(36)
面对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形势,监理会开始意识到教会教育与政府教育之间所存在的竞争,负责教育工作的学塾部曾针对此提出相应建议。如在1905年年议会上,祁天赐(N. Gist Gee)代表学塾部对当时的教育形势分析:(1)目前是我们教育工作史上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因为中国政府开始清醒地意识到教育的必要性,并开始用免费或补助的形式吸引学生进入新成立的学校。(2)无论我们学校在其他方面条件是多么优越,政府学校所提供的一些职位等条件也会吸引一部分我们学校的学生。(3)这些学校将会处于非基督教的影响之下,所以为了能沿着更好更宽广的路线发展我们的教育工作,我们就必须表现出稳固的有组织的一面,这样就能使政府承认我们所做的工作。(4)目前我们的教育工作还缺少组织。(37)
鉴于此,祁天赐特向董事部提出建议:(1)苏州大学应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进行最有效的高年级工作。(2)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我们现有的其他学校应该与该大学合作。(3)在我们所管的每一所学校里都成立预科学校,而这些学校再依次和那些较高的年级合作。(38)
在此情况之下,监理会对其教育工作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如中西书院就有两次调整:一是中西书院校长的更换。“1905年冬,潘慎文迁上海任教区长兼总编辑,校董会任葛莱恩博士为校长;葛博士为之添建宿舍,力谋改善,又提倡组织同学会,协助本校发展。”(39)二是东吴大学合并中西书院。1911年3月,孙乐文逝世后,5月1日,葛莱恩将其中西书院工作移交白约瑟(J. Whiteside)后调任东吴大学校长,同时董事会决定将中西书院与东吴大学合并,并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中西书院的教学器材。这次合并对中西书院来说是较为痛苦的一件事。在合并前,中西书院在各个方面都进展顺利:如从学生注册人数看,1911年春是191人,全年在校生是217人,其中有50名信徒;从师资上看,有12名当地教师,6名欧籍教师;经济实力也很好;而且学生对体育运动及宗教活动的兴头也都令人鼓舞。但尽管如此,还是服从大局进行了迁并。1911年秋,中西书院约80名春季入学学生转往东吴大学。(40)
对于东吴大学,监理会是着力加强。
首先是在美国完成注册。1901年6月14日,东吴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in China)在美国田纳西州注册(1908年改为Soochow University),纲领规定大学将由7所学院组成:神学院、文理学院、师范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药学院和工程学院。(41)
其次是院系建设工作。东吴大学的第一个目标是“建一所包括文学、神学和医学系在内的大学,其他各系以后加添”。
就院系课程来看:(1)1901年,宫巷中西书院迁入天赐庄升为东吴大学时,学校只设中学班,学生不足百人,1905年开设大学课程,招收大学学生。大学分为文理科(1927年改称文、理学院)。(42)(2)1904年,柏乐文在东吴大学设医学院,1909年首批3名学生毕业(1912年后成为南京协和医学院,即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学校)。(3)东吴大学神学科主要培训了两批学生,但只有一位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901年,三名志愿从事牧师职业的学生由中西书院被荐入东吴大学,希望接受神学教育。他们是1899年由博习书院并入中西书院的学生,于是文乃史用白话口语一段一段地给他们讲《保罗神学》。这三个学生中:奚柏绶的学习表现最为出色;1909年江长川从中西书院毕业后,也有从事牧师职业的诉求,并希望能接受神学培训,于是在东吴大学由孙乐文、李仲覃、文乃史、戈壁(Clyde Campbell)等组成神学教师团队单独给江长川上了三年,然后授予他东吴大学唯一一个神学学士学位。(43)
就教学设施和师资来看:始于1901年的东吴大学主楼于1905年建成,是南方风格设计样式的一座多功能大楼,内有大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及设500个座位的聚会厅。1905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为文理学士提供了完整的学习课程,并配备了充足的有能力的教师队伍。在四年的课程中,中外历史和文化、文理兼学。另外,文科学生还学习物理、化学、社会学、数学及经济学、逻辑学和美学;理科学生学习分析力学、动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及基本的科学课程。(44)
晚清政府的时政变化促使监理会调整教育政策,着重发展高等教育,从下表中西书院和东吴大学的比较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校的发展势头。东吴大学后来居上,无论是学生人数还是师资力量,都赶超了中西书院,这为东吴大学合并中西书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1—1911年中西书院与东吴大学比较(45)

由此看来,为应对当时的变革局势,监理会采取了重视高等教育以与政府教育竞争的措施。但是在1911年年议会上,学塾部在总结当时的教育政策时又认为中国差会的教育工作的比例失调,几乎是完全强调高等教育工作,也完全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低等教育工作。于是董事部又确定了政策:除苏州和湖州已有的中学外,在人力物力许可的时候于常州和松江建中学;另外又建议信徒子女应该在本教会内接受教育。学塾部还建议,在每一个有当地牧师的布道处都应该设立日校并置于有效的监管之下,然后与各中心的高等教育工作合作,并且为保证此项工作的开展,建议设立专项基金等措施。(46)问题既已提出,日后会有解答。
2.葛莱恩执掌时期(1911—1922)
此间,东吴大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是对第一个目标的完善和加添。如神学方面,1913年监理会不仅参与合办金陵神学院(1911年创办),还于1914年春正式开办了东吴大学松江圣经学院(1915年改称东吴大学圣经学校)。又一个偶然产生了,即法学的创设——1915年,蓝金在上海中西书院旧址预备开设东吴大学第二中学,却设法开办了东吴大学法律科。理科方面,在1901年东吴大学开办之初,生物学家祁天赐加入教师队伍从事理科教学,12年后化学博士龚士(Ernest V. Jones)也加入,两人共同奠定了东吴大学理科强项的根基,此后东吴大学开始有了生物系、物理系和化学系。(47)1917年,由龚士指导的两名学生获得化学硕士学位,这不仅是东吴大学首个硕士学位,也是全中国首个化学硕士学位。1919年,在祁天赐的指导下,又有两名学生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48)从中可以看出,东吴大学的理科学术水平已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语言方面因地制宜,1919年,蓝华德会督、女布道会的总干事及差会会同董事部商定设立吴语科,并“借妇孺医院的空房在正月里草草地开办起来”,任命文乃史为科长,李伯莲为主管教师。(49)该校为帮助来华传教士顺利开展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文乃史曾说:“在此后的20年中,大多到华东工作的新教传教士都在此花一年时间接受吴语培训。”(50)在职业教育方面,1920年司马德(Richard Smart)开始筹备东吴大学无锡实业学校,并于1922年3月开学。至此,东吴大学发展计划中关于专业设置的框架在葛莱恩时代基本构建起来。在此基础上,各专业在日后的发展中得以进一步完善。
二是实现第二个目标——东吴体系计划,主要内容是形成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三级教育体系”。
(1)小学。
进入民国时期,监理会对于小学的关注日益加强,特别制定出了发展小学的政策并拨入专项基金。“看目前中国时势,普及教育甚为紧要,尤当乘此机会广设小学部。本年会极其注意于此,而本部希望之目的,在各连环之各讲堂,皆有小学之附设。”(51)1915年,东吴二中、东吴三中相继进入东吴体系之时,各小学也归入了东吴教育体系之中。(52)
(2)中学主要有三处。
东吴一中:即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与东吴大学同在一处校园,共用一切教学设备,因此该校较教学条件优越,1917年改称东吴大学第一附属中学(53)。
东吴二中: 1901年中西书院部分学生归并东吴,还有部分学生不愿迁往苏州。于是监理会“另拨开办费洋500元,委蔡式之、袁恕庵、范子美、史拜言为董事,利用中西书院之校舍校具,开设一中西学堂,由董事会推潘慎文博士为名誉校长,袁恕庵兼校监,孙闻达任教务,开学后,情形颇佳”。(54)据1912年统计,当时学校定额招收150名,但后来者却多至168人,学膳宿费收入达12674元,另外学校还花6500元购置了租界外的运动场。(55)对于所开课程,学校认为“民国成立,信教自由,各学堂已不分教内外,一律为国家承认,故本校拟自明年起,所有课程注重《圣经》外,其余一遵教育部定章,以期推行一致”(56)。1915年该校成为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东吴三中: 1915年,学董部议定“将湖州海岛中学校改名为东吴大学第三中学,该两校中西课程渐与本校中学一律无异,以冀实行联合,俾毕业生可以升入本校本科肄业”(57)。
对于1916年东吴大学教育体系的进展情况,年会报告中记载:“本校一系之各学校联合手续,本年大有进步。所谓东吴教育系者如本校之正科与附属中学,上海之法律科与第二中学,湖州第三中学,松江之圣经学校,各连环所设之附属小学校20余处是也。”(58)
对于该教育体系,监理会在1918—1923年主要遵循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学制,预科二年,专科三年”(59)。其中,1921年的国立教育体系如下图所示:
对比发现,两个教育体系大致相同,而监理会教育体系却是独立国立教育体系之外,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经营的教会教育体系,从而也为后来中国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埋下了伏笔。
此时期东吴大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东吴教育体系的初步完成,专业设置的不断加添,还有许多方面,比如下表所示学生数量的增长:
东吴大学发展情况一览(61)

无论东吴大学发生多大变化,始终保持不变的还是其所实行的基督教教育及培养学生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初衷。此间,东吴大学依然将宗教列为必修课,施密德(W. M. Smith)从1910至1917年一直负责学校的宗教课程,他回国后其职位由赵紫宸接替。(62)平时学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如组织圣经讲习班、查经班,每学年组织一次复兴会,延请名人演讲,如1912年,丁立美、戈登、谢洪赉及俞止斋等就曾来校讲道。(63)另外,学生还有若干如益赛会、青年会、立志布道团等宗教团体,立志布道团每逢礼拜全都要外出传道。除宗教外,学校还强制开展体育运动,规定有兵式操、柔软操、军乐队、童子军、诗歌研究会、理科研究会、各种健身会、文学会及音乐会等,(64)且规定“每年进校的时候无论新旧学生必须要校医查验身体,该法已实行七八年,在东方各大学里面算是破天荒的事”(65)。东吴大学还同圣约翰大学一起组织学生辩论会,开展校际间的比赛,也有运动会等召开;学生的同门会、学生会等在关键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各项活动的开展不仅密切了学生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学生的生活、锻炼了学生的体魄、发展了学生的智慧、提高了学生的组织能力,还加强了校际之间的联系。
但涉及政治运动,学校往往采取回避措施。如1919年五四运动之时,东吴学生也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66),但为避免事态扩大,学校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如葛莱恩所说,“我们随机应变,放假十天”(67)。及至1927年,学校再次采取停课放假措施,避免学生的“过激”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什么都挡不住学生的爱国热情,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东吴大学学生会同苏城学生参与发起募捐活动,从6月6日到20日,共募得款项17300元,汇至上海总商会支援上海工人。(68)不止于此,学生还在1910年自己募资出力为一帮贫寒小儿设立了惠寒小学。1912年,葛莱恩曾报告说“该校之设,转手贫寒子弟,故来学者不但不取修资,且书本等亦由校中供给、而各学生之读书,日有进矣,并不间断”。(69)
总体来看,1912至1922年间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东吴大学得以迅速发展,因而初步实现了原定“大学计划”的两个设想。
3.文乃史掌校时期(1922—1927)
受1922至1928年“非基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北洋政府1925年11月16日宣布“所有的中国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等规定。东吴大学系统内也采取应对措施,率先做出部分调整。
首先是开始让中国人进入东吴大学领导层。其实,该校“开办数年后即主张学校当竭力使成中国化,学校中之领袖当以中国人居之。故校内行政最高机关即校政部,其中自始即有华人参加。关于向政府注册一层,已早于前清光绪年间向北京学部请求承认。只以当时学部方面尚未颁布规定办法,遂致未成事实……更就董事会方面论,其会员初虽尽属西国教会中重要职员,以后逐渐有本国知名之士加入,迨去年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条例,其时华人之充任董事者,人数已居三分之二矣。故除以副董事长江君长川改选为董事长,将原任之董事长改选为副董事长,行政组织方面,皆已与政府条例符合,而无须变改矣。至校长方面之改以华人充任,此举已于五六年开始办理”(70)。如1922年,东吴大学校长文乃史在北京会晤其得意弟子之一、任职于外交部的杨永清,邀请其回母校工作,并举荐其为副校长。但杨此时公务繁重无法脱身,没有同意。学校遂任命校友赵紫宸为教务长,后者亦成为进入东吴大学领导层的第一位中国人。1923年,东吴大学决定改组校董会,1924年初步实现改组,该校第一位神学毕业生、监理会著名牧师江长川和中央银行秘书胡贻谷等进入校董会,成为东吴大学历史上第一批中国校董。(71)
其次是东吴大学法科率先注册。1925年底,东吴大学法科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单位,以“中国比较法学院”的名义向北洋政府注册,结果每一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都能够获得政府许可的官方毕业文凭,而不用再额外地考试。另外,东吴大学校董会还决定1926年秋季开学后,所有的宗教必修课程将改为选修课,礼拜仪式也改由学生自愿参加,这是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最重要的一步。(72)
再次是文乃史校长积极采取措施,敦促母会同意向中国政府注册。在推举中国人出任校长的过程中,文乃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7年3月1日,他从自身做起,先行辞职,并力促校董会速选中国人为校长。文乃史于是成为中国教会学校中第一位要求由中国人接任校长的西人校长。(73)不仅如此,他还向母会一再写信要求向中国政府注册,同时要求母会继续对东吴大学的财政援助。最终,1927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校董会上会督宣读了母会关于同意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决定。(74)
最后是文乃史积极斡旋促成中国核心领导层的最终确认。1927年3月“南京惨案”发生后,西国传教士全都避居上海,东吴大学暂由中国教职员维持校务。在3月31日的校董会上,文乃史提名吴经熊为法学院的院长,盛振为则当选为法学院的教务长(75),校董会同时推选校友、该校化学教授潘慎明为代理校长。(76)1927年7月,杨永清写信给文乃史表示愿意接受校长任命,文乃史又向总会推荐说杨是最适合该校校长职位的人选。几经讨论,12月3日东吴大学校董会确认杨永清为该校正式第一任华人校长,文乃史当选东吴大学顾问。1928年春,继岭南大学之后,东吴大学成为第二所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在1928年新成立的校董会成员中有13名中国人,4名美国人,江长川为董事长,且所有东吴系统内学校除松江圣经学校外都有中国人担任行政领导。(77)至此,东吴大学核心领导层内不仅有了中国人,而且占据了首席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被纳入中国政府的教育系统之内,开始了中国人进行管理的新时代。
4.东吴大学的经济来源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差会的定期拨款及特别项目的拨款是其开展事业的基础,如东吴大学圣经学校1927年经济报单中,即有收总布道会6337.41元的记录,而当年总收入是10277.12元(78),即差会拨款约占62%。但“自养”一直是东吴大学努力的目标之一,对于自养方法,1912年葛莱恩就曾提出“一面尽力谋自养,加添学生之进款;一面尽力设法量力资助无力之学生;一面尽力筹划常年经费以备后来之用”(79)。从中可以看出,学校收入中学费收入、资助学生费用收入、常年经费等即是经济来源的三个主要方面,另外洛氏基金的资助也是很重要的一笔收入。
(1)学生费用。
学生的学费是学校自养的重要渠道,东吴二中由于处于繁华的商业大都会上海,早已实现自养。从1926年、1927年东吴二中学生人数以及学费收入的增长上,可以看出其学费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1926、1927年东吴二中学生人数及学费收入情况(80)

另外,学生还通过其他一些方式表达对母校的感情,如1912年学生“因前校长孙乐文逝世,谋建纪念华表,捐集银洋700余元”,“本校学生每于正课之假,研究音乐,现已集款六七百元,置办新出品之军乐器”(81)。已毕业的学生也向母校捐赠,如1920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前在本校的学生高阳君,每月赠洋5元,至今已有二年有余了;本校毕业生杨绍彭君,每月赠洋5元;本校毕业生笪耀先君赠美金2元”(82)。
(2)资助学生费用。
东吴大学曾有免费奖学金的政策,如1912年规定“本公会中学校每年有一名免修生;本校中学生成绩最优之一人,每年亦得免修;又有学生以工代膳,每日粪除学舍等事”(83)。对一些贫寒学生也有优惠政策,如先借待至毕业后逐渐拨还,或颁给贫寒奖学金等。另外,学校对牧师子女也实行免费政策。所以这方面的捐助就显得非常必要。有不少西人和国人对此进行捐助,如1920年东吴法学院曾有高秋荃奖学金,每年赠100元,资助无力支撑其学业的学生。(84)1926年又有东吴大学原学生杨葆灵4000元的捐助,“专为补助家寒勤学之学生”(85)。
(3)常年经费。
如1911年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之时,其一部分校产也归入东吴。葛莱恩对此曾报告说:“前年下半年总布道会应许校董之情,由中国借款建造在上海虹口昆山空地,建造80幢,为学校常年经费,现在此屋业已建成,亦此次出租,照此看来,定有宽裕之望,现以此款抵还宿债,债清之后,定为学校之助。”(86)
(4)基金。
该基金对东吴大学的捐助数额特别大,对于完善学校的教学设备及师资力量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如1924年年议会记录中曾如此记载:“东吴大学去年十二月曾向驻华洛氏医务基金委员会请求补助葛堂,设立经费,当即收到捐款洋银28000元,今夏即用此款购置器具以备本学期以完全应用,兹该堂定于十月二十九日正式开幕切盼。洛氏基金部又指定35000银圆,分五年拨付,以供增加教员书籍及经常费用之。”(87)
以上各笔捐助大多以金钱形式,有的捐助为实物形式。如1920年,曾有美国女士捐助法律书900本,另外纽约法律图书局、武昌文华大学等当时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图书室也各有捐助。(88)
东吴大学各项基础设施及建筑相继配套建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西人的捐款,如学校内林堂、孙堂、葛堂等相继落成大都是靠来自美国的捐助。而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经费支持,才保证了东吴大学教育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文乃史校长才能在当时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维持了东吴大学良好的发展势头,如添置了用于教学的完整的科学实验设备,建立了生物供应处(1924—1925)。东吴大学法科还从原址搬出,有了自己独立的教室、办公室、餐厅和宿舍等(1924),还与青年会合作加强了体育科的建设(1924)等。(89)
三、中国人执政时期的东吴大学(1928—1939)
1927年12月,杨永清就任东吴大学校长,江长川就任董事会主席,标志着东吴大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掀开了中国教会大学新的篇章。那么由中国人直接管理的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在国民政府时期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1.宗教性质
1926年,监理会曾就中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注册问题的《私立学校规程》进行多次讨论和研究。该规程规定:
一、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
二、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
三、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许可时之代表人。
四、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
五、 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
(监理会解读:“教育部解释:学校须以教育为宗旨,而对于教育者之宗教信仰与传教,并不限制。”)
六、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
(若注册一事,专关乎大学与专科学校,则改宗教一项为选修课,亦无不可,但“注册之大学不得在未注册之中学收纳学生”,那么大学注册,则大学以下之学校亦不得不同时放弃宗教必修课。(90))
除第五条外,监理会遵从上述规定并逐步实施。如1926年,将宗教设为学生选修课。有趣的是,东吴大学于1926年还添设佛经课,文乃史“鉴于佛学倡明当道提倡,于上人民虔信,于下各省监所均以延请佛学渊源之高僧居士到监担任长期讲经,感化罪犯,可见近年来佛学兴盛信仰日众,该校为应时势需要起见,现在本校学科中添辟佛经一课,聘佛学会会长觉醒和尚担任讲经事宜”(91)。
对于学校的宗教性质,杨永清则坚持“应该保持学校的基督教性质”,并继续维持与母会的联系,接受其领导,同时服从中国政府的领导,但也强调学校应该发展自己的个性。(92)杨永清上任之初即定“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
2.学校的变化
首先是东吴法学院发展。1927年吴经熊任院长之后着手进行改革,因而发展迅速。1929年将法预科转至东吴大学,上海部分也作了相应调整,且成绩斐然。随着东吴法学院声誉日隆,入学人数直线上升。1930至1931年度在校学生达594人,而同期苏州东吴大学却仅有学生450人,其中还包括186名法预科学生。1935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令更改校名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并特准可授法学硕士学位,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得授此学位的法学院之一。(93)
其次,东吴大学校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1930年添建了一个漂亮的游泳池,1935年建成体操馆,还建成了一座教师住宅,一座女生宿舍及两座男生宿舍,也进行了一些课程的建设等,但无锡实业中学及体育科却停办。(94)1928年,东吴大学松江圣经学校也“与东吴大学分离,经济及校务悉归步公个人处理,正名为惠廉圣经学院,步公维持至1932年夏乃停办”。(95)
此时期另一个重要变动是1932年东吴二中与东吴三中的合并。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东吴二中遭破坏较大,“一是日兵及浪人将东吴二中原副校长赵敌七掳去并残杀,二是整个上学期学生都未能开学”(96)。对于两校合并的原因,监理会曾给出四个理由:“一、二中地居虹口,四邻均系日侨,恐易多滋扰而发生冲突;二、该校年来势甚发达而场地狭小,校舍极已尽建,无从推广,迟早之间,势必迁往他处以图发展;三、吴兴三中校场大而校舍少,有发展余地而缺乏经济能力,二校一经合并,彼此问题既能同时解决;四、近来美国金融疲敝,总布道会贴补本校经费逐渐减少,故财政异常困难,校董会郑重考虑之后,认为与其铺张敷衍,不若收缩范围,集中经济人才以增进教育效能。”(97)由此看出,二中的财源将直接推动三中的发展。
至于小学,早在1926年,由于美国差会的津贴减少,小学数量减至10所,学生991名。另外1924年在苏州第二小学、松江第四小学及常州第十二小学加增了初级中学的课程。(98)此三校后相继转改成乐群中学(1927)、乐恩初中及恺乐学校(1934)等初级中学。到1932年小学为7所。(99)
3.学校的经济来源
此时期,因杨永清校长明确该校与美国总会的关系,接受其领导,所以总会的拨款依然是该校的常年进项之一。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时,东吴大学也深受影响,杨永清曾总结说:
“本校全部经费除西教员薪水外约共30万元,此乃包括文理法三院及三中学合计所能得到之补助金,仅基金收入约3万元,总布道会津贴美金2600元而已,维持现状深感困难,欲谋改进更不易举。本校苏州文理学院及第一中学去年预算总数为17万余元,内中可由学生方面收入者为11万元,去年春季,学校暂时停顿之故,该项收入尚不足8万余元,计短3万余元,虽经全体中国教职员于去年上学期一律牺牲减半,受薪西教士自动由薪水项下捐助约3000元拨充学校经费并筹得特别捐若干,然全年决算仍短12000余元。”(100)
从中可以看出,东吴体系中所需的运作资金数额是较大的,但美国总会的津贴费用与之相比却少得很,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东吴大学的自养程度已经很高。
相比之下,捐资渠道更为多元化。最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东吴大学文理学院的四层宿舍楼,“可容250人,造费8万元,乃由东吴同学李君中道之先君李维格先生遗产指赠,颜曰维格堂,以志纪念。按此项建筑经费纯由中国方面经募而来,实属创举”(101)。
另外,学校内设有以捐款人之名命名的多项奖学金。如东吴大学法学院曾有如下规定:“凡在本校法律系肄业之学生品学兼优者得请求以下之奖学金:同学会奖学金,钱陈震奖学金,高钏高铣奖学金,姚伯希奖学金,廌社奖学金等。”(102)而从1931年的捐款中还可了解到其他一些资金来源,其中既有美国人的捐赠,也有洛氏基金的支持,还有一些热心人士的襄赞。而最主要的是国民政府的资助,其意义非同一般。监理会人士也说,“我人辄谓现政府反对基督教教育,观于此次之奖助,如此巨款殊觉令人可喜。”(103)
一、美国爱迪克斯夫人遗嘱捐助美金1000元,按照汇兑善价可折合华币至4700元
二、国民政府教育部捐助法律学院5000元用以扩充图书馆及其他设备
三、驻华洛氏基金会捐助本校4000元为可喜实验楼添置设备之用,此承前本校教员祁天赐博士捐集
四、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捐助2000元补助本校生物系附设之生物材料所经费
五、美国裘女士(Germ Fun)捐款合华币千元有余,系为女生宿舍添置设备之用,裘女士更担任本校西教员,费德乐女士之薪金
六、此外又承其他热心人士捐助款项为数大小不一,而其热烈襄赞之同情良深忻哉。(104)
4.抗战时期的学校转移及学生情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文理学院迁至吴兴附属中学,中学部迁至南浔,法学院迁至上海租界赁屋授课,附设文学院课程。11月后,两校师生又辗转杭州、泗安、长沙及安徽黟县等地。1938年初,杨永清校长等回到上海借慕尔堂为校舍,筹备复课。在长沙和黟县的师生陆续到达上海,与上海师生会合后,1939年夏,大学部三个学院及附中在此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学校被迫停办。(105)
从下表可以看出,东吴大学在1939年已达相当规模,共1829人,尤其是大学生数远超中学生人数。在三个分院中,法学院依旧保持30年代的强劲势头。但在抗战时期,学生人数还是受影响较大的,1936年监理会学生总数曾达8000多人,而到1939年总布道部与女子部学生总数才3473人,不及当时的一半。但由于恢复教学的缘故,比1938年(3151人)又略有加增,增幅约300人。(106)
1939年东吴大学学生人数情况一览(107)

1939年,美国美以美会、监理会及美普会三会合一,监理会的名称不再,至此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也完成了既定的目标,从小小的日校开始,到小小的一个25人的英文班,再到包括小学、中学至大学三级教育网络的形成;从吸引贫寒子弟到招收富家子弟,从培训当地助手、服务当地教会到东吴桃李满天下……这些变化说明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的一步步壮大。
四、结语
东吴大学将“培训当地助手”且以贫寒学生为主体生源的苏州博习书院,和“中西并重”以富家子弟为主体生源的上海中西书院及甲午战后一个小小的重视西学的英文班作为源头,在20世纪逐步建立起了涵盖文科、理科、医科、圣经、法律、体育等科系,包括20多处小学及3所中学的东吴教育体系,使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达到巅峰。然而战争的爆发却极大地削弱了其教学力量,甚至一度停办。
从东吴大学的个案看,监理会与本土社会的互动并非只有中西之间的双向互动,更饱含本土社会的不同元素在新的时空背景下的碰撞和重组。来自江南社会的传统士人与商人既构成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撑,也是影响其发展趋向的重要力量,而且他们之间实际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差会的政策取向固然是决定监理会在华战略的关键要素,但这种政策形成的背后,本土社会尤其是时局的深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尽管如此,作为监理会在华事业的一部分,其传教取向是一个突出特征。这种传教取向即使遭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对也没有改变。在非基运动时期,国民政府要求在学校取消宗教选修课、由中国人担任领导人后,学校依然继续其宗教活动,保持其宗教性质。监理会的本色化实践不过是在非基督教本质问题上的一种调整和变化,基督教的普世性特征仍然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
应当注意的是,东吴大学的国际化特征固然为其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这种国际化特征在近代条约体制的背景下往往是以损害中国主权为代价的。监理会的学校在向国民政府注册之后,仍然接受美国监理会总布道会直接管理,实际仍处于半独立状态。这种格局的存在,不仅使监理会最终没能完全实现自立教会的“三自”目标,也为其日后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意想不到的冲击埋下了伏笔。
地方因素对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西书院开办时,林乐知、沈毓桂等人的本意是培养中西学兼通的人才,充实到政府的洋务机构之中,学校设定的目标也是发展为大学,但是该校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究其原因就在于学校经济上的支持者上海买办商人并没有协助其完成学校目标的内在动机。甲午战后,当人们希望西学维新来挽救民族危亡之时,孙乐文在文化重镇苏州开办了一个“学英语兼西学”的25人规模的宫巷中西书院,仅仅5年就发展成了东吴大学。1915年被派来掌教中西学校(原中西书院)的蓝金在校舍内开设了一个8人的夜校性质的法律班,但因为“上海工商繁盛、狱讼滋多”(108),日后该班竟然发展成为东吴大学首屈一指且全国一流的东吴法学院。由此可知,并不是所有的来华传教士都是抱着既定目标来开展工作的,地方因素在监理会教会政策的制定上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江南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载体,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从广州移往上海后,“上海财源”自然成为监理会教会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如1900年中西书院归并东吴大学,1929年东吴法学院法预科迁并苏州文理学院,1932年上海东吴二中并入吴兴东吴三中,这三次上海学校的内迁,都为接收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大笔援助。
东吴大学的案例表明,教会事业要想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存发展,必须适应和变通。适应和变通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适应是为了变通,而变通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两者互为条件。东吴大学本色化的实践,实际上也是其逐步融入社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1) 作者单位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12.
(3) Work and progress in China: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from 1848 to 1907. Nashville: s.n., 1907, p. 52.
(4)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8.
(5) 《中华监理公会第41次年议会议事录》(1926),第55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0。下文中亦有“监理公会第32次中华年会记录”、“中华监理公会第35次年会记录”、“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2次记录”等多种说法,本文皆沿用原档表述。
(6) “A. P. Parker: Short Account of the South Methodist Mission since 1877”, Chinese Recorder, Vol.XI (1881), p. 292.
(7) 《中华监理公会第41次年议会议事录》(1926),第55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0。
(8)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Golden Jubilee (1886-1935) Commemoration Volume of the Fifth Anniversary,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Young Allen Court Shanghai, China, 1935, p. 28.
(9)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46.
(10)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1868-1883 ),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p. 85.
(11)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8-1883),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p. 90.
(12) 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0页。
(13) 林乐知:《公报截止恭谢阅读诸君并定期起建中西大书院启》,《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10090页。
(14) 林乐知:《公报截止恭谢阅读诸君并定期起建中西大书院启》,《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10089页。
(15) 《监理会中华年会第10次记录》(1895),第9—1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17。
(16)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蔡咏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8页。
(17)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3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28—31。
(18) D. L. Anderson, “Kung Hong Anglo-Chinese School Report”, Minutes of the Thirteen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Oct. 20-25, 1898, p. 24. 参见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9) Minute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oochow, October 17-21,1901, p. 28.
(20) Minutes of the fif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November 14-20,1900,p. 32.
(21)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3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28—31。
(22) Minutes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October 20-25,1898,p. 21.
(23) Minutes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October 20-25,1898,p. 19.
(24)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p. 62-63.
(25) The Soochow University,Chinese Recorder, Vol.XXXIV, (1903),p. 31.
(26)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57.
(27)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19.
(28)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p. 60-65.
(29)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20.
(30)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20.
(31)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58-60.
(32) 《教会学校》,《苏州地方志·专业志》,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1606427.htm。
(33)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58.
(34)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21.
(35) Minute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oochow, October 17-21, 1901,p. 28.
(36) Minute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oochow, October 17-21, 1901,p. 36.
(37) Minutes of the Twentie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oochow, October 4-9, 1905,p. 28.
(38) Minutes of the Twentie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oochow, October 4-9, 1905,p. 28.
(39)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3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28—31。
(40) Minutes of the Twenty-Six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Oct. 12-17, 1911,p. 39-40.
(41)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60-65.
(42) 《教会学校》,《苏州地方志·专业志》,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1606427.htm。
(43)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64-66.
(44)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80-82.
(45) 参见Minutes of the fif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901至1911年各年统计表。
(46) Minutes of the Twenty-six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1911, p. 21-22.
(47)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p. 45-46.
(48)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105-111.
(49)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5次记录》(1920),第5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4。
(50)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92.
(51)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5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52)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0次记录》(1915),第5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5—97。
(53) 周承恩:《中华监理公会教育工作》,《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3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28—31。
(54) 周承恩:《中华监理公会教育工作》,《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3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28—31。
(55)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4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56)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4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57)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0次记录》(1915),第37—4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5—97。
(58)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1次记录》(1916),第5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0。
(59)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24.
(60)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蔡咏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9页。
(61) 《监理公会第31次中华年会记录》(1916),第5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0;《监理公会第32次中华年会记录》(1917),第51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1;《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5次记录》(1920),第5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4。
(62) Nance, W. B.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p. 113.
(63)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36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64) 《监理公会第32次中华年会记录》(1917),第5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1。
(65)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5次记录》(1920),第5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4。
(66) 王国平:《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67)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5次记录》(1920),第5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4。
(68) 王国平:《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69)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37—38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70) 史襄哉:《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8年第4卷第2期,第15页。
(71) 参见王国平:《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72)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155-156.
(73)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159.
(74)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163-64.
(75)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159.
(76) 周承恩:《中华监理公会教育工作》,《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3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28—31。
(77)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h. D. diss.,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p. 164-168, 182.
(78) 《中华监理公会第42次年议会议事录》(1927),第5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1。
(79)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4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80) 《中华监理公会第42次年议会议事录》(1927),第5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1。
(81)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38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82)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5次记录》(1920),第61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4。
(83)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3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84)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5次记录》(1920),第6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4。
(85) 《中华监理公会第40次年议会议事录》(1926),第5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9—56。
(86)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7次记录》(1912),第3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54—74。
(87) 《中华监理公会第39次年议会记录》(1924),第55—56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8。
(88) 《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5次记录》(1920),第6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4。
(89) Golden Jubilee (1886-1935):Commemoration Volume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Young Allen Court, 1935, p. 30.
(90) 《中华监理公会第40次年议会议事录》(1926),第5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9—56。
(91) 《海潮音》1926年第7卷第7期,第9页。
(92) Xu Xiaoguang, A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to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of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1993, p. 105-111.
(93) 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7页。
(94) Golden Jubilee(1886-1935):Commemoration Volume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Shanghai: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Young Allen Court, 1935, p. 30.
(95) 周承恩:《中华监理公会教育工作》,《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36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28—31。
(96) 《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大议会记录》(1932),第8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6—40。
(97) 《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大议会记录》(1932),第8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6—40。
(98) 《中华监理公会第40次年议会议事录》(1926),第6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39—56。
(99) 《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大议会记录》(1932),第6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6—40。
(100) 《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大议会记录》(1932),第8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6—40。
(101) 《中华监理公会第46次年议会议事录》(1931),第5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5。
(102) 《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一览》(1936年秋至1937年夏),第20—21页。
(103) 《中华监理公会第46次年议会议事录》(1931),第5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5。
(104) 《中华监理公会第46次年议会议事录》(1931),第53—5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5。
(105) 《教会学校》,《苏州地方志·专业志》,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1606427.htm
(106) 《监理公会中华年议会第54届记录》(1940),第40—4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8。
(107) 《监理公会中华年议会第54届记录》(1940),第41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07—0—48。
(108) 《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一览》(1936年秋至1937年夏),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