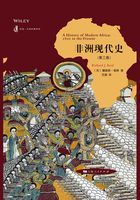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第一部分
政体、社会和经济:非洲19世纪的独特性与暴力
英文版原书页码:19
要理解非洲19世纪发展的诸多方面,一些大的主题至关重要,它们包括全球贸易的扩张、非洲政治结构快速改变的面貌、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转化,以及将这些合在一起的战争模式的改变。在19世纪的非洲,战争既是破坏性的,又是建设性的,一场军事变革——它在非洲大陆有着不同的形式——既驱动着快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反过来也是被它们所驱动。要理解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百年间的活力和创造,这样才能充分认识20世纪的独特模式。
长途和跨海的贸易改变了社会和政体的性质,为财富的积聚提供了机会,在本地生产和交换的相当简单的农业体系中,这种机会不一定存在。全球贸易带来了社会流动性,这既是向上的,也是向下的。这反过来又涉及政治权力平衡上的变化。与此同时,在19世纪,统治精英对“奢侈”或重要物品的分配也是确保政治支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达荷美(Dahomey),精心安排的“年俗”就涉及把这类物品分配给国王的追随者;布干达(Buganda)王国的政治中心,也存在一种类似的恩赐和分配体系。当然,输入进来的物品也有着实际效用,靠近海岸的政治和贸易上层人物使用外国进口物品来交换北方的马匹,比如约鲁巴(Yoruba)的情况。换言之,贸易力量可以转变为军事或政治力量。那些能够以这种方式积聚财富的人,也就处在一个能够购买人的地位上,而非洲“权力”的大部分都与拥有或能够影响的人数直接相关。贸易权力带来了扩大自己追随者的权力,购买奴隶、妻子或两者兼买的权力——在家庭延续和政权确立上,女性奴隶起着格外重要的作用。所以,由贸易而来的财富就能够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也在社会流动性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英文版原书页码:20
这些主题在整个非洲大陆都是共同的,不过,在其他方面,东非与西非的情况有着鲜明的对比。基本而言,东非的奴隶贸易在19世纪膨胀,在西非则是衰退下去。在西非,奴隶贸易促进了——的确也依赖于——分等级的政治—军事结构的兴起,这种结构由能够垄断进出口贸易的上层人物支配,他们通过自己对奴隶和奴隶贸易的控制做到了这一点。战争既是政治活动也是经济活动,代表着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当然这不是没有风险,它有可能被击败或造成严重伤亡,也可带来可观的回报,确保现存上层人物的统治。19世纪见证了这种情况的变迁,绝大多数奴隶贸易的主要欧洲参与国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废除了奴隶贸易,有一些国家继续“非法”进行奴隶贸易,直到60年代为止。那些从事奴隶贸易的上层人物的地位,因人口买卖的逐渐衰退(这在某些地区是非常缓慢的)和所谓的“合法”贸易(原材料和农产品贸易)的兴起遭到破坏,他们因失去对贸易和市场的控制而失去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由于进入到农业生产领域中,一些较小的生产者现在也能够与“大人物”竞争了。然而,在某些地方,尽管统治阶层发现自己的地位被削弱,但仍然能够使用他们的政治力量来补偿经济基础上的弱化。比如,1862年在旧卡拉巴,在尼日尔三角洲,小额棕榈油贸易就被首领禁止,这是为了至少维持一种寡头卖主垄断。19世纪中期,在达荷美,也对出售棕榈油课以重税。
大西洋非洲国家和部族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奴隶,这也带来了社会变化。使用奴隶是农业生产扩张的直接结果。普遍而言,19世纪中奴隶的价格是下跌的,这使普通的生产者也可以买得起奴隶。奴隶被用于耕种、货物运输、军事作战,有时甚至作为低级贸易者来使用。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合法”贸易的兴起,奴隶的待遇恶化了,这是因为奴隶相对便宜了,他们的主人可以较以前更狠地让他们干活。然而,奴隶们也有了一些机会,有些以暴力来反抗虐待,而经济活动中奴隶的数量越大,他们也就拥有越大的集体力量。不过,更重要的或许是19世纪的贸易变化意味着奴隶自身也可能积累财富,买到自己的自由,建起自己的政治权力。
在非洲大陆的另一边,则是朝向军事统治的趋势,这是奴隶贸易和象牙贸易扩张的直接结果。战争是获取奴隶的主要来源,涉及武士首领的兴起,他们收集俘虏,组建高度私人化的军队,创建个人权力。东非的贸易扩展导致出现中央集权,它自身又常常植根于武器和一些重要物品的进口。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暴力的加剧,再加上贸易和军事冒险带来的机会,就导致社会结构古老形式的崩溃、政治形式的改变,以及某些地区中新的身份的出现——如坦桑尼亚中部和北部,或者是现存身份和政治结构的加强——如布干达和埃塞俄比亚高原。
英文版原书页码:21
在非洲大陆的两边,战争与新的贸易和政治模式都有着内在的关系。非洲19世纪的许多暴力冲突都与争夺对贸易的控制有关,要获取贸易带来的利益,而利益之一就是武器。19世纪见证了重商主义在许多非洲社会中的兴起,它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联结。重商主义最清晰的表现,就是使用战争作为政策的手段。暴力冲突无疑伴随着非洲大陆各处的许多变化,当奥约(Oyo)的约鲁巴帝国——它原是一个主要的奴隶出口国——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崩溃时,就预报了约鲁巴人之间几十年冲突的开始。约鲁巴争夺对贸易的控制,同时也在更北边与穆斯林作战。暴力产生了相当数量用于“非法”出口的奴隶,这种现象最终促使英国在这一地区进行干预,其形式是对拉各斯潟湖城邦的合并。更朝西去,达荷美保持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对于它来说,奴隶贸易仍然至关重要,这个国家的分层政治结构中,军国主义是一种核心成分。战争是力量使用中的关键活动,也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在东非,作为对贸易网络扩张的回应,精力充沛的扩张主义(如果说往往短命的话)兼重商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国家接连出现,比如19世纪70年代,尼亚姆韦齐和金布分别由米拉姆伯(Mirambo)和尼亚古耶马维(Nyungu-ya-Mawe)统治。在北边,相对古老的布干达王国颇具进攻性地抓住了自己的贸易机会,在19世纪以使用武力为手段来获取贸易霸权。如同达荷美一样,布干达也把一种强力军国主义融入自己的政治结构和更广泛的文化构成中。埃塞俄比亚高原那些“哈贝沙”(habesha)政体也这样做,尤其是绍阿和提格雷,它们的位置很好,能够开发依靠红海和亚丁湾的贸易轴线。它们部分使用(尽管只是部分使用)战争作为确保贸易支配的手段。我们也不能只讨论那些中央集权国家的这种进程,在大裂谷地区中部,比如图尔卡纳和马赛,19世纪也有一种趋势,发展出更专门化的军事领导阶层和人丁年龄管理的新形式,尽管在这些地方,主要争夺目标不是贸易权而是地方资源,尤其是牧场,冲突常常因气候变化而爆发。
英文版原书页码:22

19世纪的非洲:主要民族和地区。
在南部非洲,19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也是暴力性的。祖鲁国在恩古尼人数十年的冲突中崛起,到2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成功的军事帝国之一,放在次撒哈拉非洲这个整体中也是如此。它建立在一种冷酷而高效的人丁年龄管理体系之上,与东非大裂谷地区的情况并无二致。祖鲁所代表的军事变革的反响十分深远,逃离这些冲突的难民分散到北至维多利亚湖南岸的地方,他们为这里带来了新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的样式。在南部非洲,长途贸易一直很重要,但这里的局面却因白人定居者越来越多而复杂化,他们既出现在开普殖民地,也出现在内陆的布尔“共和国”中,形成了人们所看到的政治和经济空间的三角争夺,也就是英国人、布尔人和非洲人自己。
当然,这些政体中的每一个对于冲突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在军事组织和领导上有不同的手段,使用战争作为政策的延伸有不同的目的。在祖鲁国,或者是大裂谷地区放牧部族的常备军,这种情况是相对稀少的;绝大多数国家和部族仍然依赖兼职的民兵,在需要时(或想要时)召集起来。布干达没有职业常备军,但它有一种深远的军事文化和社会风气。米拉姆伯的国家依赖“鲁加鲁加”(ruga ruga)这种力量——用枪、抱负和获利驱动武装起来的小伙子们,靠着吃本地的一种致幻药,拥有很高的士气。的确,许多这样的社会越来越依赖武器的进口,尽管枪炮在战争中的真正效果在非洲大陆各地并不相同。那些海岸边的西非国家积聚了大量的武器,东非内陆的国家也如此。在埃塞俄比亚,前后几任皇帝——特沃德罗斯、约翰尼斯和迈拿里克——也能够获取不少的现代或准现代武器。武器成为商业、社会和政治成功的象征,也推动着战争本身,但仍然有着地区的不同。在西非许多地方,随着时间推移和经验获得,人们已经能有效地采纳和使用枪炮,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在布干达,枪炮在19世纪后半叶才被引入,它们实际上削弱了军队的表现,这是因为缺乏训练,而且错误地强调武器的象征作用,而不是武器的实际威力。在非洲大陆,枪炮常常是次等的、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这就使得非洲社会在19世纪的最后岁月面对欧洲侵蚀时非常不利。
英文版原书页码:23
所以,非洲19世纪的政体、社会和经济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就与重塑政治与经济结构的斗争联系起来,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经常起着主要的作用。扩张主义的中心与武装的边疆发生冲突,新的政治和军事文化产生,它们之中有一些得到了巩固,而大量的则落潮下去,这一切发生在欧洲瓜分非洲的前夜。这种变化中的许多都与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机会相关,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小国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属于干达人和祖鲁人那些中央集权的重商主义的王国。对于西部、南部和东部非洲来说,欧洲帝国主义本身最终是与这些区域的商业和政治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种认为非洲社会天然不稳定的观点,就意味着贸易必须被保护,如果必要的话,用对混乱的武力压制和占领土地来保护。欧洲人把内部混乱、冲突和战争视为贸易的障碍,但奴隶贸易在19世纪很长时间中一直“非法”进行着,即使那些确实维持了秩序的非洲统治者,早晚也会被视为是危险的、不稳定的当权者,必须被除掉,以保证贸易的进行。在本书第三章,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些主题。
英文版原书页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