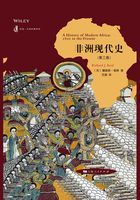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人民
环境的多样性推动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出现。相应地,各种独特环境使人们发展出不同的体质,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繁衍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体现出人类适应这些环境和气候、回应不同营养供给模式的过程。所以,就出现了诸如非洲南部的科伊桑(Khoisan)人,北部的非洲—地中海群体,还有跨越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森林的黑人民族。在19和20世纪,这些体质上的独特常常错误地用“种族”一词来表达,而且欧洲人(包括某些地方的非洲人自己)常常用体质类型来表示某个民族的“落后”程度,或者是它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达到的“文明”程度。比如,欧洲人常常认为“肤色浅”的民族把较为成熟的技术和政治体系带到了某个地区。[27]事实上,体质上的不同——比如皮肤的色素积淀,与“种族”毫无关系。从生物学上讲,只有一个人类种族,有着不同基因库的不同群体应被称为“种群”。
英文版原书页码:13
与体质多样性相伴的是语言上的多样,这些年来在语言方面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大陆非洲可以分为4个不同的语系。一个语系指若干关系密切的语言,它们由一个被称作“母语”的共同祖先发展而来。[28]非洲最大的语系之一是亚非语系,它覆盖了非洲大陆北半部的大部和西亚。亚非语系包含了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周边地区的许多语言,如北非的柏柏尔语、西部的豪萨语,它还把希伯来语和近几个世纪来与非洲关系更为密切的阿拉伯语包括在内。另外就是尼日尔—刚果语系,它的根源在西非,覆盖了非洲大陆南半部的大部,其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班图语,现在各种班图语在热带非洲的很多地方被使用。[29]尼罗—撒哈拉语系分布于撒哈拉,尼日尔—刚果语系之外的其他黑人种族也使用这个语系中的语言,但主要集中于从乍得湖到尼罗河之间的地带。最后是科伊桑语系,它可能是这个大陆所有语言群中最古老的,非洲南部的牧人和流动的狩猎—采集部族使用它,尤其是在喀拉哈里(Kalahari)沙漠。在很广泛的意义上,亚非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和尼罗—撒哈拉语系都与定居农业的传播相关联,尽管也常常与牲畜的放养联系在一起。这些语言的发展和逐渐占支配地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某些地方是数千年,这可能体现了获取食物方式的改善、相对的人口增长以及科伊桑语系使用者的边缘化。
过去两千年的非洲历史,基本上就是人口迁移、同化和细分的历史。比如,在北部非洲,阿拉伯移民——从阿拉伯半岛迁入埃及,随后几个世纪中又穿越马格里布地区进入尼罗河流域,都是在伊斯兰教于7世纪兴起后不久就开始的。在马格里布地区,这个“阿拉伯化”的过程与阿拉伯游牧部族贝都因人从10世纪到13世纪的迁移相关联。那些沿海岸移动者被称作“班努·希拉勒”(Banu Hilal),而那些在内陆迁移者则称为“班努·苏莱姆”(Banu Sulaym)。他们的迁移伴随着已有农业社区某种程度的破坏和混乱,但也带去了阿拉伯语言和文化,还有伊斯兰教,他们逐渐吸收了柏柏尔人社会。这一时期见证了北非转变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30]阿拉伯人也缓慢地深入尼罗河流域,尤其是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因14世纪阿拉伯游牧部族的南迁而推进。从那以后,阿拉伯人就进入非洲中央内陆,穿越达尔富尔,朝向乍得湖。然而,这个过程在把伊斯兰教带给这些地区的同时,也受到了通婚和社会同化、文化同化的影响,原来移动的阿拉伯部族逐渐定居下来和“非洲化”。古老的社会就以这种方式变异,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成了。[31]
英文版原书页码:14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它尤其与讲班图语的部族从如今的尼日利亚—喀麦隆边界一带进入非洲东部、中部,最终逐渐向南部迁移的过程有关。在班图人扩展之前,那些地区主要由讲科伊桑语的部族或讲相近语言的部族居住,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至今在非洲大陆的南端仍可见到这些部族。在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中,苏丹地带东部(比如上尼罗河地区)的部族,离开这一地区朝西,采纳了那里的经济体系;当东苏丹的民族变成游牧民族或牧人时,西非的民族则变为以农业为主,发展出定居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尤其是富拉尼(Fulani)人,他们许多人都保持着游牧方式,并与北非部族互动。农业性的西非人发展出更大也更密集的人口,超过了放牧或游牧区域。班图人的扩展一部分是与改进了的农业技术和铁作技术相联系的。这种扩展看来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或稍后开始,此时定居农业进入了班图家园,在接下来的三千年或更长时间内持续。一些被称作“北班图人”的部族开始沿着赤道大森林的边缘东进,从喀麦隆朝向大湖地区。在这些族群中发展出最早的东班图人和最早的西班图人。西班图人朝南进入中部刚果盆地,时间是公元前1000年的中期,并进入安哥拉的林地;也有其他人朝东出发,朝向坦噶尼喀湖和赞比西河。东班图人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抵达了湖区非洲,讲班图语的部族在公元头几个世纪进入了中南部非洲,也就是今天的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一带。现代观念认为这并不是“大”迁移,而是零碎的和地方性的,靠的是一段段的缓慢移动,持续了好多个世纪。[32]然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讲班图语的部族移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带,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被视为这一广阔区域的真正拓荒者,把它带入了定居农业。一场波及整个大陆的人口移动涉及迁移民族和本地人口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换,最重要的是,定居下来的人口和食物生产者群体,为独特的本地社会和文化奠定下基础,并反过来导致人口增长,刺激出更多的技术进步。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个结果,班图人还将他们的人口添加到中部和北部的非洲人口中,他们既是奴隶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害者。
根据一种标准的历史观点,复杂的物质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镇化、经济专业化和社会分层,所有这些都需要相对密集的人口。如同我们注意到的,这些在非洲大陆常常缺乏。不过,就政治结构和效用以及各种技术的使用而言,都有着相当的多样性。比如,非洲北部和撒哈拉南部之间就有着重要的农作技术差异。北非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在诸如犁的使用这类技术上相对先进,就增加可耕种的区域;然而撒哈拉以南则主要以锄来耕作,在任何时候这都只允许耕作相对较小的区域。[33]当然,锄能派上自己的用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许多地方,贫瘠的土地不适宜犁耕,那会毁坏微薄的土壤,导致土壤侵蚀,所以锄对于使用它的这种生态体系是完全适宜的。再举一个例子。确实,锄不能推进产量——尽管犁在北方能够做到,可殖民地官员却经常不懂得使用锄的好处。次撒哈拉非洲的农人种植各种庄稼,既有自己食用的,也有经济作物。撒哈拉沙漠两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域差异,这就是运输。北非人使用轮车,而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完全没有,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险恶的地形使得轮车无法使用,也是由于缺乏驮畜在舌蝇传播疾病的区域拉车运输。所以,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技术和商业发展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形式,这些地方的机会被限于某些区域。骆驼和马匹在沙漠和草原可以使用,但在林地和森林地区,运输的重负就要用头来顶,这就意味着低价值的重物不值得运输携带,长途贸易的最重要物品是小而高价值的东西,比如黄金和象牙。当然,奴隶是可以自己行走的。
英文版原书页码:15
较低的生产力也与人口情况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注意到,非洲的人口密度明显较低,它的大片地方无人居住。所以,不同于西欧或南亚,这里的稀缺资源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大而中心化的社会结构要发展,对人的控制远比对土地的控制更为关键,财富和权力都要靠控制人来获得。非洲的农业体系常常是一种自然轮作,农业是粗放而非精细的。当人口增长受到抑制时,文化和意识形态就会围绕人口生产的核心概念来发展,受这种意识形态支持的社会就围绕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来建构。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都涉及对生产和繁殖的控制。儿童意味着劳动力和这个族群的延续,血族关系的概念——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就要靠强迫威压。比如,普遍而言,此时很少有“无地农民”被迫以很少的报酬为拥有大片土地的上层人物干活的情况,这种现象只在殖民地时代才出现,当时整个族群都被转移,为白人定居腾出地方。当然,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中,通过长途奴隶贸易的人口输出——无论是穿越大西洋、撒哈拉沙漠或红海和印度洋,都是格外有破坏性的。
最后,非洲人在这个大陆建起了其多样性和复杂性都令人吃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欧洲人倾向于把非洲的政治计量单位称作“部族”,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术语,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但这里已可以说它只是在一些特殊背景中才正确或有效,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20世纪构建的概念。真实地讲,非洲社会从游牧社会到中心社会和区域社会,从季节性迁移的牧业到定居农业,这一切都有。许多非洲社会大致围绕着氏族观念组织起来,涉及血族关系和家系的概念;然而,有时这些却是想象出来的,并非实际情况。不过,一概而论是危险的,也有许多国家和社会围绕对一些杰出个人领袖或群体的忠诚而建立,服膺于他们特别的政治、技术或精神才华,与血族关系无关。还有许多是区域性的,其主权建立在空间界定上,这有时甚至是可移动的,尤其是在土地充足的地区。殖民统治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非洲人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能力,但改变在19世纪如同在20世纪一样,仍在持续,并且快速持续到21世纪。
英文版原书页码:16
注释:
[1]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分析要感谢近些年来在“现代”问题上的学术成果。比如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马萨诸塞州莫尔登,2004)。
[2] 这方面有一个精彩的简述,见约翰·伊利夫《非洲:一个大陆的历史》第2版(剑桥,2007),第1—5页。
[3] 艾里什·伯杰和E.弗朗西斯·怀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女性:女性回归历史》(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1999);凯思林·谢尔顿《非洲女性:早期历史至21世纪》(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2017)。
[4] 伊戈尔·库比托夫所编《非洲边疆:传统非洲社会的复制》(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1987)。
[5] 伊利夫《非洲:一个大陆的历史》,第71—72页。这个过程在这一地区的口传史诗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见班巴·苏索和班那·努特《桑介塔(Sunjata):曼丁哥史诗的冈比亚版本》(伦敦:1974/1999)。
[6] 理查德·J.雷德《过去与强调当下:“殖民地时期之前”与非洲历史的投影收缩》,《非洲史学刊》52:2(2011)。
[7] 维尔纳·吉伦《非洲艺术简史》(伦敦,1984);汤姆·菲利普斯所编《非洲:一个大陆的艺术》(伦敦,1995);萨姆·福格《埃塞俄比亚艺术》(伦敦,2001)。
[8] 吉伦《非洲艺术简史》,第330—333页。
[9] 西德尼·利特菲尔德·卡菲尔《非洲艺术与殖民遭遇》(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2007)。
[10] 菲力普·D.科廷《非洲想象:英国的观念与行动,1780—1850》,2卷本(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64);T.C.麦克卡斯基《文化冲突:19世纪的英国与非洲》,收入安德鲁·波特所编《牛津英帝国史第3卷:19世纪》(牛津,1999);理查德·J.雷德《惊骇、傲慢与仁慈:非洲的国际卷入,1914—2014》,《国际事务》90:1(2014)。
[11] 尼希米·莱兹恩和兰德尔·L.保韦尔斯《非洲穆斯林中宗教体验伊斯兰化和变种的模式》,收入尼希米·莱兹恩和兰德尔·L.保韦尔斯所编《非洲伊斯兰教史》(俄亥俄州雅典,2000)。
[12] 比如见詹姆斯·C.麦卡恩《玉米与优雅:非洲与新世界农作物相遇》(马萨诸塞州剑桥,2005)。
[13] 这方面的经典研究是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语系之根》第1卷《古希腊的建造,1787—1987》(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1987);《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语系之根》第2卷《考古和文献证据》(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1990)。但也可参看玛丽·莱福克威兹《并非出自非洲:非洲中心论怎样变成了把神话当作历史讲授的借口》(纽约,1996)。
英文版原书页码:17
[14] 转引自A.G.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哈洛,1973),第32页。
[15] 比如见托因·法罗拉《民族主义与非洲知识分子》(纽约州罗彻斯特,2001),尤其是第3部分。就当代的著名论述而言,见T.O.兰杰所编《非洲历史中浮现的主题》(内罗毕,1968)。
[16] 见《非洲的历史:方法论之刊》,这份刊物出版于1974年;以及约翰·爱德华·菲利普斯所编《写下非洲历史》(纽约州罗彻斯特,2005)。
[17] 贾恩·瓦思纳《作为历史的口头传统》(伦敦,1985)。
[18] E.S.阿台尼奥—阿蒂安波《从非洲史料编纂学到非洲历史哲学》,收入托因·法罗拉和克里斯蒂安·詹宁斯所编《知识非洲化:遍布各学科的非洲研究》(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2002),第15—17页;约瑟夫·米勒所编《非洲的过去在说话:口头传统和历史论文集》(康涅狄格州哈姆登,1980)。
[19] 格雷厄姆·康纳《非洲文明:热带非洲殖民地时期之前的城市和国家,一个考古学视角的考查》(剑桥,1987),第183页;约翰·索伦森《想象埃塞俄比亚:非洲之角的历史与身份之争》(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1993),第21—37页。
[20] 这个观念在里安·马伦《我的叛徒之心》(伦敦,1991)中有生动的表述。
[21] 科廷《非洲想象:英国的观念与行动,1780—1850》;也见V.Y.穆迪姆比的开创性著作《显然是发明出来的非洲:灵知、哲学和知识秩序》(伦敦,1988)和《非洲的观念》(伦敦,1994)。
[22] 比如阿奇博尔德·代尔扎尔《达荷美历史:非洲的一个岛屿王国》(伦敦,1793)。
[23] 米娅·卡特和芭芭拉·哈洛《使命:基督教,文明和商业》,收入芭芭拉·哈洛和米娅·卡特所编《帝国档案》第2卷《瓜分非洲》(达拉谟和伦敦,2003),第243—245页。
[24] 这是弗雷德里克·卢吉那部著作《英国在热带非洲的双重使命》(爱丁堡和伦敦,1922)背后的基本观念。
[25] 这方面最好的介绍之一,就是乔斯林·默里所编《非洲文化地图集》(纽约,1998)。
[26] 经典研究是J.福特《非洲生态中昏睡症的影响》(牛津,1971)。
[27] 约翰·汉宁·斯皮克《尼罗河之源发现日记》(爱丁堡和伦敦,1863);C.G.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伦敦,1966)。
[28] 约瑟夫·格林伯格《非洲的语言》(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63),以及随后的修订版。
[29] 德里克·纳斯和杰拉德·菲利普森所编《班图语言》(纽约,2003)。
[30] 汉弗莱·费什《马格里布东部和苏丹中部》,收入罗兰·奥利弗所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约1050—约1600年》(剑桥,1977)。
[31] P.M.霍尔特和M.W.戴利《苏丹人的历史:从伊斯兰教到来至今》(伦敦,2000),第1章和第2章。
[32] 比如见贾恩·瓦思纳《新的语言学证据和“班图扩张”》,《非洲史学刊》36:2(1995);克里斯托夫·俄瑞特《班图扩张:早期非洲史中的一个中心问题的再审视》,《非洲史研究国际学刊》34:1(2001)。
[33] 杰克·古迪《非洲的技术、传统与国家》(伦敦,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