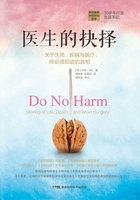
天堂与地狱近在咫尺:手术台上的意外
3个星期后,一个周日的晚上,我步伐沉重地走进了医院。与往常一样,我去探视第二天接受手术的那位女患者以及其他患者。事实上,我非常不情愿来到医院,那天我烦躁不安,一直在想,自己要硬着头皮去见她,直面她的焦虑。
每周日傍晚,我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医院,同时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这种感觉似乎只存在于从家通向医院的路上,无论我接手的是哪种手术,都会出现这种感觉。这次夜访只是例行公事,是工作多年形成的习惯。虽然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仍旧无法调整自己的心态,无法摆脱周六下午的心神不定与惴惴不安。当我沿着安静的后街骑行时,总感觉会有死亡或厄运降临。一旦见过患者,与他们稍加交谈,并说明一下第二天的手术将会如何进展,我便不再害怕,如释重负般地回到家里,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手术。
那位女患者躺在病房中拥挤的角落里,我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和她在一起,那样我就可以与他们俩同时交谈。不过,她却告诉我,她的丈夫先离开了,孩子们还在家里需要照顾。我们聊了几分钟,说明了手术的情况,既然她已经决定,就没有必要强调风险的事。风险在门诊已经说过了。不过,在患者签署复杂的手术知情同意书时,我还要提一下。
“你需要多休息。”我嘱咐她。“我肯定会的。这是当下最重要的事。”对于我的玩笑话,她笑着回应道。我在手术前夜经常与患者开这样的玩笑。她可能也清楚,在医院里所能做的就是安静休息,特别是第二天早晨还要动手术。
我见到了另外两名即将接受手术的患者,便又向他们介绍了手术的详细情况。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后,他们便声称将一切都托付给我了。焦虑具有传染性,信心也一样,走向医院的停车场时,我感到患者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就像一名船长一样:船上井井有条,大家各就各位,甲板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等着明天一系列的手术了。玩味着这些航海词语,我的心情很轻松,很快离开医院回家。
早晨例会后,我来到了麻醉室,患者躺在担架车上,正准备接受麻醉。
“早上好。”我语气尽量轻松些,“昨晚睡得好吗?”
“很好。”她平静地答道,“一晚上都挺好。”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
我只是想再次确认她是否真的了解手术所面临的风险,也许她只是勇敢、天真,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话。
在更衣室,我脱掉便装,换上手术服,一位同事也换好了衣服。我问他当天都安排了哪些手术。
“哦,只有几例背部手术。”他说,“你的是动脉瘤手术?”
“动脉瘤没有破,但最麻烦的是,如果患者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残废了,那你只能怪自己技术不精,毕竟术前他们一切安好。如果术前动脉瘤就破了,至少可以认定他们的残疾是先前的出血造成的。”
“确实,但没有破裂的动脉瘤往往更容易处理。”
我走进了手术室,注册医生杰夫正在把患者抬上手术台。虽然每年都会有一批美国医生到我们的科室进行为期一年的神经外科培训,但是很少见到西雅图人,不过杰夫就是其中一员。与大部分美国受训医生一样,他出类拔萃。杰夫把女患者的头紧箍在手术台上,铰链架上的3颗钢钉穿过头皮钉进头骨,这样患者的头就不会移动了。
我答应过她尽量少剃头发,杰夫就从前额剃起。之前我们都会把患者的头发剃光,这令他们看上去像个囚犯。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剃光头发会降低伤口感染率,但这已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怀疑,真正的理由是要让患者失去人性尊严,这样更有利于手术的进行。
我们尽可能少地剃掉了患者的头发之后,便到消毒槽洗手,然后戴上口罩、手套,穿上手术服,回到手术台前,开始手术。助手会给患者头部涂上抗菌剂,再用消毒毛巾盖住,这样就只能看到手术部位,同时消毒护士要安装、调试手术设备和工具。仅仅这些程序就要花费10分钟。
“刀,”我对消毒护士欧文说道,“我要开始手术了。”我又对手术台另一端的麻醉师大喊一声。
借助气动磨钻,30分钟后,我打开了患者的头骨,头骨内侧凹凸不平的部分则通过磨钻使其平滑。
“撤掉灯,把显微镜和手术操作椅拿过来!”我大声喊道。或许是出于兴奋,或许是我希望声音盖过手术室内仪器设备发出的格格声、嗡嗡声和嘶嘶声。
如今的双筒手术显微镜的确不可思议,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台仪器,就像一个技术好的手艺人钟爱自己称手的工具一样。它价值10万英镑,重达250千克,但是平衡度非常好。一旦固定好,这台显微镜就像一架吊车,带着勤学好问和丰富的思想靠近患者的头部,而我通过前头的双筒,向下就可以窥见患者的大脑。镜头轻如鸿毛,在我面前的平衡臂上自由移动,轻轻动动手指控制按钮就可以将其控制。镜头不仅具有放大功能,还可以照明,打开明亮的氙气灯,光束所到之处瞬间亮如白昼。
两名手术室护士弯下腰,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笨重的显微镜慢慢推到手术台前,我随即钻进后面的手术操作椅上。这是个带有可调节靠手的特制座椅。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敬畏。我并未完全失去那种天真的热情,正是带着这种热情,30年前我第一次目睹了动脉瘤手术的全过程。我就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跨上战马,追杀神话中的魔兽。从显微镜里看到患者大脑的镜像的确有些不可思议,镜头里的影像比外部的世界更清晰、更明显、更艳丽。阴暗的医院走廊、各种机关协会、文山会海和协议规章都属于庸俗的外部世界。显微镜镜片价格不菲,但它造就了不同寻常的深邃和清澈,使我对神秘的渴望愈加强烈。这完全是个人之见。此刻,手术团队就在我的四周,他们可以通过连在显微镜上的视频监视器看着我进行手术的全过程。我的助手就在我的身边顺着侧壁往下看。走廊里贴着许多有关医院管理的布告,每张布告中都公开宣扬团队合作和广泛交流的重要性,但对于我来说,这仍旧是一个人的战斗。
“好了,杰夫,我们继续。再给我拿一个牵开器。”我吩咐欧文。
我从中选了一个牵开器。它是薄薄的弹性钢片,一端像吃圆筒冰淇淋时用的扁平木片,而我要把它放在患者额叶下方。首先,我要向上提拉整个大脑脑体,使其离开颅骨底面(外科专业术语叫作“升位”)。在这一过程中,我必须小心翼翼,以毫米为单位进行提拉,进而大脑下方逐渐形成了一个狭小的空间,沿着这个空间我们可以慢慢接近那颗动脉瘤。多年来我一直借助显微镜做手术,它已经成为肢体的延伸。用到显微镜时,我就像顺着显微镜钻进了患者的大脑,显微工具的最前端就像我的指尖一样触到肿瘤。
我把颈动脉指给杰夫看,随后让欧文去拿显微剪。我小心翼翼地切开了大动脉周围蛛网膜的薄膜,正是这条动脉使人类的半个大脑充满了活力。
“多么奇妙的景观啊!”杰夫感叹道。这的确很奇妙。此时,我们在给动脉瘤做手术,灾难性的破裂还未出现,因此,这次对大脑的解剖做到了清晰和完美的水准。
“再来一个牵开器。”我吩咐道。
现在有了两个牵开器,我开始牵开额叶和颞叶,它们紧贴在一起,中间隔着一层薄膜,学名叫蛛网膜。该词源于希腊语,意为“蜘蛛”,因其形状如蛛网而得名。脑脊液(简称CSF)如液体水晶般清澈透明,在蛛网膜成绺的细丝中循环流动,在显微镜的灯光下,像白银一样闪闪发亮。透过脑脊液,可以看见光滑的大脑表面呈黄色,红色的毛细血管蚀刻在上面。这些毛细血管又称为小动脉,呈现出十分漂亮的枝杈状,就像从空中俯瞰所见江河的支流。光亮的暗紫色静脉在两个脑叶之间流过,向下直通大脑中动脉,最后到达动脉瘤。
“太棒了!”杰夫又叫起来。
“脑脊液里没有血也没有感染时,以前我们都把这种情况称为‘清亮’,”我对杰夫说,“可能现在得使用‘无菌’这个专业术语了。”
很快,我锁定了目标——大脑中动脉。实际上它的直径只有几毫米,但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很粗大、很吓人。这根粉红色大血管的起搏频率与心跳保持同步,它正一脸凶相地在那里悸动着。我要顺藤摸瓜深入下去,直抵位于大脑两叶之间的侧裂,去寻找深藏在那里的动脉瘤。动脉瘤就长在动脉血管上。如果动脉瘤破裂,分离大脑中动脉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因为新近的出血通常会使两片脑叶粘连在一起。由于分离过程杂乱无章、困难重重,我非常担心也许就在进行上述操作时,动脉瘤又一次破裂。
我分开两片脑叶,轻轻地把它们抻开,一手用显微剪切断了将脑叶绑在一起的蛛网膜,同时用一块吸盘清除血液和脑脊液。大脑皮质上有许多血管,为防止出血模糊视线、破坏大脑的血液供应,必须尽量避免撕破静脉和微小动脉。有时,如果分离工作过于困难、紧张或危险,我也会暂停,把手放在扶手上歇一会儿,看一眼正在接受手术的大脑。当我看着由脂肪、蛋白质和包围、缠绕在周围的血管组成的隆起团块时,我会想:人类的思想难道就是从这样的东西中产生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它们。这种思想本身就很疯狂、不可理喻,我便继续进行手术。
今天的分离比较容易,就像大脑装了拉链,轻松地就拉开了脑叶。因此,我只需要做一点点任务——迅速分离额叶和颞叶,几分钟后我们就看到了动脉瘤,它已经与周围的大脑和暗紫色的静脉完全脱离,在显微镜的明亮灯光照射下熠熠发亮。
“很好,它正等着我们呢,是吧?”我对杰夫说,同时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因为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在这种手术中,如果动脉瘤在医生接触之前就破裂,出血的情况极难控制:大脑瞬间肿胀,动脉血上涌,手术部位会立刻出现大量鲜血,形成红色的漩涡,透过这个红色的涡流,你必须竭尽全力找到动脉瘤的精确位置。由于显微镜的放大作用,你会感觉视线被一片血海吞噬。如果无法迅速止血,那么一夸脱(1夸脱=1.136升)血液从心脏进入大脑之后,患者在几分钟内就会失去数升血液。动脉瘤过早破裂引发的灾难使患者生还的希望极为渺茫。
“让我看看夹子。”我说。
欧文递给我一个金属盘,里面装着亮晶晶的钛金动脉瘤夹,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用以应对处于不同状态的动脉瘤。我从显微镜中看了看动脉瘤,又瞧了瞧这些夹子,然后视线又转回到动脉瘤。
“6毫米,短直角的。”我吩咐道。
欧文挑了一个夹子装在了持夹器上。持夹器结构简单,有一个把手和两个弯曲的弹簧片,两端啮合在一起。夹子会装在把手的顶端,你需要做的就是按压把手的弹簧,使夹子的夹片张开,小心地把夹片放在动脉瘤的颈部,然后轻轻地使弹簧片在手中分开,这样夹片就锁住了动脉瘤,封住了动脉瘤寄生的动脉,血液无法进入其中。最后使持夹器的弹簧片完全分开,夹子一旦从持夹器上分离,你就可以收回持夹器,而夹子则夹在动脉瘤上,伴随患者一生。
那是我们期望发生的情况,至少在我过去做过的上百次类似的手术中经常出现。
这颗动脉瘤看上去很容易处理,所以我请杰夫来做。首先,我要从手术操作椅上下来,这样他才能接替我。我的助手和我一样,虽然动脉瘤向我们发出的召唤是致命的,但也非常诱人,我们对此很敏感。他们也很渴望亲手做一例类似的手术。然而,现在的绝大多数动脉瘤手术都是从内部栓塞而不是从外部夹住,这就意味着我无法为他们提供常规培训。偶尔有一例符合培训要求的手术,我也只能让他们做最轻松、最简单的部分,而且还要在我寸步不离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
杰夫就位后,护士递给他装好夹子的持夹器,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移动夹子靠近动脉瘤,看来一切正常,顺着助手的镜臂,我紧张地看到夹子围着动脉瘤在不停地晃动。
无论是心理压力还是技术难度,总之,培训一名初级医生要比自己亲自手术难上100倍。
过了一会儿,也就是几秒钟,但那感觉绝非几秒,我实在忍不住了。
“真是笨手笨脚,不好意思,还是让我来吧。”杰夫一声不吭地从座椅上滑下来。他脾气急躁,经常向领导抱怨,更别说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冷静。我们又换回了之前的位置。
我接过持夹器,朝动脉瘤上放。我按了一下把手上的弹簧,但是没有反应。
“妈的,夹子没动!”
“我刚才就这样。”杰夫一脸委屈地说道。
“真是见鬼了!好吧,给我换一个持夹器。”
这一次我很轻松地张开了夹子,将夹片夹在了动脉瘤上。我一松手,夹片闭合,正好夹住了动脉瘤。动脉瘤被制服了,皱缩起来,因为里面已经没有高压的动脉血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当动脉瘤最终得到妥善的处置时,我总会如此。但令我感到恐惧的是,第二个持夹器有着更加致命的缺陷,夹子夹紧动脉瘤后,持夹器无法释放夹子,所以我的手一动也不敢动,唯恐把这颗微小、脆弱的动脉瘤从大脑中动脉上撕扯下来,造成大出血。我坐在座椅上一动不动,手也似乎僵在那里。如果动脉瘤被意外地从寄生的动脉上撕下来,通常为了止血,医生只能牺牲这根动脉,但这会导致患者发生严重的脑卒中。
我大声诅咒着,但尽力保持手的平衡。
“他妈的,现在怎么办?”我并没有对单独某一个人大喊。几秒钟(这几秒有如几分钟那样漫长)过后,我意识到除了冒着将动脉瘤弄破的风险摘掉夹子之外,别无选择。我重新闭合了持夹器的把手,令人备感宽慰的是,夹片很轻松就打开了,动脉瘤又迅速鼓了起来、恢复活力,动脉血随即涌入。我感觉它好像在戏弄我,眼看就要破裂了,但就是没有破。我身子靠在座椅上,嘴里骂得更厉害了,随手把那个恼人的工具扔到了外面。
“以前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大叫着,但很快平静下来,笑着对欧文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三次把工具扔在地上。”
我要再等几分钟,另外找一把持夹器。造成持夹器失灵的原因也很奇怪,竟然是铰合处僵硬。后来我才想起30年前曾与一名医生交谈,那时我还在他手下受训。他告诉我,有一次他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的患者远没有我的患者那样幸运,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在使用持夹器之前会检查的医生。
医生们总是津津乐道“医学的艺术与严谨”。我向来不以为意,并认为这个词组非常做作。我更喜欢将从事的工作视为一门手艺。夹动脉瘤就是一门手艺,这需要多年的练习。当动脉瘤出现在你的面前时,便需要你下手处理。然而,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追猎,仍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亟待处理:如何用夹子夹住动脉瘤。更重要的是,你是否完全夹住了动脉瘤的颈部,而并未损坏它寄生的那根关乎性命的动脉。
这颗动脉瘤看起来很容易处理,但我的神经过于紧张,不敢再让助手继续,于是我拿了一把新的持夹器,亲自操作。这颗动脉瘤的形状使夹子无法完全穿过其颈部,我注意到有一部分瘤体超出了夹子边缘。
“没夹好。”杰夫提醒我。
“我知道!”我厉声道。
现在是手术的攻坚时刻,我稍微打开夹子,重新选择最佳的位置,但在这一过程中,动脉瘤可能会被撕裂,那时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动脉血像喷泉一样透过显微镜向自己涌来。另一方面,如果动脉瘤颈部没有完全锁闭,也有一定的危险,很难确定危险系数,但患者将来某一时刻会出现第二次大出血。
一位著名的英国外科医生曾经说过,外科医生必须要拥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狮子般强大的心脏、女人般精巧的双手。上述品质我都不曾拥有,相反,在动脉瘤手术的关键时刻,我必须要有一股强烈的意愿,那就是想方设法把手术完成,将夹子放在合适的位置,但是有可能放得并不完美。
“优秀的敌人是卓越。”我对助手大声咆哮。对他们来说,手术仅仅是一场精彩刺激的观猎。看到我处理动脉瘤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他们会获得某些快感,因为他们不必收拾动脉瘤撕裂后留下的烂摊子。如果那种事真的发生了,他们就会兴奋地看着自己的上司在血海中挣扎。当我还是一个实习生时,就很享受这种快感。另外,在我巡视病房时,看到了受到伤害的患者,他们也体会不到我心里承受的煎熬,也不必为发生的灾难承担任何责任。
“哦,很好。”我通常会这样回应他们的漠然,事实上我为这些助手感到可耻。不过,我又想起了过去上百例手术中夹过的动脉瘤,与大多数的神经外科医生一样,通过实战演练我成了一个有经验的老手。一些刚刚入行的医生过于谨慎,只有经过无数次的实践练习,他们才能意识到一定可以渡过难关,但起初,一切看起来却是如此恐怖、如此艰难。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夹子,沿着动脉瘤轻轻地向前推进。
“还是有个地方出来了。”杰夫说道。
有时遇到这种情况,以往动脉瘤手术的那些梦魇就会在我眼前像幽灵一样一队一队经过,在记忆中已经消失多年的容貌、名字与悲伤的家属又突然闪现。当我努力挣扎着心平气和地完成手术、直面大出血造成的恐惧时,在内心深处某些无意识的地方,所有的幽灵都聚在一处,关注着我,而我要迅速做出决定是否再重新放夹子。同情与冷漠、内心的恐惧与精湛的医术之间将上演一番较量。
我再一次重放夹子,看来这次终于成功了。
“这次可以了。”我说。
“棒极了!”杰夫兴奋地说,但有些遗憾自己没有亲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