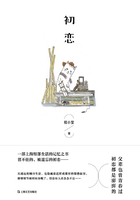
第7章
我的生活从上海北站开始。火车站,梦和冒险经历的起始。火车站的铃声和汽笛。“月台”这名字真好听。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比这更美妙的名字。站在月台上,可以看见边上交错岔开的铁轨,戴着帽子的信号灯。所有的一切令人着迷。持续的铃声一中断,火车头就要发出撕裂般的尖叫,红色的车轮,白色的边带,轮子就是用一根铁手臂带动的;火车头老是要喘着粗气,或者发出短促的一声,一团白汽像一朵云似的飘起来,很好看的。远处的蒸汽机车头,喷着蒸汽开过来,机头里总归会有一个司机,从里面探出半个身子,往前方张望;绿色的列车像一条长蛇,游移着。在一列行动起来的列车车窗前,我经常会看见摆着的吃食和饮料。一张脸在望着窗外;在另一扇窗口,是卧铺,立着一个穿着睡衣的老头。一列火车开走了,月台上的人即刻散去。我经常会想,这些人,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晓得在这个城市活下来的我,是认得生活了。这一路上,开始有许多记认。
有许多里弄加工厂,糊纸盒、绕线圈、敲小铁床的床绷,让我这一路上走着,便听着乒乓乒乓的敲打之声。我站在自家的弄堂口过街楼下,一个铅皮匠的摊头边,整个下午看着铅皮匠用一块方方正正的木块敲打铁皮。这是我对做工之人的最初印象。那种锅底、铅桶、痰盂、浇花的壶和喊口号的喇叭筒,就出自这样的手。这让我在后来读到“能工巧匠”这个词儿的时候,耳畔就会有乒乓乒乓的声响。这便是活儿。
做工之人,总要弄出些声响。是修锁配钥匙的担子,铿锵铿锵地晃来,小钢锉哧哧地响,让人牙根儿咝咝地发痒;箍桶的,小锤对着凿子笃笃地敲着,节奏是明快的,绕着木桶兜一圈,间或,箍桶的一扭头,以为他要对我说什么,却听得一声响亮的吆喝——箍桶哦!至于修自行车的主儿,把个废钢圈挂在树杈上、路牌上,有事无事地铛铛敲几下,地上掼着各式扳头,活络扳头、套筒扳头、内六角外六角扳头……
对面的弄堂,有爆炒米花的声响,吸引了我们。我和金华经常会为我们拟定的出发而准备干粮。我们用我们的“特务经费”,用她从家里偷出来的米、黄豆、玉米,去爆米花。我们成群结队跑过去,地上是一溜竹篮头,里面是个小铁罐,盛着米或玉米、年糕片、蚕豆、黄豆……破旧的炉灶里,火焰随着风箱的啪嗒啪嗒声,发出哔哔剥剥的声音。爆米花的一只手摇着炸弹似的生铁闷罐,一只手拉风箱,脸上是一道一道污黑的汗水,埋头想自己的心事,然而,身子是很稳重的。谁也没注意到,他会留神生铁疙瘩上的一个压力表,到了某个时分,便用力支起生铁闷罐,随手拖过一个脏得不能再脏的破麻袋,将生铁闷罐口对着麻袋里面,以一个熟练的动作封牢,抄起一根铁管套住生铁闷罐的口盖,跟着是一声“炒米花——响啦!”。
我们一哄四下散开,蜷缩在墙根底下,捂着耳。随着一声爆响,是香喷喷的味道,让我的鼻子一阵紧忙,鼻翼都瘪进去了。
在那时,一个小男孩默默等待着的、注视着的、想念着的,便是这样的破麻袋里倒出来的白花花的炒米花。有一个星期里,我们的零食便是这。
如果是爆黄豆,便吃黄豆,便会产生大量的屁;大量的屁跟着我们到各自的家、学校、电影院、公共汽车上,散发出大量的臭气,当人在揣度这些臭气的来源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
还有,便是对所有做工之人伟岸的劳动姿态,打心眼里深深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