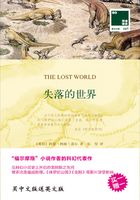
第4章 这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
门刚一关上,查林杰夫人就像一颗子弹一样从餐厅里冲了出来。这个小个子女人的火爆脾气爆发了。她挡住自己丈夫的去路,那情形就像一只发怒的母鸡挡在了一只斗牛犬的面前。显然,她只看见我出去了,没有注意到我回来了。
“你这个残暴的家伙,乔治!”她厉声说,“多好的小伙子啊,你也把他打伤了。”
他用大拇指往后一指。
“他就在这儿,安全而且完好无损。”
她被弄得有点儿糊涂了。
“真不好意思,我没看见您。”
“别担心,女士,我完全不介意。”
“您这可怜的脸都被他弄伤了!噢,乔治,你看看你有多残暴啊!一天到晚除了丑闻就是丑闻。所有人都憎恨你,取笑你。我的耐心都让你磨没了,我真受够了。”
“家丑。”他嘟囔着。
“还有谁不知道啊。”她大叫了出来,“你去问问这条街的人——整个伦敦市的人——走开,奥斯丁,这儿不需要你。你以为人家不会对你议论纷纷吗?你的尊严呢?你,本该在一所很好的大学去当皇家教授,受到几千学生的尊敬。你的尊严呢,乔治?”
“那你的呢,我亲爱的?”
“你太过分了!你这个恶棍——狂暴的恶棍——这就是你现在的样子。”
“你规矩点儿,杰西。”
“狂暴、喧嚣的混账!”
“够了!反省反省吧!”
真是出乎我意料,他竟然一把把他的妻子抓起来,放在了屋角的一个黑色大理石台子上。那个台子至少有七英尺高,而且又很窄,她坐在上面根本没法保持平衡。还有什么比她在那上面的时候因愤怒而抽搐的脸、悬空的双脚以及因为害怕和沮丧而显得僵直的身体更加可笑的吗?我简直想象不出。
“把我放下来!”她哀号着。
“你要说‘请’。”
“你这个恶棍,乔治!马上把我放下来!”
“到书房里来,马龙先生。”
“真的,先生——”我看着悬在台子上面的女士说。
“马龙先生为你求情呢,杰西。你说‘请’,我就放你下来。”
“噢,你这个恶棍!请!请!”
他一把把她拎下来,就像拎一只金丝雀一样。
“你得规矩点儿,亲爱的。马龙先生是位新闻工作者。明天他就会把情况全都发表出来,在我们这个社区多卖上十几份。‘高层生活的奇遇’——你在那台子上坐着确实感觉挺高,不是吗?然后再加一个副标题,‘怪异家庭一瞥’。他是个食腐动物,就是这位马龙先生,就是以吃腐肉为生,跟他的同类们一样——恶魔圈子里的猪猡。就是这样,马龙——什么来着?”
“您真是让人难以忍受!”我大发雷霆。
他发出一阵大笑。
“我们马上就要结成同盟了,”他大声喊道,看了看他的妻子,又看了看我,鼓了鼓他那宽大的胸膛。随后,他又突然改变了口气,“请原谅我们这孩子气的家庭玩笑,马龙先生。我叫你回来不是想把你搅进我们这小小的家庭纠纷,而是有更严肃的目的。快走开吧,小妇人,别烦了。”他把两只大手搭在妻子的双肩上。“你说的都没错。如果我听了你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那样我就不是乔治·爱德华·查林杰了。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亲爱的,但是乔治·爱德华·查林杰就这一个。所以就随他吧。”他突然给了她响亮的一吻,这比他之前暴力的行为更让我感到尴尬。“现在,马龙先生,”他表现出很有尊严的样子,继续说,“您这边请。”
我们又回到了十分钟前才喧闹着离开的那个房间。教授轻轻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朝一张扶手椅指了指让我坐过去,将一个雪茄盒子推到我的面前,打开了盖子。
“纯正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圣胡安,”他说,“像你这样容易激动的人来点儿麻醉药好些。天啊!别咬!切——小心点儿切!现在,放松,认真听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耐心等待,我会给你机会的。”
“首先,虽然你现在回到了我家,那也不说明之前对你的驱逐是不公正的,”他的胡子向前伸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在挑衅一般,“就像我说的,你之前被我赶出去也是理所应当。之所以把你叫回来是因为基于你对那个爱管闲事的警察的回答,我似乎对你产生了一丝好感——至少是比你的那些同行们好一些。通过承认这件事情是你的错,你表现出了一定的超然精神和宽宏大量,让我不由地产生了一丝赞赏之意。你不幸所属的那个人类的亚种是我平时根本看不上眼的。但是你那句话使你的境界突然得到了提升。你这才获得了我的认真关注。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请你跟我回来,因为我愿意对你做进一步的了解。请你把烟灰弹到你左肘边那个竹制桌子上的日式小盘里,谢谢。”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像一位教授在给他的学生上课一样。他旋转他的转椅面对着我,像只巨大的牛蛙一样喷着气,头朝后仰,眼皮低垂下来,一副高傲的样子。突然,他朝一边转过去,呈现在我眼前的是那乱成一团的头发和一只通红的支棱着的耳朵。他在桌上的一堆废纸中翻了一通,最后,手里拿着一本破破烂烂的素描簿重新朝我转过来。
“我接下来要跟你说说南美洲的事情,”他说,“请你尽量不要插话。首先,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要跟你说的一切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在任何公共场合提起,而我是绝不可能允许你这样做的。明白了吗?”
“这很难做到,”我说,“当然了,您这么考虑是很明智的——”
他重新把素描簿放在桌子上。
“那就没必要继续了,”他说,“祝你早安。”
“不,不!”我大喊,“任何条件我都答应。只要我能看见,我别无选择。”
“一个人都不可以。”他说。
“嗯,那么,我答应。”
“你保证?”
“保证。”
他用轻蔑的目光看着我,满是怀疑的神色。
“但是,我怎么知道你说话算话呢?”他说。
“说实话,先生,”我气愤地大喊,“您也太过分了!我一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羞辱。”
对于我的爆发,他表现出来的兴趣倒是多于恼怒。
“圆头,”他嘟囔着,“头颅短小,灰色眼睛,黑头发,黑人特征。凯尔特人吧?我猜。”
“我是爱尔兰人,先生。”
“纯正爱尔兰人?”
“是的,先生。”
“当然了,显而易见。让我想想,你向我承诺了我的秘密会得到尊重?那个秘密,我要说,根本还没有完整的结论。但是我要给你介绍几点,还是很有意思的。首先,你可能知道,两年前我去了趟南美洲——那将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次经典之旅,对吧?那次旅行的目的是要验证华莱士和贝茨得出的一些结论。只有在他们做出那些发现的相同条件下对他们所报告的现象进行观察,验证才有意义。即使我的考察没有结果这也依然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但是考察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引发了探究的新起点。”
“你可能知道——又或许,你还处于半懵懂的年龄,所以也有可能不知道——围绕亚马逊某些地段有一个现在还处于半开发状态的国家,它有很多附属国,有一些在地图上甚至根本没有标明,现在都已经被河水淹没了。我的任务就是去寻访这个不为人知的国家,研究那里的动物群。我提前拿到了多达几章的资料。那是一项动物学界伟大的、不朽的工作,足以证明我人生的意义。工作完成之后,在我返回的途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其中一个附属国当地的小村庄度过了一个夜晚——附属国的地点和名字我就不提了。当地居民都是柯克马的土著居民,那是一个和蔼可亲但是品位低俗的民族,他们的智力连普通的伦敦市民都比不上。在我溯河而上的途中,我帮他们治愈了一些疾病,并用我的个性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他们热切地盼望我归来倒是意料之中的事。从他们的表现我可以看出,有人急需我医疗方面的帮助。我跟随酋长来到一座小屋前。进门之后我发现,那个等待我来救治的人那时已经去世了。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个人竟然不是当地人,而是一个白人;真的,是一个很纯正的白人,他有着亚麻色的头发,并且具有一些白化病的特征。他衣衫褴褛,憔悴不堪,显然是忍受了很长时间的病痛折磨。经过当地人解释之后我才知道,他们也并不认识他,在他独自从森林里来到他们村庄的时候,他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个人的背包就放在长椅旁边,我打开检查了一下里面的物品。包里的一个标签上写着他的名字——梅普尔·怀特,湖滨大道,底特律,密歇根州。这是一个令我崇敬之至的名字。如果这项事业最终得以完成,那么我的名字也将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从背包里的东西看,很明显这个人在考察的过程中也是一个艺术家和诗人。背包里有一些小段的诗歌。我不敢说自己对这种东西很懂,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似乎没有什么价值。背包里还发现了一些很普通的河流风景的照片,一个绘具箱,一盒彩色粉笔,几把刷子,那只放在我墨水台上的弯骨,一卷巴克斯特的‘飞蛾与蝴蝶’,一支廉价的左轮手枪,还有几枚子弹。关于个人装备,他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是在旅行途中弄丢了。这就是这位美国的吉普赛人留下的所有东西。
“当我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他那破旧的外套里露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素描簿,当时它就已经像现在这样残破不堪了。真的,我拿到这个本子时简直如获至宝,把它看得比莎士比亚的原著都珍贵。现在,我要把它交到你的手里,请你一页一页认真看下去。”
他点了一支雪茄,靠在椅背上,用挑剔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关注着我对这份资料产生的反应。
我打开了素描簿,期待着可能会看见某种启示,但是具体是哪种类型的启示我也想象不出来。然而,第一页却有些让我失望,只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身穿粗呢短外套的肥胖男人,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吉米·科尔夫在邮船上。”接下来的几页是一些素描,画的是一些土著居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又出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乐呵呵的牧师,身材有点发福,头戴一顶铲型宽边帽,对面坐着一个清瘦的欧洲人。照片下的注释写着:“与弗拉·克里斯托弗在罗萨里奥共进午餐。”接着又有几页是关于妇女和儿童的研究,然后是一连串的动物图画,下面的注释有“沙滩上的海牛”,“海龟和海龟蛋”,“米瑞缇棕榈树下的黑色刺鼠”——一种类似猪的动物;最后,是两页关于一种长着长鼻子的蜥蜴类动物的研究情况。我也看不出那是什么动物,于是我对教授说:“这肯定是鳄鱼吧?”
“短吻鳄!短吻鳄!在南美洲都根本不会有真正的鳄鱼。他们之间的区别——”
“我的意思是我看不出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你刚才所说的话啊。”
他沉着地笑了笑。
“再看看下一页。”他说。
我还是没有办法领会。那一页画得满满的,都是风景,还大致地涂了颜色——显然是户外艺术家为了将来更加详尽地进行考察而画的。最突出的位置是一片浅绿色的羽状植被,倾斜着一路向上延伸,尽头是一片暗红色的悬崖,悬崖是一条一条的,很像我见过的玄武岩结构。岩石一直延伸过去,布满了整个背景。其中有一块孤立的金字塔形山峰,上面长着一棵大树,由中间的一个裂缝与悬崖的主体隔开。在这些悬崖的后面,是炙热的蓝天。而这些血色的悬崖顶上也生长着一些绿色的植被,像是镶上了一圈绿色的边儿。
“怎么样?”他问。
“这结构当然是很有意思,”我说,“但是凭我这点有限的地理知识还判断不出有什么妙处。”
“妙处!”他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个结构可以算得上的是与众不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得到这种结构存在的可能性。现在,看下一页。”
我又翻过了一页,这一看我直接惊呼了一声。这一页上画满了我见到过的最奇特的生物。这东西只有瘾君子在吸了鸦片,神志不清的时候才想象得到。它长着家禽一样的头,身体像一只肿胀的蜥蜴,拖曳的尾巴上面长有一些向上的长钉,弯曲的后背上也长有一些高高的波浪齿,那样子就像十几个公鸡脖子上的肉垂连成一排长在那里。这只动物前面是一个矮得可笑的人,或者是个侏儒吧,正站在那里愣愣地盯着那东西。
“嗯,你对这个怎么看?”他一边带着胜利的态度摩擦着双手一边大喊。
“这是个怪物吧——奇形怪状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只动物呢?”
“我猜是为了换点儿杜松子酒喝吧。”
“噢,这就是你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了,是吗?”
“那么,先生,你的解释是什么?”
“有一点很明显,这个生物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生活中真实场景的写照。”
要不是想到我们很可能会再进行一次“转轮烟花滚”,我肯定就放声大笑了。
“那当然,”我说,就像在迎合一个傻子的无稽之谈。“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又继续说,“这个小个子的人确实让我不明白。如果他长得像个土著居民,我们还可以把他当作美洲的俾格米人(身材十分矮小的一个种族)存在的证据,但是从他戴着的遮阳帽看,他却应该是个欧洲人。”
他像一头气愤的水牛一样咆哮起来。“你真的是挑战我的极限了,”他说,“你真是让我开了眼界。脑神经麻痹!精神迟钝!太好了!”
他当时的表现太可笑了,我甚至都生不起气来。确实,跟他生气纯粹就是浪费精力,因为如果你要跟他生气的话就要一直生下去了。我厌倦地笑了笑,说:“这个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子很小。”
“看这儿!”他身子前倾,用一根长满汗毛,像一根香肠一样粗大的手指指着图画,大声嚷道,“你看见这只动物身后那棵植物了吗?我想你以为这是一株蒲公英或者球芽甘蓝什么的吧?嗯,那其实是一株象牙棕榈,与动物之间的距离是大概五十到六十英尺。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个人是有意被画上去的。要想站在这个猛兽前面活着把它画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把自己画进去就是要提供一个参照物。据估计,他的身高应该在五英尺以上。据估计那棵树的高度是他身高的十倍。”
“天啊!”我禁不住大喊出来,“那么,你觉得那只动物是——不会吧,就连查林十字街站那么大的地方也容纳不下这样的一只巨兽啊!”
“除去夸张的因素,画面上这只动物显然是它们种群中一个发育良好的范例。”教授洋洋自得地说。
“但是,”我大声说,“人类先前的经验也不能因为一张草图就被全盘否定了啊。”——我又往后翻了一页,发现后面没有什么内容了——“一个流浪的美国艺术家,没准画这张图的时候还吸了大麻,或者是因为高烧而神志不清,又或者只是出于他异想天开的想象而已。作为一名科学家,你不能根据这些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啊。”
为了继续回答我,教授从书架上拿下来一本书。
“这是我一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写的专题论文,他叫雷·蓝吉斯特!”他说,“这有一张插图你可能会感兴趣。啊,对,就是这儿!图片下注明:‘侏罗纪恐龙中剑龙可能的真实外貌。仅后腿的高度就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身高的两倍。’那么,关于这个你怎么看?”他把打开的书递到我的手上。
我先看了看图片,图片中所画的那种已经灭绝了的动物的确是跟那位无名艺术家画的那张草图很相像。
“这的确是非同凡响。”我说。
“但是你还是不承认这是最终结论吗?”
“当然了,这可能就是一个巧合,或者,那个美国人之前看见过类似的图片,在他的脑子里还有印象。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这种幻想是很容易出现的。”
“很好,”教授宽容地说,“我们暂且放下这个不谈。现在,请你来看看这根骨头。”这是那名死者的遗物。他将骨头递到我的面前。那根骨头大约六英寸长,比我的拇指要粗一些,一头有一些干了的软骨组织。
“你看这根骨头属于哪种已知的生物?”教授问。
我仔细看了看,努力地回忆着一些已被遗忘的知识。
“这可能是一根较粗的人类锁骨吧。”我说。
教授轻蔑地摆了摆手,表示不赞成。
“人类的锁骨是弯的。这根是直的。它的表面上有一个沟槽,这表示这里有一根肌腱,所以不可能是锁骨。”
“那我必须要坦白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不必因为暴露了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因为说实话,我认为全肯辛顿南区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叫出它的名字。”他又从药盒里拿出一块像豆子一样大小的骨头,“据我判断,你手中拿着的那根骨头就相当于人身上的这块骨头。依此你可以大致判断这只动物的大小。从软骨组织可以看出,这不是化石标本,而应该是新近的。对此你有什么话说吗?”
“当然了,有可能是大象——”
他皱起眉头,呲牙咧嘴,好像被谁弄疼了一样。
“别!在南美洲不要提大象。即便是在这寄宿学校盛行的时代——”
“嗯,”我打断了他,“那就是某种体型较大的南美动物——貘,比如说。”
“年轻人,你要知道,我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是很精通的。这根骨头既不属于貘,也不属于任何动物学界已知的动物。它应该属于一种体形很大,非常强壮,而且也非常凶猛的动物,这种动物存在于地球上,却一直没能引起科学界的注意。你还是不信吗?”
“至少我现在很感兴趣了。”
“那么你这个人还不算无可救药。我感觉你这个人骨子里还是有些理智的,所以,我愿意花些耐心帮你挖掘一下。现在,我们不谈那沉闷乏味的美洲了,听我继续讲下去。你应该也能想象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去做更深层次的挖掘的话我是不会甘心离开亚马逊的。根据一些迹象,我大致推断出了那名死亡的旅行者行进的方向。我主要依据的是当地的一些传说,因为我发现在当地所有河流部落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一片神奇的土地的传言。库鲁普利,你肯定听说过吧?”
“没有。”
“库鲁普利是树木之灵,很可怕,很恶毒,人们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能够说出它是什么形状或是什么性质,但是在亚马逊流域一提起来就令人心惊胆战。现在,所有的部落对于库鲁普利生存的地点都达成了一致,认为那个美国人就来自那个方向。那个方向一定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东西。而弄清楚那种东西是什么就是我的工作任务。”
“那你是怎么做的?”我先前的轻率无礼此时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个人影响力很大,让人不由自主地注意他,对他产生尊敬的情绪。
“当地人对这件事比较忌讳,甚至根本不愿意谈起,我通过我的见识来说服他们,给他们送礼物,并且,我必须得承认,也用了一些胁迫的手段,终于找到了两名向导。过程我就无须赘述了,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冒险,走过了不知道多远的距离,我们一直坚持着方向,最终来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被记载过,也从来没有被我那些运气不佳的先辈们发现。能否麻烦你看看这个?”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大概有半个盘子那么大。
“照片有点儿损坏了,这是因为,”他说,“在我们渡河的时候,船翻了,装着还未冲洗出来的胶卷的箱子给摔坏了。结果是灾难性的,几乎所有胶卷都毁掉了——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这张就是仅存的几张之一。有人解释为证据不足或是畸形,这还都可以接受。有人认为是我造的假,我也没有心情跟这些人争辩。”
照片已经褪色得不成样子了,又模模糊糊的,很容易被那些心存不善的评论家解释错误。照片上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色,经过一番仔细辨认,我发现那是一片绵延距离很长,又很高大的悬崖,远远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瀑布,前景是一片有点倾斜的平原,长着一些树木。
“我想这就是那张画上所画的那个地方吧。”我说。
“就是那儿。”教授回答说,“我在那儿找到了那家伙露营的痕迹。现在来看这个。”
那是同一地点拉近后拍的一张照片,但是照片已经很不清楚了。但我还是能够确定无疑地看出一个独立的、顶上长着一棵树的高峰,独立于后面的悬崖。
“我对此确定无疑。”我说。
“嗯,终于有所突破了,”他说,“我们还是有进展的,不是吗?那么,你现在能不能注意看一下那个山峰的顶部?你看到什么了吗?”
“一棵大树。”
“那树上呢?”
“一只大鸟。”我说。
他递给我一支放大镜。
“没错,”我透过放大镜看了看,“一只大鸟站在树上。这鸟的喙似乎很大。我觉得是一只鹈鹕吧。”
“我真的没法恭维你的眼力,”教授说,“那不是鹈鹕,也不是什么鸟。我要说我后来把那东西打下来了,你一定会很感兴趣吧。那是唯一一件我能带回来的证据,证明我所有的那些经历。”
“那么它在你的手上?”这下终于有了确凿的证据了。
“曾经在我手上。但是就是在那次翻船事故中,不仅我的照片被毁掉了,这东西也不幸被弄丢了。那次我真是损失了不少东西。它消失在激流里的时候我拼命地想要把它抢回来,但是只抓住了它翅膀的一部分。被冲上岸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知觉,但我还是把我的宝贝标本紧紧地抓在手中。现在放在你面前的就是。”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那看起来像是一只巨大蝙蝠翅膀的上半部分,至少有两英尺长,是一根弯曲的骨头,下面还有一层薄膜似的东西。
“一只巨大的蝙蝠吧!”我说。
“根本不沾边儿,”教授严厉地说,“作为一个生活在教育与科学氛围里的人,我简直难以相信动物学的基本知识竟然普及得这么差。可能你不了解比较解剖学的基本知识,你都不知道鸟的翅膀其实是他的前臂,而蝙蝠的翅膀是三根延长出来的手指,中间以薄膜相连吗?那么,这样的话,这根骨头显然不是前臂了,你自己也能看到,这个薄膜是长在一根骨头上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一只蝙蝠。那么,如果它既不是鸟也不是蝙蝠的话,会是什么呢?”
我那点儿可怜的知识储备早就不够用了。
“我真不知道。”我说。
他又打开了先前向我提到过的那本书。
“看这儿,”他指着图片中一只正在飞行的怪物说,“这张图片画的是一只双型齿翼龙,或是翼龙,是侏罗纪时期一种能够飞行的爬行动物。下一页是它的翅膀结构的图解。麻烦你将它与你手中的标本对照一下。”
我低头一看,一种惊异的感觉像电流一样瞬间传遍了全身,我信了。绝对就是那个东西。这几样证据加在一起让人无法反驳。草图、照片、教授的讲述,现在再加上真实的标本——这些证据已经足够了。我把自己的看法表达了出来——带着热情,因为我感觉教授之前确实是被人们误解了。他靠在椅子靠背上,眼睛低垂,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似乎在享受着这突然出现的一丝阳光。
“这可是我听到过的最重大的事件了!”我说。此刻,虽然我对科学依然没有产生激情,但是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激情确实被激发出来了。“这个发现太重大了。您发现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可以算得上是科学界的哥伦布了。我为我之前表现出来的怀疑郑重地道歉。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一看到这些证据就明白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
教授满意地“嗯”了一声。
“那么,先生,你后来又做了什么呢?”
“当时正是雨季,马龙先生,我的补给已经耗尽了。我对那个大悬崖几个地方进行了探测,根本找不到可以攀登的地方。那块我看见和打下翼龙的金字塔形石头还有爬上去的可能。我也算是一个攀岩能手,我拼尽全力爬到了那块山峰的半山腰。从那个高度看来,我对那崖壁顶上的平坦地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块平地很大,向东向西都无法看到尽头。下面是一片沼泽和丛林密布的区域,蛇虫遍地,成了这个独立的国度的天然屏障。”
“你还看到其他生命的迹象了吗?”
“没有,先生,我没有,但是在我们在悬崖脚下扎营的那一周里,我们听到有很奇怪的声音从上面传出来。”
“那么那个美国人画的那种动物呢?您怎么解释?”
“我们只能假设他想方设法爬到了最高点,在那里看到了那只动物。因此,我们知道肯定有一条能够让我们爬上去的路。当然我们也知道,那肯定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否则那些动物早就下来踏平了周围的国家。这样解释还算清楚吗?”
“但是它们是怎么到了那儿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教授说,“只能有一种解释。南美洲这个地方,你可能也听说过,是一片由花岗岩组成的陆地。在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曾经突然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这些悬崖,我要说,都是玄武岩,因此,属于火成岩。一个区域,可能大概有苏塞克斯(英格兰东南部一旧郡名)那么大吧,带着那上面的所有生物被抬升了起来,又因为四周有陡峭的悬崖阻隔,使它完全脱离了四周陆地的影响。那么结果是什么?平常意义上的自然法则失去了作用。广泛影响到这个世界上的物竞生存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弱化或改变。结果本该消失的物种被保留了下来。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翼龙也好,剑龙也好,都是存在于侏罗纪时期,在生命演化的过程中都属于很古老的物种。是那些特殊而又偶然的条件使它们违反了自然规律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你掌握的证据确凿,这是肯定的。你只需要把它们展示给专家就可以了。”
“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多么天真啊。”教授苦涩地说,“我只能告诉你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四处碰壁,处处遭遇怀疑,原因部分来自于愚蠢,部分来自于嫉妒。先生,向任何人阿谀奉承或是在遭到怀疑的时候向人家去解释证实,这都不是我的性格。在遭遇第一次的质疑之后,我就不再屈尊向人家展示我掌握的确凿证据了。我非常讨厌这个话题——我不想再谈下去了。当那些像你一样的人,那些代表着公众愚蠢的好奇心的人,来探听我的隐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到有尊严地面对他们。我这个人,我必须得承认,脾气火爆,在遇到挑衅的情况下又有暴力倾向。恐怕你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我摸了摸受伤的眼睛,没有说话。
“关于这一点我的夫人经常劝我,但是我觉得任何有尊严的人都应该有我这样的感觉。但是,今晚,我决定尝试一下控制我的情绪,于是我邀请你来看了这些东西。”他将桌子上的一张卡片递给我,“你看,珀西瓦尔·沃尔德伦先生,一位颇有声望的博物学者,将于今晚八点半在动物学研究会的报告大厅做一场题目为《年代的记录》的报告。我受邀作为特邀嘉宾,到讲台上对演讲者进行公开鸣谢。到时候,我会把握住这个宣传自我的机会,通过运用我非凡的机智和谨慎,我会说上几句话,这样就可能会引起公众一定的关注,并且激发他们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了解的欲望。不会是什么有争议的观点,你明白,就是给他们一点儿暗示,表象之下还有更多有待于挖掘的东西。我会尽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要看看通过这样的自制,我能否获得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那我能去吗?”我热切地问。
“嗯,当然了。”他诚挚地说。他拥有着一种非凡的和蔼气质,其影响力几乎与他的暴力一样强大。他那仁慈的笑容给人的感觉相当美好,他那半闭的眼睛和浓黑的胡须之间露出的双颊会突然变成两只红苹果的模样。“无论如何要来。对我来说,知道大厅里至少有一个人是支持我的,心里会感觉比较欣慰,尽管这个支持者对这个问题了解不多,懵懵懂懂。尽管沃尔德伦这个人根本就是个骗子,但是他还是有不少的追随者的,因此,可以想象,到场的观众应该不在少数。现在,马龙先生,我跟你聊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任何个人都不应该独占本属于全世界的东西。我很期待在今晚演讲时看见你。同时,你要明白,我给你的这些东西都不能用于公开宣传。”
“但是,麦卡德尔先生——我们的新闻主编,你知道的——肯定会问我来这里的情况的。”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可以加上一句,如果他再派别的人来打扰我,我就拿着马鞭去拜访他。但是你要保证今天我告诉你的这一切都不能见报。那么,今晚八点半动物研究所报告大厅见。”我又最后看了一眼他那红苹果一样的脸颊、水流一样的蓝色胡子,还有透着心胸狭窄的眼神,就被他挥挥手赶出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