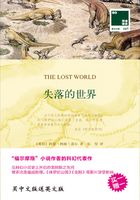
第5章 质疑
带着与教授第一次会面给我带来的身体上的冲击,以及第二次会面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冲击,我从查林杰教授家走了出来。这时的我,看上去就是一个意志消沉的记者。在我那隐隐作痛的脑袋里面,一个念头一直在骚动:这个人讲述的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一定会引起轰动,如果我能获得授权进行报道的话,肯定会获得极大的成功。一辆出租车停在路的尽头,我一跳上去,它就朝我的办公室疾驰而去了。麦卡德尔一如既往地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喂,”他充满期望地大声说,“情况怎么样?我在想呢,年轻人,你可能跟他打起来了吧。别告诉我他打了你了啊。”
“我们一开始是有一些分歧。”
“那是个什么人啊!你是怎么办的呢?”
“嗯,后来他理智了一些,我们聊了聊。但是我什么也没问出来——没什么值得报道的。”
“这可不一定。他把你的一只眼都打青了,这不就是报道的素材吗?我们可不能容忍这种恐怖的行径,马龙先生。我们要让这个家伙受到应有的惩罚。明天我要发表一篇有关于他的简短社论,批得他体无完肤。你给我提供素材,我要让这家伙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夸夸其谈教授’——用这个做标题你觉得怎么样?约翰·曼德维尔再现——卡里奥斯特罗——历史上所有的骗子和流氓。我就是要揭露他那骗子的嘴脸。”
“我不想这样,先生。”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个骗子。”
“什么?”麦卡德尔的声音近乎咆哮了,“你不会告诉我你真的相信他那些关于什么猛犸象、乳齿象和大海蛇的学说吧?”
“嗯,那个我也不知道,他没那么说。但是我相信他是发现了些新东西。”
“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小伙子,你就把它写出来吧!”
“我也想,但是是我先答应他不报道他才同意告诉我的。”我把教授的叙述简化成几句话,“就是这么回事。”
麦卡德尔看上去对此深表怀疑。
“那么,马龙先生,”他最后说,“说到今晚的科学会议,那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任何私密性可言的。我觉得别的报纸肯定都没有去进行报道的兴趣,因为沃尔德伦已经被报道过十几次了,而且也没有人知道查林杰会在会上发言。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以抢先报道。你无论如何也要到会,你就好好给我们报道一下吧。我会在午夜前一直给你保留位置。”
这一天我可真是忙得够呛。我跟塔尔普·亨利在野人俱乐部早早吃了晚餐,期间跟他讲了一些我上午冒险经历的情况。他听着我的讲述,瘦削的脸上满是不相信的微笑,当听到我相信了教授的说法时,他竟然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亲爱的伙计,现实生活里可没有那样的事。无意中遇到了天大的发现,结果证据不见了,怎么会呢?这只能是小说里才有的情节。这家伙就像动物园猴山上的猴子一样诡计多端,简直是一派胡言。”
“但那个美国诗人呢?”
“根本就没这么个人。”
“我看见他的素描簿了。”
“你觉得是他画的那只动物吗?”
“当然是他了,要不然是谁?”
“好吧,那么,照片呢?”
“照片里什么都没有。你自己也承认了,你只看到了一只鸟而已。”
“是一条翼龙。”
“那是他的说法,是他让你在脑子里形成了翼龙这个印象。”
“好吧,那么,那些骨头呢?”
“第一根是从一锅土豆洋葱炖肉里捞出来的,第二根也差不多。只要你够聪明,也掌握了技术,那么伪造一根骨头比伪造一张照片难不了多少。”
我开始感觉有点儿不自在了,或许我真是相信得太过仓促了。但是,马上,我又产生了一种很高兴的念头。
“你来参加会议吗?”我问。
塔尔普·亨利表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和蔼的查林杰,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说,“很多人都跟他有过节。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伦敦第一号受憎恨的人。如果医学学生们出席的话,那么对他的指责肯定会没完没了的。对那样嘈杂的场合我可没兴趣。”
“至少你可以听听他怎么陈述自己的意见,这对他来说也算公道了。”
“嗯,或许只算得上是公平吧。好吧,今晚我听你的。”
到了报告厅,我们发现与会人员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多得多。一群白胡子的教授从一排电动车上走了下来,而步行的观众像黑压压的潮水一样从一道拱门里涌了进来。这个场面一看就知道,与会的观众不仅科学知识丰富,而且非常受欢迎。的确,我们一坐到座位上,立刻就清晰地感受到,大厅的后部和走廊里到处都充斥着一种年轻的,甚至是有点孩子气的气息。向身后望过去,我看到了几排非常熟悉的医学学生特有的脸。显然,各大医院都派来了代表。出席观众的举止看起来幽默诙谐,但又不大友善。大家热情洋溢地合唱着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的片段,这情景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科学讲座的前奏,而且已经有人互相开起了玩笑,完全将这里当成了娱乐场所,这对于那些获奖者们是多么尴尬啊。
因此,当一把年纪的沃尔德伦博士头戴他那顶著名的卷边帽登台的时候,满场响起了“哪来的瓦片?”的叫声。他赶紧把帽子摘下来藏在椅子下面。患了痛风的沃德利教授一瘸一拐地走到座位那儿,大厅里四处传来对他脚趾的情况关切的询问,这显然让他尴尬不已。而引起最大轰动的则是我刚刚结识的人,查林杰教授。他进了门,向最前排尽头的位置走过去。当他那黑黑的胡须刚刚从拐角处露出来的时候,观众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欢迎声。那时,我开始怀疑塔尔普·亨利的推测了,我甚至想,这次聚会可能不仅仅是为了讲座,而是因为这位著名的教授即将出席会议的消息已经在外面传开了。
他一进来,前排衣冠楚楚的那些观众发出了一阵同情的笑声,好像刚才学生们对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欢迎似的。的确,那问候声爆发出来得很突然,有点儿吓人,就像动物园里的食肉类动物听到饲养员拿着喂食桶走近的时候发出的吼声一样。这问候声里带有些许无礼的语气,但是总得说来,我认为这只是高声的喧闹,意味着被欢迎者是一个给他们带来欢乐和乐趣的人,而不是一个受到厌恶和鄙夷的人。查林杰轻蔑地笑了笑,笑容里透着厌烦和容忍,那表情就像一个善良的人看到一窝汪汪叫的小狗一样。他缓缓地坐了下来,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用手轻轻捋着胡须,眼皮低垂,用高傲的眼神看着面前拥挤的报告厅。欢呼声还没结束,主席罗纳德·莫里和演讲人沃尔德伦先生挤过人群来到台上,仪式开始了。
如果我说莫里教授跟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有听力不济的毛病,他一定不会介意的。有人要表达一些值得倾听的内容时,却不肯费哪怕一点心思来琢磨一下怎么让别人听得进去,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难解之谜了。他们的表达方法就像是在通过一条根本不通畅的管子将泉水注入到蓄水池里一样,而实际上想要疏通这根管道是非常容易的事。莫里教授对他那白色的领带和桌上的玻璃水瓶评价了两句,然后又不无幽默地将话题转移到他右边的银烛台上。之后,他坐了下来。而沃尔德伦先生,一位以受欢迎而著称的演讲者,则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站了起来。他瘦骨嶙峋,看上去有点严厉,说话嗓音有点儿生硬,行为举止也是咄咄逼人。但是他却非常擅长将别人的看法进行同化,而且,他也很清楚以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能够使话题在那些外行的观众看来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充满趣味,对于看似根本不可能的事,他也有诀窍,那就是尽量用一些滑稽有趣的语言来解释。于是,类似昼夜平分日以及脊椎动物的形成这些话题经过他的诠释都成为很有意思的话题。
通过使用清楚甚至有时极富画面感的语言,他将一副创作的鸟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幅图只有用科学才可以解释。他向我们介绍了地球,大量的可燃烧气体,火焰蹿上天空。然后,他又给我们描绘了固化、冷却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山脉怎么形成,蒸汽如何变成了水,整个世界如何做好了让这戏剧化的生活上演的准备。关于生命的起源,他的态度颇为谨慎,没有解释得很清楚。但是,他提出,生命的胚芽根本熬不过高温的烘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生命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那么生命是在地球冷却过程中的无机因素中自己演化出来的吗?很有可能。或者,生命的胚芽是通过陨石从外太空带来的吗?这简直无法想象。总而言之,最聪明的人永远都是在这一点上最不教条的人。我们做不到——或者说至少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成功地做到在实验室里从无机材料中制造出有机生命。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目前对于我们的化学来说还是不可跨越的。但是在自然界中还存在着更高水平更加微妙的化学,它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能创造出人类创造不出来的奇迹也并不是没有可能。这个问题还要留待以后解决了。
演讲者将话题继续,谈到了动物的出现,一开始是贝类和一些低级的海洋动物,然后是爬行动物和鱼类,最后又出现了袋鼠这种直接生出幼崽的动物,成为所有哺乳动物的直接祖先,所以,应该也是在座的每一位观众的祖先了。(“不对,不对。”后排一个学生提出了质疑。)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那位系红领带的年轻人喊了“不对,不对’,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从蛋里孵出来的吧。我很愿意见见这位极具好奇心的人,希望会后他愿意等一下(笑声)。如果我们说这位系着红领带的年轻人就是自然漫长的进化过程的顶点,当然是很奇怪的提法。那么进化过程已经停止了吗?这位年轻人应该被认为是最后的物种,是进化过程的归宿和终点吗?”他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不管那位年轻人在私人生活中拥有怎样的美好品质,宇宙的进化过程以他的出现作为结局肯定是不公正的,他还提到希望自己提出的这种观点不会让那位年轻人的感情受到伤害。进化不是一种被耗尽了的力量,它现在依然在起作用,并且它将来要创造的奇迹甚至会更大。
演讲者说这话的时候,台下当然免不了吃吃偷笑,但他也将这中途被打断的情况很巧妙地处理好。之后,他又回到了对过去画面的勾勒过程,随着海洋的干涸、沙滩的出现、岸边开始出现了动作缓慢的黏体动物,咸水湖里开始拥挤不堪,于是原来生活在海洋中的动物开始迁移到泥滩上,那里食物充足,于是它们的个体开始长得很大。“因此,女士们先生们,”他又补充道,“我们现在在威尔登或索伦霍芬这些地方看到一窝蜥蜴都吓得要死,幸亏那些大型的动物在人类出现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灭绝了。”
“我质疑!”台上发出了一声洪亮的叫喊。沃尔德伦先生一向严格地奉行纪律,又带有一点儿酸溜溜的幽默感,正如刚才在处理那位系红领带的年轻人的情况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打断他的演讲绝对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但是这次插话对他来说可能有点儿太荒唐了,所以他甚至都没有考虑应该怎么处理。那情形就像是莎士比亚风格遭遇了带有腐臭味的培根主义者,或是天文学家遭到天圆地方说抨击一样。他顿了顿,然后,抬高了嗓音,又慢慢地重复了一下自己的话:“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灭绝了。”
“我质疑!”那个洪亮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了。
沃尔德伦吃惊地挨个儿打量着台上坐着的一排教授,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查林杰的身上。查林杰此刻正靠着椅背坐着,闭着眼睛,脸上带着愉快的表情,好像正在睡梦中微笑一样。
“我知道了!”沃尔德伦耸了耸肩说,“是我的朋友查林杰。”在一片笑声中,他继续自己的讲座,就好像他刚才听到的是最终的结论,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但是这件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不管沃尔德伦以怎样的方法讲解过去的进化过程以及史前生物不可避免的灭绝,都必将引出一个结果——查林杰教授会像一头公牛一样咆哮起来。随后观众也参与了进来,教授一喊,他们就一起高兴地跟着大喊起来。报告厅里满满坐着的学生都参与了进来,每次查林杰教授的嘴一张开,还没发出任何声音,一声响亮的“质疑!”就从几百人口中一起爆发出来,之后,好像在作出回应似的,同样是几百个声音齐喊出“秩序!”“羞耻!”沃尔德伦虽说算得上是个坚毅的演讲者,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但也不禁慌乱了起来。他开始犹犹豫豫、结结巴巴,说话开始反反复复,甚至在说一句很长的句子时忍不住咆哮了起来,最终,他对这一切麻烦的源头变得怒不可遏。
“太让人难以忍受了!”他瞪着讲台对面,大喊一声,“我请求你,查林杰教授,请你不要再进行这样无知而又粗鲁的干扰了好吗?”
报告厅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学生们安静了下来,兴致勃勃地看着奥林匹斯山上的两位大神吵了起来。查林杰那笨重的身躯从椅子上费力地站了起来。
“那么我也要请求你,沃尔德伦先生,”他说,“请你不要再发表这些严格来说根本与科学事实不符的学说了。”
这话引起了一阵骚动。出于消遣和憎恨的大喊中还夹杂了一些其他的声音。“羞耻!羞耻!”“听他说!”“把他赶出去!”“把他轰下讲台!”“公平竞争!”主席站起来,拍着双手,带着兴奋的情绪轻声说:“查林杰教授——个人的——观点——一会儿再提。”他那近乎自言自语的声音在一片喧闹声中几乎根本听不到。查林杰鞠了一躬,微笑着轻抚着胡须,重新坐了下去。沃尔德伦脸涨得通红,强忍住内心的怒火,继续演讲。每当他提出一个论断,他都会恶毒地看一眼他的对手。而对方则好像是睡着了一样,脸上一如既往地带着那开心的微笑。
最后,演讲终于结束了——我觉得这算不得是一次成熟的演讲,因为结束得非常匆忙,而且也毫无条理。论证的线索被粗鲁地强行打断,观众内心充满着期望、躁动不安。沃尔德伦坐了下来,主席尖声尖气地说了两句之后,查林杰教授站起来走到讲台边。为了更好地进行报道,我将他的发言逐字记了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在后边持续的一阵骚乱中,他开了口,“请原谅——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孩子们——首先我必须要道歉,由于一时疏忽我遗漏掉了这很可观的一部分观众(台下一片喧哗,同时,教授抬起了一只手,他富有同情心地点了点他那巨大的头,好像他是一个主教,正在赐福于众人似的)。我有幸被选中为沃尔德伦先生刚才那生动而富有想象力的演讲进行致谢。演讲中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我不敢苟同,我有责任当面指出,但是,尽管如此,沃尔德伦先生已经很好地达成了他的目标,将自己想象中的地球历史讲解得简单明了,引人入胜。受欢迎的演讲者往往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我想沃尔德伦先生(此时他朝沃尔德伦眨着眼笑了笑)也一定会原谅我的。我要说这次演讲既肤浅又对人起到了误导作用,因为它所针对的是一群无知的观众,必须要照顾他们的理解能力(喝倒彩的声音)。一名受欢迎的演讲者骨子里就是个寄生虫(沃尔德伦先生愤怒地摆出了一个抗议的姿势)。
“为了金钱和名誉,他们对他们那些贫乏而默默无闻的同胞的工作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在实验室里得出的最微不足道的新发现,用于建造科学殿堂的一块砖,尽管得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也比那些足足浪费大家一小时的二手结论展示要强得多。我现在做出这样的反思,并不是故意想要贬低沃尔德伦先生,而是希望大家不要失去自己的主次观念,不要将新手误认为是领头人(说到这儿时,沃尔德伦先生对主席低声说了几句话,主席稍微站起一点儿,严厉地对着桌上的水瓶说了句什么)。但是,这种情况应该到此为止了(响亮而持久的欢呼声)!让我来讲点儿更有意思的吧。作为一个原创型的研究者,我要针对哪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提出质疑呢?就是地球上某些动物物种生命的持久性。关于这个论题,我不是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也不是以一名受欢迎的演讲者的身份来发表观点,我要说的是基于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良知,我不得不尊重事实。我要说沃尔德伦先生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亲眼见过所谓的史前动物就说它们已经灭绝了,这种设想是非常错误的。正如他所言,它们的确是我们的祖先,但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说法,它们是我们当代的祖先,只要我们拥有力量和胆识去寻找它们的栖息地,那些强大的、令人惊骇的动物依然可以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些我们认为只存在于侏罗纪,能够捕猎和吞食体型最大、最为凶猛的哺乳动物的怪兽,依然存在于当今世界(有人大喊‘胡扯!’‘怎么证明?’‘你怎么知道的?’‘质疑!’)。
“你是问,我怎么知道的吗?因为我到它们的秘密栖息地走了一遭。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掌声,吼声,有人大喊‘骗子!’)。我是骗子吗(有人热烈而喧闹地表示赞成)?我听到有人说我是骗子了,是吗?那个叫我骗子的人请站起来让我认识一下可以吗(有人喊:‘他在这儿,先生!’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毫无恶意的小个子挣扎着被人从一群学生中推了起来)?就是你叫我骗子吗(‘没有,先生,没有!’被指控的年轻人大喊了一声就像玩偶盒玩具里的人偶一样,转眼从视线里消失了)?如果这个报告厅里有任何人敢质疑我的话的真实性,演讲结束后我愿意跟他聊一聊(‘骗子!’)。谁说的(那个没有恶意的人一边拼命挣扎着一边又被人高高地推起来)?如果我走到你们中间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喊‘来吧,爱你,来吧!’喊声使得演讲一时间没法再进行下去,主席站了起来,挥舞着两只胳膊,那样子像是在指挥一个乐队。沃尔德伦教授脸颊通红,鼻孔扩张,胡子都炸了起来,已经处于狂暴状态了)——每一位伟大的发现者都曾经遭遇过这样的怀疑——来自这种傻瓜的怀疑。当伟大的发现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们根本不具备能够帮助你理解它们的直觉和想象力。你们只会朝那些为了开创科学的新境界险些失去生命的人扔泥巴。你们迫害先知!伽利略!达尔文!还有我——”人群发出持久的欢呼,发言彻底没法进行下去了。
我在演讲时匆匆做着笔记,几乎没有注意到刚才观众发出的嘈杂声现在已经变小了好多。观众的吼声刚才那么大,几位女士已经被吵得匆忙离开了会场。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似乎也受到了学生们情绪的感染,我亲眼看到那些白胡子的老人们站了起来,向那顽固不化的查林杰教授挥舞着拳头。全体观众像一锅开水一样,都沸腾了。查林杰教授向前走了一步,举起了两只手。这个人身上有着一种很强大,很引人注意,很有男子气概的气质,在他那命令式的姿势与威严的眼神面前,台下逐渐安静了下来。他好像是有一些很明确的信息要公布,他们都安静下来倾听着。
“如果要走,我不会强行挽留你们,”他说,“没有什么值得我那样做。事实就是事实,不会因为几个愚蠢无知的年轻人——还有,恐怕我还要提到,他们那同样愚蠢无知的导师——发出的几句吵吵嚷嚷就能改变的。我要说我开创了科学的一个新领域。你们可以提出质疑(欢呼声)。然后我要考考你们。你们能不能推举一两个人作为代表,来对我的论述进行考察?”
比较解剖学的老教授夏莫里先生从观众中间站了起来。这个人个子高高瘦瘦,一副严厉的样子,像一个干瘪的神学专家。他说,他希望查林杰教授告诉他刚才查林杰教授所提到的结论是否是两年前在去往亚马逊上游源头的那次旅行中得到的。
查林杰教授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夏莫里先生又问像华莱士、贝茨以及其他一些在科学界颇有声望的科学家在之前的考察中都没有做出的发现,他却做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查林杰教授回答说,夏莫里先生似乎是将亚马逊河与泰晤士河弄混了,实际上亚马逊河是一条很大的河,给夏莫里先生讲一个有趣的情况吧,与它交汇的奥里诺科河流域,就有长达五万英里的河道是开放的,空间如此之大,一个人发现了另一个人遗漏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可能。
夏莫里先生冷笑着说,他对泰晤士河与亚马逊河之间的区别当然是完全了解的,这种区别恰恰说明,任何关于前者的论断是可以进行验证的,而后者则不行。他请求查林杰教授公布发现史前动物的那个国家的经纬度。
查林杰教授回答说他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公布那些信息,但是可以从观众中选出一个小组来,在提前进行一定警告的情况下向他们透露。夏莫里先生是否愿意参与到这个小组中,亲自来进行验证呢?
夏莫里先生说:“当然,我愿意。”(热烈的欢呼)
查林杰教授说:“那么我保证将指引你找到那些动物生存的地点。然而,既然夏莫里先生要验证我的结论,那么应该有其他一两个人跟他一起去才对。不瞒大家,这个过程中既有艰难又有危险。夏莫里先生需要一个年轻点的同伴。有志愿参加的吗?”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人生危机一跃而出。当初我进入这个报告厅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过我即将投身到比梦境还要疯狂的冒险当中。但是格拉迪斯——这不就是她所说的那种机会吗?如果格拉迪斯在的话,她一定会让我去的。我站起身来,想要开口,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跟我一起来的塔尔普·亨利扯了扯我的衬衫,我听到他在小声说着:“坐下,马龙!别给大家看你的屁股啊。”就在这时,我发现坐在我前面几排的一个高高瘦瘦、一头深姜黄色头发的男人也站了起来。他用愤怒的目光狠狠地瞪着我,但是我丝毫也没有让步。
“我愿意去,主席先生。”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姓名!姓名!”观众大喊。
“我叫爱德华·邓恩·马龙,是《每日公报》的记者。我承诺,一定会成为一名公正的见证。”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主席问那个高个子男人。
“我叫洛德·约翰·洛克斯顿。我以前去过亚马逊,对那里的地形很熟悉,非常适合去做这次考察研究。”
“洛德·约翰·洛克斯顿,世界著名的运动员和旅行家,”主席说,“同时,有一位新闻界的成员参加这次考察当然也是件好事。”
“那么我提议,”查林杰教授说,“这两位先生都被选为这次会议的代表,同夏莫里教授一起进行这次考察,并报告我结论的真实性。”
于是,在一片喧闹和欢呼声中,我们的命运被决定了下来,而我被漩涡一样的人流裹挟着涌向门口,大脑被刚刚出现的新任务满满地占据着。我从报告厅出来后,看到人行道上有一群学生正在说说笑笑,一只胳膊伸出来举着一把伞,在人群中摇摇晃晃。然后,在一片牢骚和欢呼声中,查林杰教授的电动布鲁厄姆式汽车缓缓开动,而我则在雷金特大街那银色的路灯下慢慢走着,任由格拉迪斯和对我未来的设想占据了我的思绪。
突然,我感觉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我转身一看,原来是那位毛遂自荐跟我一同去进行这次奇怪的探险的瘦高个男子,呈现在我眼前的正是他那带有一丝幽默又有点威严的目光。
“马龙先生,我明白,”他说,“我们马上就属于一个团队了。我家就在马路对面,在奥尔巴尼街。我希望耽误您半小时的时间,我有些话非常想跟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