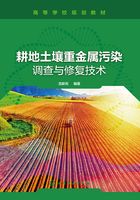
第1章 绪论
1.1 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概述
耕地是指种植食用类农产品的农用地,包括水田和旱地。水田是指筑有田埂(坎),可以经常蓄水,用来种植水稻、莲藕、席草等水生作物的耕地。旱地是指除水田以外的耕地,包括水浇地和无水浇条件的旱地。水浇地是指旱地中有一定水源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下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无水浇条件的旱地是指没有固定水源和灌溉设施,不能进行正常灌溉的旱地。
耕地质量是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缺,2016年底耕地总面积为1.35亿hm2,合20.24亿亩(1亩=666.67平方米),人均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且总体质量不高,中低产田达到了2/3。近年来,由于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我国耕地面积保有量总体有所下降。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集约化的快速发展,各种来源的重金属元素通过降尘、施肥、灌溉等途径进入耕地,且数量逐年增加,导致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重金属污染不仅能够引起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还能够抑制作物根系生长和光合作用,致使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更为重要的是,重金属还可能通过食物链迁移到动物和人体内,严重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
1.1.1 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
2006—2013期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开展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专项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共布设点位67615个,采集了213754个土壤样品。2014年4月17日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简称《公报》)。《公报》显示:我国耕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的点位所占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中国地质调查局(2015)发布的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显示,重金属中-重度污染或超标的点位比例占2.5%,覆盖面积3488万亩;轻微-轻度污染或超标的点位比例占5.7%,覆盖面积7899万亩。污染或超标耕地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湘鄂皖赣区、闽粤琼区和西南区。
在各种科研项目的资助下,我国科技工作者相继开展了一些区域性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的调查与监测工作。2002年,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主持开展了“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探查研究”,调查范围包括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和辽宁5省,结果显示珠三角部分城市有近40%的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长三角有的城市连片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土壤基本丧失生产能力,以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超过0.4亿hm2良田(蔡美芳等,2014)。2006年,原环境保护总局对30×104hm2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的重金属抽测了3.6×104hm2,重金属超标率达12.1%。宋伟等(2013)利用我国138个典型区域的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数据库,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作为评价标准,结果发现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概率为16.67%左右,据此推断我国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量的1/6左右。其中尚清洁、清洁、轻污染、中污染和重污染比例分别为68.12%、15.22%、14.49%、1.45%和0.72%;8种土壤重金属元素中,Cd污染概率为25.20%,远超过其他几种重金属元素。浙江大学徐建明研究团队(2018)调查了长江中下游某地区污染较严重的4.4万亩农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状况,发现主要超标元素为Cd和Cu,轻微、中轻度和重度Cd污染土壤面积分别占45.62%、12.3%和1.74%。
综上所述,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其中以西南、中南、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污染最为突出。在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和面积尚未清楚的情况下,开展土壤污染详查尤为重要。因此,2017年8月,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部署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计划于2018年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
1.1.2 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
1.1.2.1 污染成因复杂多样
我国耕地土壤受重金属污染的成因复杂,包括自然的成土母质条件、人为的污染因素以及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叠加作用等。
从区域大尺度上看,自然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成土母质和母岩等地球化学属性直接影响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调查资料显示(赵其国和骆永明,2015),不同类型母质发育的土壤重金属含量差异很大,火成岩和石灰岩母质发育的土壤中Cd、As、Hg和Pb平均含量显著高于风沙母质土壤。瞿飞等(2020)在黔东南黄平县分别采集典型砂页岩、老风化壳、石灰岩、页岩、河流冲积物、泥岩6种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样品257个,结果显示,不同母质土壤Cd含量大小为石灰岩>河流冲积物>老风化壳>泥岩>砂页岩>页岩,Cr含量为老风化壳>泥岩>页岩>石灰岩>砂页岩>河流冲积物,Hg含量为石灰岩>泥岩>砂页岩>河流冲积物>老风化壳>页岩,As含量为泥岩>石灰岩>老风化壳>砂页岩>页岩>河流冲积物,Pb含量为泥岩>老风化壳>石灰岩>砂页岩≈页岩>河流冲积物。成土过程中元素的次生富集作用也是造成我国中南、西南高背景地区土壤中Cd、As、Hg和Pb等重金属含量高的重要原因。例如,贵州地表土壤与沉积物中Cd的地球化学背景值为0.31mg/kg,是我国平均水平的2.5~3.5倍(何邵麟等,2004)。长江三角洲自然土壤中As、Co、Cr、Ni和Zn等元素含量高于珠江三角洲自然土壤中对应的元素含量。
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华北城郊区域等局部范围内,耕地土壤重金属含量异常往往是人为因素的影响。在大中城市郊区,大气沉降和污水灌溉是城市工业和交通源重金属进入农田土壤的最主要途径。陈世宝等(2019)分析了2011—2015期间报道的不同农田土壤重金属输入源的文献数据,发现全国范围农田土壤中Cd的年输入通量约为4.83μg/kg,但不同省农田土壤中Cd输入通量及来源有很大差异。河北和湖南省农田年输入通量则达到14.4μg/kg和19.6μg/kg,分别为全国农田土壤中Cd年输入通量的2.97倍和4.06倍。工业大气沉降和污水灌溉是导致我国部分省区农田土壤Cd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河北省工业大气沉降和污水灌溉分别占Cd年总输入通量的58.2%和27.3%,湖南省则分别占16.6%和69.9%。韩志轩等(2018)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22个点位上采集的44件冲积平原土壤样品,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和铅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了重金属元素的来源。结果表明,As、Pb、Hg的异常受人为活动影响较严重,Zn、Cd的高含量既与地质背景有关,也受人类活动影响。
1.1.2.2 空间分布异质性强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背景值和累积量差异较大(陈卫平等,2018)。《公报》显示: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张小敏等(2014)结合2000—2013年公开发表文献中的农作物土壤的重金属含量数据和相关数据库中的部分数据发现。中国区域农田土壤Pb、Cd、Cu和Zn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富集,重金属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西南地区土壤重金属含量较高,其次是两广和辽宁地区,其他地区相对较低。Liu等(2016)调查了我国22个水稻种植省份土壤Cd累积量,显示全国水稻土Cd平均含量为0.45mg/kg。
金属采矿区和冶炼区的周边耕地土壤重金属的含量较高,属于重金属高风险区。例如,曾希柏等(2013)调查了某冶炼区和三个采矿区周边较小区域的农田土壤,结果发现,每个调查点土壤样品均有三种以上元素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Ⅲ级含量标准,占采集样品的比例为10%以上,最高甚至达91.2%,超标最严重、超标样品比例最高的是Cd,其次为As,在调查的4个地区均存在较大程度超标,其超标幅度达21.1%~62.3%,而Zn、Cu、Pb等元素超标样品的比例则相对较低。吴劲楠等(2018)在某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共布设496个采样点,测定表层土壤中重金属(Cd、Hg、Pb、Cu、Zn)的含量。结果表明:Cd、Hg、Pb、Cu和Zn的平均含量(mg/kg)分别是该矿区所在省背景值的33.05、5.83、12.02、4.89和16.33倍;单因子指数评价结果显示,99.8%的样品达到Cd重度污染水平,其次是Cu(82.06%)和Zn(62.50%)。杨世利等(2019)调查了中国西南某铅蓄电池厂污染场地土壤,距离厂内生产区20~30cm处土壤Pb的质量分数高达12784mg/kg,厂内生产区、熔炼区、排污口、循环水池处的Pb含量远高于背景点。
1.1.2.3 土壤类型差异明显
我国土壤类型多样,由于土壤条件、气候条件和耕作管理水平的不同,不同类型土壤理化性质差异较大,进一步加剧了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多样化格局(陈卫平等,2018)。罗小玲等(2014)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典型农田和菜地两种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监测与评价,发现工业型农村的耕地以铜超标为主(超标率22.2%),种植型农村的耕地以Cd超标为主(超标率16.7%),其余重金属超标率低或不超标。Rafiq等(2014)对我国7种典型农田土壤Cd活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酸性土壤类别中,富铝土中交换态Cd含量约为黄壤中交换态Cd含量的近4倍。黄颖(2018)的研究发现,不同耕作方式对重金属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Cd、Hg、Pb、Cu、Zn在蔬菜地和水稻田中含量较高,在旱地和园地含量较低,而Cr、As、Ni三种元素在园地含量最高,在其他类型土壤较低。
1.1.2.4 土壤酸化加剧了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我国土壤酸化面积近200万hm2,近年来粮田、菜园和果园土壤酸化趋势均有增加(赵其国等,2013)。1980—2000期间,我国5种典型土壤pH降低范围为0.13~0.80单位,其中水稻土酸化最为严重,pH年均下降速率为0.012单位(Guo et al.,2010)。土壤酸化增强了土壤中的重金属活性及其迁移能力,加剧了重金属污染的生态危害。这也是我国个别地区近年来稻米Cd含量超标问题多发,而同样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其他亚洲国家(泰国、韩国、日本等)稻米Cd含量超标问题不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Yang(2017)对某地的调查发现,在土壤pH<5.5的菜地和水稻田中,蔬菜和稻米Cd含量超标率分别为7.8%和89.4%;而在土壤pH>6的菜地和水稻田中,蔬菜和稻米Cd含量超标率显著降低至1.3%和32%。
1.1.3 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1.1.3.1 直接经济损失
据估算,我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不仅如此,因土壤污染每年造成的粮食减产也相当大,全国每年由耕地污染而造成的粮食减产达到1.25×109kg。如果将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所需的资金非常惊人。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全国有5000多万亩土壤受到重金属等的中重度污染。因此,我国污染耕地土壤修复所需资金数额巨大,仅对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土壤而言,即便选择土壤修复成本较低的植物修复技术,单位治理成本为100~500元/吨,直接治理成本约3.1×104~15.6×104亿元。
1.1.3.2 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土壤重金属进入植物体后,可通过抑制一些蛋白酶的活性、在植株细胞中产生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损坏细胞抗氧化系统,导致细胞受损或死亡等,从而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发育,导致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严重时,甚至绝收。例如,Cd胁迫会导致细胞质膜的透性发生变化,影响矿质营养元素的吸收,导致植株体内营养元素含量和成分的改变。水稻极易吸收并积累镉,而积累过量镉会导致严重的毒性效应,影响植株的光合色素含量、呼吸强度、蒸腾和光化学效率,从而严重影响水稻的生长并导致其减产,稻米品质劣变(胡婉茵等,2021)。在盆栽实验条件下,Cd胁迫显著降低了水稻的产量、穗数和结实率,但粒重受影响不显著(陈京都等,2013)。
耕地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有时会发生“镉米”事件。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我国部分地区稻米质量安全普查结果表明,约有10%稻米Cd含量超过我国1994年颁布的《食品中镉限量卫生标准》(GB 15201—1994)限定标准值0.2mg/kg。
1.1.3.3 危害人体健康
耕地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粮食、蔬菜等农产品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畜健康,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等。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痛痛病”和20世纪50年代的“水俣病”。
1.1.3.4 导致其他生态环境问题
土壤污染影响植物、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危及正常的土壤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表明,土壤重金属对蚯蚓、线虫等无脊椎动物数目、丰富度、生物数量和群体构成等有直接影响。
农田土地受到污染后,含重金属浓度较高的污染表土容易在风力和水力的作用下分别进入大气和水体中,导致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其他次生生态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