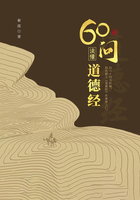
第一问:为什么“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是传世版《道德经》开篇第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老子对《道德经》全文作出的一个终极注解。如果读不懂这句话,那么也很难去读懂《道德经》。
我们常说“眼见为实”,其实眼见也并非是实。同样的事物,在不同光线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那么到底哪个形象才是真实?
有句话叫“凡所有相(象),皆是虚妄”。光线和声音一样,都只是一种媒介,用以传递真实世界的信息。但是经过它们传递而呈现出来的音声形象,却并非就是这真实世界的真实模样。
语言和文字,也同样只是一种媒介。所以我们用语言描述出来的“道”,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道”本身,这就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同样的世界,在人的眼中和动物的眼中各不相同,那么谁的眼中才是真实的世界?我眼中的“你”,和“你”眼中的自己,也不相同,那么谁才算了解真正的“你”?
庄子在《齐物论》中论述了这一现象:当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我”去认知万物时,就必然同时存在一个“我”(认知方),一个“非我”(被认知方)。这两个概念,其中一个消失,另一个也不复存在。所以“我”,不会超脱出“我”而知道“非我”的立场;“非我”,也不会超脱出“非我”而知道“我”的立场。
既然你我立场并不一样,“我”并不是“你”,那么我认知中的“你”,和“你自己”,是一回事吗?我们认知中的事物,和事物本身,是一样的吗?我们眼中的马,和马自身,是一体的吗?所以“马非马”,我们认知而来的“马”,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马”自体。
天地,就是那个被大家所共同认知的事物;万物,就是那匹我们眼中的马。因此,我们对天地万物进行认知,给予它们的命名和定义,并不能与它们本身相等同。这就是“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语言的表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常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相信老子在面对这无名无形无象的大道之时,他的心中也一定有这样的感慨。但他还是留下了五千言,并且在开篇就提醒众人:我说出来的道,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道,要想得道,你就必须亲自发现它。
把“道”用语言描述出来,就需要对它进行命名和定义。所以老子又说:“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给了它一个名字叫作“道”,定义为“大”,但这个名字和定义并不能等同于道的全部内涵。因此老子才说自己是“强为之名”,只是很勉强的给了它一个名字,一个定义。
因为道,本无形无象而无名。如果强为之名,这个勉强的名,就只是以我们所能认知到的,道的某一方面特征为依据,比如大,远,反。然而这所有落于具体的名,都不能概括得了道的真正内涵。
比如,我们可以用“有”,来概括有形有质的东西,可以用“无”,来概括无形无质的东西。但是对于道来说,“有”和“无”同出于道,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所以它们都不足以用来概括道。
道很大,大到无以复加,但同时又很小,再细微的地方都有它;道很远,远至八荒六合,但同时又很近,近至我们每个人。也就是说,道非“有”非“无”,非大非小,非远非近,而且又“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既不光明,也不昏暗。这样的事物,我们要怎样去用一个“名”来概括它呢?
名字和定义是人赋予的,而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名字和定义与事物本身是可以剥离开来的。那如何通过这些被剥离开来的“名”,来把握住它们所指向的真实呢?这就涉及了“名”和“实”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笑话: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人定义为“双足的无毛动物”,于是另外一个哲学家狄奥根尼就把一只鸡的羽毛全部拔光,拎到讲桌上说:“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柏拉图无言以对,只好另作补充,把人的定义修改为:“人是没有羽毛的,有扁平指甲的两脚动物。”然而这样的定义,能算得上是对人的完美诠释吗?
“人”只是一个名词,用以指代像我们一样的生物。我们都知道人,所以一说“人”这个名词,马上就能调用自己意识里对人的认知,自行把“人”这个概念补充完整。但是,如果他是在描述一种我们谁也不知道的生物呢?此时名字就不再具有指代性,而只能通过语言描述来建立对这种生物的认知。
不过很显然,我们并不能凭借柏拉图的描述来建立对人这种生物的正确认知。“没有羽毛的,有扁平指甲的两脚动物”,一百个人用这个定义能想象出一百种各不相同的生物。
同样,老子写了五千文来描述道,我们能否通过他的描述来建立对道的正确认知呢?很难。通过他的描述所认知的“道”与实际存在的“道”可能天差地远,就像那只无毛鸡和人一样。因为语言,并不能构建事物本身,并不能制造真实本身,故而“知者弗言,言者弗知”。
据说,战国时有一赵国人公孙龙欲乘马出关,关吏说:“按照惯例,过关人可以,但是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一番论证,关吏听了之后连连点头,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请你为马匹付过关钱吧。”于是公孙龙便骑着他“不是马”的白马过关了。
故事真假不可考,但“白马非马”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论题。按照公孙龙的说法,“马”这一名是只命形不命色的;“白马”这一名是既命形又命色的,一个只包含单一特征的概念,又怎么能等同于一个包含两个特征的概念呢?概念与事物本身尚且存在差别,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更加毫无联系了,所以白马不是马。
那么白马是马吗?白马当然也是马。然而仅从字面意义去解释,仅从概念名词去推敲,像公孙龙这样的优秀名学家,论证出“白马非马”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探讨名和实(形)的关系,在战国时就已形成了一个学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主张循名责实,明赏慎罚,后人称为“刑名之学”(古时“形”通“刑”)。
法家的韩非子也同样重视“刑名”。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法令颁布下来,即落于“名”,就很容易和事“实”之间产生偏差与冲突,必须要“综核名实”。因为“名”可以不副实,“象”也可以有假象,所以很容易被人用来混淆或替代真实本身。
“白马非马”,正是“名”的自演绎结果与其“实”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心外无物”,正是“象”的自演绎结果与其“体”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用文字描述的事实可以被人演绎成巧妙的文字游戏;用光影传递的形象可以被人演绎成高明的视觉欺骗。被万物外在的“名”“象”所迷惑所束缚,也就已经与其本体相差甚远矣!
“名”本为“实”之末,却能被人反用来诘难和限制“实”;“象”本是“体”之映射,却能被人反用来决定和制约“体”。所以“道之华”反而被人看成真道;“愚之首”反而被人看成聪明;“大智”反而被人当成“愚”;“大巧”反而被人当成“拙”,如此本末颠倒“正复为奇”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真实世界虽然折射出万象,但象与真实之间,是有迹可循的,是可以依据象来探寻到真实的,否则也不会有“知音”、“知文”之说了。音虽幻,但承载了心声;文虽虚,但根源于真实,所以知音则能知其心;知文则能得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