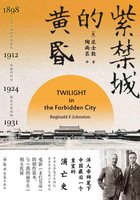
第一章 1898年戊戌风云
整个19世纪,中国满族统治的权力和威望一直在崩塌。国内叛乱和灾难性的对外战争不仅动摇了皇位的根基,还成为中国“崩溃”的前奏曲,这自然为查尔斯·贝思福勋爵于189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崩溃》提供了一个他自以为最合适的书名。就在4年前,大中华帝国被她一直在鄙视和招惹的小岛国日本打得一蹶不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中国台湾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5;如果没有欧洲三大列强(德国、俄国和法国)的干预,她就会失去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港在内的满洲的重要领土(辽东半岛)6。然而,仅仅3年之后,她便真的失去了它,当时,俄国不仅以佯装的宽宏大量夺取了他曾迫使日本归还给中国的领土,还因此加强了自己在“满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东北后,妄称东北三省为“满洲”)的军事地位,并控制了满族皇室的龙兴之地。1898年居住在此的英国商人们说,“俄国对中国的鲸吞蚕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进行着”。有一位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宣称,“他本人及其传教团都把满洲人看作俄国人——除了名字”。对于那些想了解当今满洲问题背景的人来说,这些事实不可被遗忘!中国人没有做过将俄国人赶出满洲的任何努力;毫无疑问,如果日本没有于1904—1905年在满洲大地上与俄国作战并将之击败,那么,不仅辽东半岛,而且整个满洲,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名义上,都将成为今天俄国的一个省。7
但是,到1898年年底,中国台湾和满洲并不是中华帝国唯一落入洋人手中的领土。那一年是西方列强争夺中国沿海港口和租界以及划定势力范围的顶峰之年。胶州湾及其秀丽壮观的青岛港都被德国占领了;威海卫有将近300平方英里8的领土“租”给了英国,在接下来的32年里,它被当作英国殖民地管理;另一个面积相当的地区——香港——也沦为英国殖民地,“租期”为99年;广东南部沿海的广州湾也同样“租”给了法国。意大利宣称要拥有浙江省沿海的一个港口,当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这一要求时(那是在墨索里尼时代以前),意大利人因为在这场大规模土地掠夺游戏中未能得逞而感到狼狈不堪,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对自己胆敢如此硬气地拒绝而感到惊讶不已。
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它们瓜分中国的勾当可以轻松愉快地进行下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连眉头都不敢皱一下,那么,它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外来侵略开始将一种“文明模式”注入一个民族的血液中。那些以前几乎不知道“爱国主义”意味着什么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而这个世界往往由对立的民族团体组成。中华民族团体在数量上是最大的,并且占据了(如果包括殖民地)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大的地理区域。可惜,与许多拥有不到中国1/20的领土和人口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影响力却更小,受到的尊重也更少。
那时的中国人民和现在一样,是一个过于骄傲和敏感的民族,他们不甘心在世界各民族中处于永久的劣势地位。不要指望他们默许西方人或日本人的种族优越感;显而易见,任何种族优越性理论(在最了解该理论的人看来)都是错误的。中国人民拒绝这种谬论的原因远远不只是虚荣心在作祟。因此,当受过教育和富有思想的阶级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并将之与自己心中的祖国形象相比较时,他们必定会在可以改变的环境中或在可以纠正的错误中寻找这种恶果的根源,而不是与自然法则做徒劳的斗争。因此,中国维新派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该党派又分裂为两大派系。右派(保守派)相信循序渐进的发展,不会出现灾难性的政治剧变;左派(改革派)坚持认为,在新的基础上对国家生活进行根本性的重建是救国的必要条件,只要允许清王朝(他们认为清朝是垂死的、无能的、极度腐败的)出面捣乱,这样的重建就是不可能的。
康有为的家乡在广东南海,他的弟子们因此称呼他“南海”,他是19世纪最后10年里中国维新改良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由于他对皇帝忠贞不渝,因此要另外归类——“温和派”。然而,在绝大多数中国的当权派看来,他写给皇帝的奏折直接导致了1898年著名的“百日维新”,表明他是中华帝国最危险的“极端派”。他和他的著作充满了对汉族和满族官僚中正统且“可敬”成员的恐惧和仇恨,犹如中世纪欧洲异教和巫术引起的恐怖,抑或当今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在各自反对者中引起的憎恶。如果允许跨时空比喻的话,那么,康有为就是1898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他坚持的观点贯穿他的一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仅仅15年之后,他注定会成为“死硬派”和“守旧派”,遭遇轻蔑和漠视、嘲弄和拒绝。其实,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各个时代,都会有类似的厄运降临在大量宗教改革家、社会改革家和政治改革家的身上。9
早在康有为“异端学说”的具体思路呈给皇上之前,他就已经在自己的家乡广州树立了美好的声誉。他是一位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倡导者,也是一位大胆而有独创性的儒家经典评论家,还是“今文派”的领袖(章太炎是“古文派”领袖)。他始终是皇帝的忠实臣民,也始终是孔子的虔诚信徒,并视之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之父”。到1898年,他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波求知若渴的学生。康有为作为年轻人的导师和激励者,其美誉从广东传遍了中国各地,他的教育造诣最终引起了湖南巡抚陈宝箴10、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帝师翁同龢等具有较高官方影响力和威望之人士的关注。
翁同龢,祖籍江苏,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1856年,他在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获得了中国学术界最高的荣誉——状元。从此,他踏入官场,并平步青云,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同文馆(当时在北京新成立的外语学院)总教习。作为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他在中国文学界被视为18世纪作家刘墉的精神传人,而后者正是乾隆盛世时期的文人代表,也是装饰门面的人物。翁同龢的学者生涯以其被任命为帝师而达到顶峰,他在这一职位上连续侍奉了同治和光绪两任皇帝。
翁同龢是儒家学派的大师,是传统文化的一流学者,也是一个思想开阔自由的人,对康有为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请教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陈宝箴、许景澄,早在决定命运的1898年,他就向皇帝力荐康有为,并与他的皇帝学生讨论了这位广东改革家的政治信条之要点。尽管到1898年,光绪皇帝已年近三十,不再是个“学生”了,但翁同龢还是能够畅通无阻地觐见皇帝,因为帝师的职位具有终身的特权,包括私人谒见的权利。此外,帝师有权在皇帝跟前畅所欲言,省去了其他官员(无论官位多么尊贵)必须遵循的传统而烦琐的君臣礼节。
像翁同龢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居然能使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得到皇帝的赞许,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一方面,它为翁同龢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并显示出他完全没有心生嫉妒(当时中国朝廷官员的一种恶习),也不受那个时代文人的迂腐保守主义之束缚;另一方面,它也表明,皇帝本人绝不是某些作家笔下的“白痴、弱智,脑袋里一团糨糊,自命不凡的庸人”,那只是为博取读者怜悯和挑起看客嘲弄的文学手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翁同龢比朝廷里任何人(包括慈禧太后在内)都更了解光绪的性格和能力;况且,如果这位皇帝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话,翁同龢也会认为,没有必要与一个既不懂改革之道也不愿付诸实施的小皇帝讨论康有为的改革计划。
1898年的春天,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少年皇帝,后者在前者的心坎上留下了一种毋庸置疑的印象。许多年以后,我曾有几次机会同康有为讨论那一年发生的事,他谈到光绪皇帝的时候,每次都带着近乎崇敬的语气。如果当时的热情改革家发现自己的国君和支持者缺乏智慧、爱国主义或改革热忱,那他很可能会加入那些逐渐壮大且认定“天命已不再归于皇家,清王朝是中国进步道路上必须清除的障碍”的革命阵营。如果说康有为早年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么他在见到君主的一刹那间,就把这些念头从脑海中统统赶跑了,因为这位君主不仅支持和赞同维新运动,而且渴望担起其领袖责任。

康有为
有人说,康有为就是帝师。其实,他从未担任过这个职位,他与皇帝的会面也很少。但在一次觐见中,皇帝授予他一种崇高的特权,即不通过普通的官方渠道而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康有为欣然接受了这种特权,接着,他的一系列奏折引来了一系列著名的改革诏令,并于1898年夏天逐一出台、匆忙颁布,这就是所谓的“百日维新”。在当时的中国,这些诏令既让寥若晨星的自由主义者感到满意和欣慰,也让绝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感到震惊并提出了强烈抗议。
人们习惯于批判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及其载体——改革诏令,认为他的构思过于草率,不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条件,与中华文明之精神格格不入。这些批驳的观点并非都是不合理的,但批驳者们自己也想尝试把康有为的设想变为现实,只不过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快速转变为西方民主模式,与康有为通过缓和的改良手段形成对立。人过中年之后,康有为也承认自己的一些改革计划是不明智的,比如,建议放弃中国服装,转而选择西方服装,这将意味着中国丝绸工业的毁灭。但是,他的大部分改革设想或为此进行的论战,并没有异想天开或不合理之处。遗憾的是,康有为及其“帝王同谋”建立梦想新中国的努力以完败收场了,不是因为他们的梦想本身是荒谬的,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那些非个人性格和智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讲到这些问题。
5 1895年,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6 1895年,俄国、德国、法国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使得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从日本手中将其赎回。3年后,东北又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7 参见亚历克西斯·克劳斯《衰退中的中国》(伦敦:1900年)第184页,“俄国采取的措施……相当于对满洲的非正式兼并……满洲实际上不仅是俄国的一个省,而且已经由俄国军队投资,等待俄国首都开放和发展的时机”。鉴于满洲地区的现状,克劳斯的以下补充说明值得关注。他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大约有1400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农人和土匪。后者总是掠夺前者……接下来的一代人也是这样的状况,唯一的变化就是人口翻倍了。”《泰晤士报》在评论杨格窝尔德《满洲的国际关系》(192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书时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日本发动了一场战争,满洲和蒙古早就被沙皇俄国吞并了。”这篇文章发表于1930年2月6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比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满洲发动“九一八事变”)早19个月之多。此处的1904—1905年战事是指日本与俄国为争夺各自利益而在中国东北大地上掀起的一场帝国主义兼并战。
8 1英里=1.609344千米。——译者注
9 刘易斯·爱因斯坦先生(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部长)在1928年11月的《双周评论》(第581页)中告诉我们,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先生(美国第31任总统)1899年访问中国时,刘易斯被任命为政府工程师,就是因为这个事实——“当时,年轻的光绪在孙中山的建议下,试图将西方的改革引入中国,并希望一名美国工程师担任新成立的矿务局局长”。不用说,孙中山从来没有向光绪皇帝提过建议。试想一下,还有什么比“把康有为同孙中山搞混”更让康有为苦恼的事情吗?既然他们都已经踏上了“这些声音之外的和平之路”,或许他俩都会认识到对方曾以各自的方式为祖国振兴大业鞠躬尽瘁。
10 不要将“陈宝箴”与“陈宝琛”混淆,后者后来成了宣统皇帝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