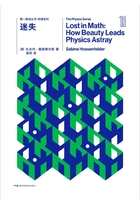
第1章
物理学的隐秘规则
优秀科学家的难题
我会创造新的自然定律,也以此为生。这世上有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任务是让我们的粒子物理理论更加尽善尽美,我也是其中之一。在知识的殿堂中,我们是那些在地下室挖来挖去的人,探索着这座殿堂的地基。我们检查每一条地缝,对现有理论的缺陷满心疑虑;如果我们有所发现,就会叫实验人员来发掘更深的地层。20世纪,实验人员和理论学家之间的这种分工一直运行良好,但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却行不通了,这很让人震惊。
我在理论物理领域待了20年,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在以研究没人见过的东西为业。他们编造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新理论,比如我们的宇宙只是无穷多个宇宙中的一个,而所有这些宇宙合起来就成了“多重宇宙”。他们发明了数十种新粒子,宣称我们是更高维空间的投影,而这一空间产生于虫洞,多遥远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虫洞相连。
这些想法有极大争议,然而也非常流行,纯属猜测但又引人入胜,中看但并不中用。大部分都很难验证,实际上可以说是无法验证;另外一些就连理论上都没法验证。这些想法的共同之处是,支持这些想法的理论学家都坚信,他们用到的数学中有自然真理的一个要素。他们相信,他们的理论太优秀了,不可能不成立。
如何发明新的自然定律——确立新的定理——不是在课堂上能学到的,也不是教科书会讲的。物理学家学会这些,部分是通过研究科技史,但更多的是通过向年长的同事、朋友、引导人、导师和评论家学习。这些技能代代相传,主要都是些经验之谈,是一种来之不易的直觉,知道什么能奏效。如果被问到某项新提出但尚未验证的理论前景如何,物理学家会援引自然、简洁、优雅、美丽的概念。这些隐秘规则在物理学的基础中无处不在,是无价之宝,但也与科学的客观性使命完全冲突。
这些隐秘规则对我们非常不利。尽管我们新提出了大量自然定律,但全都未经证实。在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职业陷入危机的时候,我自己也陷入了个人危机。我不再肯定,在物理学的地基中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不是,那我又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呢?
我投身物理学,是因为我无法理解人类行为。我投身物理学,是因为数学会告诉我物理学是怎么回事。我喜欢井井有条,喜欢丁是丁、卯是卯的机器,喜欢数学对自然发号施令。20年过去了,阻碍我理解物理学的,是我仍然无法理解人类行为。
“我们没法用严格的数学规则来定义,某个理论是不是美丽动人。”吉安·弗朗切斯科·朱迪切[1](Gian Francesco Giudice)说,“不过,看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对定理的美丽和优雅趋之若鹜,还是很让人惊讶的。我要是告诉你:‘你看,我有篇新文章,这个理论可漂亮了。’我用不着告诉你理论的细节,你就能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激动了。对吧?”
我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找他聊:为什么自然定律必须在意我的发现美不美?我和宇宙之间的这种关联似乎非常神秘,非常浪漫,也一点都不像我。
但吉安认为大自然在意的并不是我的发现美不美,而是他的发现美不美。
他说:“大部分时候这都是直觉,没有什么能用数学术语来衡量:这就是所谓的物理直觉。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对美丽的看法有极为重要的区别。解释经验事实和运用基本原则要正确结合,才能让物理理论又成功又美丽。”
吉安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理论部门的负责人。核子中心运行着目前最大的粒子对撞机——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这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对物质基本结构最切近的审视:价值60亿美元、长27 km的地下环形管道,用来加速质子,使之以接近光速的速度互相撞个粉碎。
这台对撞机是各种极端的集大成者:超导磁铁、超高真空、计算机集群(实验中每秒能记录约3GB数据——与数千本电子书相当)。数千名科学家荟萃于此,集数十年研究之功,还用了数十亿高科技零部件,目的只有一个:找出质子是由什么构成的。
吉安接着说道:“物理学这个游戏十分精妙。发现其规则不仅需要理性,还需要主观判断。对我来说,正是这些不合情理之处让物理学趣味横生、激动人心。”
我是从自己的公寓打的这通电话,我周围堆满了纸箱。我在斯德哥尔摩的职位已经到期,是时候向前看,去找点别的研究经费了。
毕业时我觉得,理论物理的圈子会成为我的家,一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探寻者的家,探寻着去理解大自然。但我的同事们一边鼓吹着不偏不倚的经验判断极为重要,一边又用审美标准来为自己钟爱的理论辩护,在他们中间,我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了。
吉安说道:“如果你一直想攻克一个问题,那当你找到答案时,你就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狂喜。在这一时刻,你突然就开始看到,在你的推理背后出现了结构。”
吉安的研究集中在发展粒子物理的新理论,希望解决现有理论中的问题。他开创了一种方法,可以量化一个理论有多自然。这是种数学检验标准,从中可以确定一个理论有多依赖于几乎不可能的巧合[2]。一个理论越是自然,就越不需要巧合,也越有魅力。
他说:“物理理论中的美感必定是我们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由社会构想出来的。这种美感能触动心弦。当你在一个美丽的理论面前张口结舌时,你的情感反应就跟你站在一件艺术品面前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不知道的是,这有什么关系。我很怀疑,我的美感能成为发现自然界基本定律的可靠指南,就是这些定律支配着实实在在的行为表现,但我对这样的实在并没有直接的观感,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如果这种美感在我的大脑中与生俱来,那就应该曾在自然选择中大有裨益。但懂得量子引力能有什么样的进化优势呢?
尽管创作美丽的作品会让人肃然起敬,但科学并不是艺术。我们寻找理论可不是为了唤起情感反应,我们是在为观察到的一切寻求解释。科学事业要有条有理,这样才能克服人类认知缺陷,避免陷入直觉的谬误。科学无关乎情感,而是关乎数字和方程,关乎数据和图表,关乎事实和逻辑。
我想,我挺希望他证明我错了。
我问吉安在最近的LHC数据中有何发现,他说:“我们很困惑。”终于,我明白了一点什么。
失败
LHC在运行的头几年,尽职尽责地产生了一种叫作希格斯玻色子的粒子,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人预言有这种粒子存在。我和同事们对这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寄予厚望,希望它除了能证实人人都毫无疑问的事情之外,还能做到更多。我们在物理学的地基中发现了一些缝隙,这让我们坚信LHC也会产生别的迄今尚未发现的粒子。我们错了。LHC没有任何发现能支持我们新提出的自然规律。
我们天体物理学同行也没好到哪儿去。20世纪30年代,他们发现星系团所包含的质量,比所有可见物质加在一起所能解释的要多得多。即使考虑到数据中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还需要一种新的“暗物质”才能解释观测结果。暗物质的万有引力的证据越来越多,因此可以肯定暗物质是存在的。然而,暗物质由什么组成仍然是个谜。天体物理学家相信,这是某种地球上不存在的粒子,既不吸收光线,也不发射光线。他们想出了新的自然规律和未经证实的理论,以指导建设探测器,验证他们的想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数十个实验小组一直在寻找这些假想的暗物质粒子。他们一无所获,新理论仍然得不到证实。
宇宙学的前景看起来也同样黯淡。这个领域的物理学家在试图了解是什么让宇宙膨胀得越来越快,这一观测结果被归因于“暗能量”,但他们同样徒劳无功。他们可以从数学上证明,这层奇怪的基底只不过是真空携带的能量,而目前他们还算不出来这一能量的大小。这是物理学家想要一窥究竟的地基上的缝隙之一,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发现能支持他们想出来解释暗能量的新理论。
同时,在量子物理学领域,我们的同行想要改进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理论。他们的行动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什么东西跟可测量实体不符,那么其数学结构就肯定有问题。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尼尔斯·玻尓(Niels Bohr)和20世纪另外一些物理学偶像都曾抱怨:“没有人懂量子力学。”这让他们很恼火。量子领域的研究人员想发明更好的理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相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缝隙。所有实验都支持来自20世纪的无法理解的理论作出的预测。新理论呢?都还只是未经检验的猜测而已。
为了找出新的自然定律,人们付出了极大心血,但全都付诸东流。30多年了,我们一直未能让物理学的地基更加稳固。
所以,你想知道是什么让这个世界凝为一体?宇宙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的存在遵循什么规律?你最有可能找到答案的方法就是,沿着事实的轨迹一直向下追寻到科学的地下室。一直跟着这条轨迹,直到事实也只剩一鳞半爪,而在你前进的路上,那些争论着谁的理论更漂亮的理论家挡着道。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抵达地基了。
物理学的地基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理论中,就我们目前所知无法从更简单的东西中推导出来的那些成分。这是物理学大厦的最底层,目前我们有空间、时间和25种粒子,还有规定这些元素的行为表现的方程式。因此,我的研究主题就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粒子,它们不时相撞,或形成合成物。不要认为这些粒子是小球:它们可不是小球,因为有量子力学管着(稍后详述)。最好把这些粒子想象成可以是任何形状的云朵。
在物理学的最底层,我们只处理无法再进一步分解的粒子,并称之为“基本粒子”。我们现在只知道,基本粒子没有更底层的结构。但基本粒子可以结合起来,组成原子、分子、蛋白质——由此也产生了我们周围能看到的各种结构。组成你、我以及宇宙间万物的,就是这25种粒子。
但这些粒子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粒子之间的关系,是决定粒子间相互作用的原则,是生成了宇宙并让我们得以存在的那些定律的结构体系。在我们的游戏中,我们关心的是规则,而不是零件。而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大自然是由数学规则决定的。
数学制造
物理学中的理论是由数学构成的。我们运用数学不是因为我们想吓跑那些不熟悉微分几何或阶化李代数的人,而是因为我们是傻瓜。数学让我们保持诚实——让我们不至于自欺欺人。你的数学可能出错,但你没法撒谎。
我们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任务,就是发展数学方法,或用于描述现有观测结果,或用于作出预测,指导实验策略。在理论发展中运用数学,加强了逻辑上的严谨和内在的一致,能确保理论没有歧义,结论也可以重现。
数学在物理学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这一质量标准如今被严格执行。今天我们建立的理论是一套套假设——数学关系或定义,以及将数学与现实世界中的可观测内容联系起来的阐释。
但并不是我们写下假设,然后用一系列定理和证明得出可观测结果就算是发展出理论了。在物理学中,理论几乎总是始于松松散散、东拼西凑的思想。打扫物理学家在发展理论时留下的烂摊子,找到一套干净利落的假设并能从中推导出整个理论,这项任务通常都留给了我们搞数学物理的同行——这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不是物理学。
大多数时候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已经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不过物理学家总会抱怨数学家过分讲究,数学家则会抱怨物理学家过于马虎。不过两方面都非常清楚,其中一个领域的进展也会推动另一个领域向前迈进。从概率论到混沌理论,再到以现代粒子物理为基础的量子场论,数学和物理一直齐头并进。
但物理学并不是数学。成功的理论除了要内在一致(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结论),还必须与观测结果一致(不能与数据不符)。我所在的物理学领域研究的是最基本的问题,对一致性有很严格的要求。现有的数据非常多,因此对新提出的理论根本不可能都进行所有必要的计算。也没必要做所有计算,因为有一条捷径:我们先证明,新理论与已经充分证实的旧理论在测量精度内是一致的,从而能够重现旧理论的成果。这样一来,我们就只需要加上用新理论解释更多数据所需的计算。
要证明新理论能重现成功的旧理论的全部成果非常困难。原因在于,新理论可能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数学框架,跟旧理论用的数学框架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要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两种理论对已经做出的观测无论如何都会得出同样的预测,往往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来重新阐述新理论。如果新理论直接应用了旧理论的数学,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很简单,但如果用的是全新的框架,那很可能就难上加难了。
比如说,爱因斯坦就花了多年时间来努力证明:他关于万有引力的新理论——广义相对论会重现其前身——牛顿引力理论的成功。问题并不在于他的理论出错了,而在于他并不知道在自己的理论中怎么才能把牛顿的重力势能找出来。爱因斯坦的数学全都是对的,但缺乏与现实世界的紧密关联。在好几次试错之后,他才找到证明这一点的正确方法。数学是对的并不能保证理论就也是对的。
我们在物理学中运用数学还有别的原因。除了让我们保持诚实,数学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经济、最清晰的术语体系。语言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意义取决于上下文和阐释。但数学并不在意文化和历史。如果一千个人阅读同一本书,他们读到的会是一千本不同的书;但如果一千个人去读同一个公式,他们读到的就是同一个公式。
不过,我们在物理学中运用数学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可以这么做。
物理学的特权
尽管逻辑一致性始终是对科学理论的要求,但也并不是所有学科都适合数学建模。如果数据没那么严谨,那用严格的语言来解释数据也没什么意义。而在所有科学领域中,物理学研究的是最简单的系统,因此成了数学建模的理想对象。
在物理学中,研究主题十分容易重现。我们非常了解如何控制实验环境,也知道可以忽略哪些影响而不至于牺牲精度。实验结果很难重现的学科有心理学,因为没有哪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也很少能确切地知道,是哪些人类的怪癖在起作用。但物理学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氦原子不会饿肚子,周一和周五的脾性也都会一样好。
这种精确是物理学能如此成功的原因,但同时也让物理学变得如此困难。对于不谙此道的人来说,那么多公式可能会显得高不可攀,但跟这些公式打交道其实只是教育和习惯问题而已。让物理学如此困难的并不是要理解数学。真正的困难是找到合用的数学。你可不能随便拿点儿看起来像数学的东西过来,就说这是个物理学理论。要求新理论有一致性——既内在一致,也跟实验一致,跟所有实验都要一致,这才是物理学如此困难的原因。
理论物理是一门高度发展的学科。我们今天所用的理论经受过大量实验的检验。每当理论通过了另一项检验,要想对理论再做任何改进都会变得更加困难。新理论要顾及现有理论的所有成功之处,此外还得再好上那么一点。
只要物理学家是在发展理论好解释现有的或即将进行的实验,成功就意味着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正确的数字。但我们的理论能描述的观测结果越多,就越难检验所提出的改进。从预测中微子到发现中微子花了25年,确认希格斯玻色子花了将近50年,直接探测到引力波则花了100年。现在,检验新的自然界基本定律要花的时间,可能会比一位科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还要长。这迫使理论学家不得不采用经验以外的标准,来决定追寻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审美诉求就是其中之一。
在我们寻找新想法的过程中,美扮演了诸多角色。美是指引,是奖赏,也是动力。美同样也是系统性的偏误。
看不见的朋友
搬运工已经搬走了我那些箱子,因为知道我不会待在这儿,大部分箱子我拆都没拆。空荡荡的橱柜里,回响着搬家的声音。我给德国亚琛的物理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ämer)打了个电话,他是我朋友,也是同事。
迈克尔研究超对称理论,简称超对称。超对称理论预测了大量仍未发现的基本粒子,给每一种已经发现的粒子都配了一个小伙伴,此外还提出了几种别的粒子。在人们提出的新自然定律中,目前最受欢迎的就是超对称。我有成千上万名同事都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押在了超对称上,但直到现在,这些额外的粒子还一个都没被发现。
“我觉得我会开始致力于超对称研究是因为,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人们就在搞这个,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迈克尔说。
超对称的数学与已经完整建立的理论所用的数学非常相似,标准的物理课程则为学生研究超对称做了很好的准备。迈克尔说:“这个框架定义得很好,非常容易。”这是个上佳选择。迈克尔在2004年拿到了终身职位,如今领导着德国研究基金会资助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新物理研究小组。
“我也很喜欢对称。这让物理学对我来说充满了吸引力。”
我在前面提到过,在我们了解世界由什么组成的追寻中,已经发现了25种不同的基本粒子。超对称理论让这个集合变得更完整,加进去了一组尚未发现的伴侣粒子,每种已知粒子都有一个伴侣,还有几种是额外的。超对称理论的完备性非常吸引人,因为已知粒子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即费米子和玻色子[分别以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萨特延德拉·纳特·玻色(Satyendra Nath Boson)命名],而超对称理论解释了这两种类型为何有共同的归属。
费米子极为特立独行。无论你怎么尝试,都不可能让两个费米子在同一个位置有同样的行为——两者之间总会有些不同之处。但玻色子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很乐意彼此携手共舞。电子就是一种费米子,因此只能围绕原子核居于各自独立的电子层。如果电子是玻色子,就可以一起待在同一个电子层,宇宙中也就没有化学这回事了;同样也不会有化学家,因为我们自身的存在就依赖于小小的费米子拒绝共享空间。
超对称理论假定,如果将玻色子和费米子交换,自然定律也还会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每种已知玻色子一定有一种费米子伴侣,而每种已知费米子也都有一种玻色子伴侣。但除了跟各自伴侣的从属关系有所不同之外,这些伴侣粒子必须全都等同。
由于所有已知粒子都不符合要求,我们得出结论,这些已知粒子之间不存在超对称对。因此,必定有新的粒子等着我们去发现。这就好像我们有一堆零零散散的罐子和盖子,于是坚信肯定会有与这些相匹配的盖子和罐子就在什么地方。
但是,超对称理论的方程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超对称伴侣的质量是多少。因为产生更重的粒子需要更多能量,所以粒子的质量越大,就越难被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了解到,就算超级伴侣存在也必定非常重,我们的实验能量还不够高,产生不出来。
超对称理论有很多好处。除了揭示出玻色子和费米子是一体两面,还会有助于统一基本作用力,并有可能解释一些数值上的巧合。此外,有些超对称粒子刚好具备组成暗物质所需要的性质。后续章节我会告诉你们更多细节。
超对称理论与现有理论非常吻合,因此很多物理学家坚信,超对称必须是对的。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物理学家丹·胡珀(Dan Hooper)写道:“尽管有成百上千名物理学家投入了大量心血,做实验想要找到这些粒子,但还没有观测或探测到任何超级伴侣。”然而,“这对那些热切期望着自然界就是以超对称的方式形成的理论物理学家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些科学家里面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超对称理论背后的思想太完美、太优雅,不可能不是我们宇宙的一部分。这些想法解决了那么多问题,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契合也是那么自然而然。对这些真正的信徒来说,超级伴侣粒子就是必须存在。”[3]
胡珀强调了这一信念的力量,他不是一个人。英国物理学家杰夫·福肖(Jeff Forshaw)指出:“对很多理论物理学家来说,很难相信会有什么地方,超对称理论会不起作用。”[4]在2014年《科学美国人》的一篇题为《超对称理论与物理学的危机》的文章中,粒子物理学家玛丽亚·斯皮罗普录(Maria Spiropulu)和约瑟夫·莱肯(Joseph Lykken)提出了他们的期望,即认为证据最后一定会出现,并断言:“如果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粒子物理学家都相信超对称理论必须成立,恐怕也并非夸大其词。”[5]
有一种与玻色子和费米子有关的对称,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不可能成立,因为似乎有数学证据为其反证,但这反而增加了超对称的吸引力[6]。但是,没有证据好过一切假设。结果表明,如果该证据的假设条件可以放宽松点,超对称理论就会成为可能适应现有理论的最大的对称性[7]。大自然怎么可能不去运用这么美丽的思想呢?
迈克尔回忆道:“对我来说,超对称最美的一面始终是,这是那种最终极的对称性。我觉得这很有吸引力。在了解到这个例外之后我觉得‘哦,好有意思呀’,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想法——把对称性强加进去,就能得到正确的自然定律,就算你并不理解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似乎是个非常强大的原则。因此在我看来,对称性值得追求。”
20世纪90年代晚期,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最简单的超对称模型已经与数据有了矛盾,人们已经开始设计更复杂但仍然有望成功的模型[8]。对我来说,这个领域如果没有首先检测到预测中的粒子,似乎就说不出来什么新鲜事儿。在检测到新粒子之前,我决定先离超对称远点。
但一直没有检测到新粒子。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一直运行到2000年,都没有发现任何超对称的证据。正负质子对撞机(Tevatron)达到的能量比LEP高得多,并一直运行到了2011年,但同样一无所获。大型强子对撞机则重新利用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轨道,也达到了更高的能量层级,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运行,但超对称仍然缘悭一面。
然而我仍然在担心,担心没有投身这一领域是不是犯了个大错,毕竟有那么多同行都曾认为,如今也仍然认为,还是有很大希望。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大型强子对撞机必定会出点什么新东西,因为如若不然,那么根据吉安·弗朗切斯科·朱迪切等人提出的标准,现有的对粒子物理的最佳描述——标准模型——就不自然了。这些用来检验某个理论是否合乎自然的数学规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如果哪个理论里有特别大或者特别小的数字,那这个理论就谈不上漂亮。
在本书剩下的部分中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一信念是否合理。现在我们就说这个信念非常普遍就够了。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朱迪切解释道:“自然性这一概念……是通过学术群体的‘集体活动’形成的,他们日益强调其与标准模型外的物理学存在的关系。”[9]而他们越是研究自然性,就越是会坚信,要避免丑陋不堪的数字巧合,就必须尽快有新的发现。
迈克尔说:“事后来看,人们对这种自然性的观点,重视得让人吃惊。回头去看,人们只是重复着同一个观点,一遍又一遍,但对这个观点从未真正反思。同样的话,他们说了十年。更加让人吃惊的是,模型构建中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这个观点为主要依据的。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挺奇怪。我仍然觉得自然很迷人,但我不再相信自然性会指向LHC的新物理学。”
LHC的第一次运行结束于2013年2月,之后关闭,以进行升级。第二次运行始于2015年4月,能量更高。现在是2015年10月,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预计将看到第二次运行的初步结果。
迈克尔说:“你应该跟阿尔卡尼—哈米德(Nima Arkani-Hamed)聊聊。他赞成自然性标准,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真的挺有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很神奇的。他会在某个领域钻研一段时间,收获一些追随者,然后下一年又转身研究另一个领域。十年前他致力于这个自然超对称的模型,谈论起来也总是能让人心悦诚服,于是人人都开始研究这个模型了。但两年之后他就写了这篇关于非自然超对称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末,尼玛·阿尔卡尼—哈米德就已经声名鹊起,那时候他跟萨瓦斯·季莫普洛斯(Savas Dimopoulos)和格奥尔基·德瓦利(Gia Dvali)共同提出,我们的宇宙也许还14有更多维度,这些维度蜷曲在极小的半径中,但仍能用粒子加速器来验证[10]。存在额外维度的想法并不新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1]。阿尔卡尼—哈米德及其合作者的天才之处在于,指出这些维度仍然很大,因此应该很快就可以验证了;他们这个说法鼓舞了成千上万的物理学家去埋头计算,并披露更多细节。至于说为什么LHC应该能揭示额外维度,论据就是自然性。文中指出:“自然性要求,向额外维度的迁移不可能在能量上超越TeV(特电子伏特)尺度太远[12]。”这是他们第一篇谈到新模型的文章,如今他们提出的这个模型被称为“大额外维度模型”(ADD)。截至目前,这篇文章被引用了5000多次,是物理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
2002年,我自选的博士论文主题是20世纪20年代额外维度理论的一个变化版本,这个题目困住了我。这时我的导师劝我说,最好转而研究其现代版本。于是我也写了一些关于在LHC上检验额外维度的论文。但LHC上未曾见到任何关于额外维度的证据。我开始觉得来自自然性的观点很成问题。尼玛·阿尔卡尼—哈米德如今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教授,也已经从大额外维度模型又转向了超对称理论。
我在心里边记下要找尼玛谈谈。
迈克尔告诉我:“当然,他远比我难以相约。我觉得他不会轻易回电子邮件的。他可是在推动美国整个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他还有个看法就是,我们得有个100TeV的对撞机来检验自然性。现在说不定中国人会给他建这么个对撞机吧——谁知道呢!”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点就是,LHC不会带来证据,证明人们所期待的更美丽的自然规律,因此粒子物理学家再次把希望转移到下一台更大的对撞机上。尼玛极力倡导在中国建造新的环形粒子加速器,其影响甚巨。
但无论在更高的能量层级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发现,LHC目前还是未能找到任何一种新的基本粒子。这就意味着,按照物理学家的标准,正确的理论不自然。我们确实把自己弄进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根据我们自己对美的要求,自然本身成了不自然的。
“我担心吗?我也不知道。我很困惑。”迈克尔说,“我真的很困惑。在LHC之前,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现在呢?我困惑得很。”听起来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