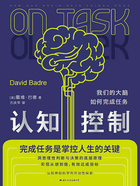
功能丧失的大脑皮质
脑部疾病或者脑部受损的病例不仅证实了认知控制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而且证实了其脆弱性。其脆弱不堪,是由于许多(即便不是大多数)神经功能障碍或精神疾病会导致认知控制遭受一定程度的损伤,这些功能障碍或疾病包括中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等,它们会影响到大脑额叶(frontal lobe),更确切地说,会影响到大脑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简称PFC(图1.1),从而导致丧失认知控制功能。

图1.1 人脑左侧面图表明额叶和前额叶皮质的位置,底部的方位图指明了相关解剖学术语方位。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大脑前额叶皮质对人类最高级的脑功能,包括认知控制功能,至关重要。确实,这种说辞激发了公众无穷的想象力。警匪剧都喜欢把大脑额叶损伤说成非理性暴力行为、人格变化之类案件的罪魁祸首。一个健康网站甚至宣扬“大脑前额叶皮质锻炼十法”,声称通过练习诸如“学习杂耍”这种荒诞之法可以帮助你“专注和思考”。
在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神经科学家曾一度怀疑大脑前额叶皮质可能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功能,或者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辅助。19世纪末20世纪初,神经科学家开始在动物实验中精准地破坏动物大脑的不同部位,探究它们到底有什么功能。如果动物大脑的某部位受到损伤后,丧失某一特定功能,那么可以据此推测,该受损的大脑部位对实现此特定功能必不可少。与此同时,在治疗过程中,临床医生通过手术切除了患者的部分大脑,或者给因中风、头部受伤或者因其他原因导致大脑受损的患者做诊断时,都试图得出类似的结论。然而,奇怪的是,这些早期的研究者发现,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因高级认知功能丧失而带来的种种剧变。实际上,很难定义一个具体的功能是否已经完全丧失。
在对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的患者进行神经系统检查时,其感知功能和运动功能显示正常。和医生谈起过去的经历或者熟悉的话题时,患者口齿清楚、谈吐不凡。在对他们进行临床心理测评时,他们比智力衰退的患者组表现更好。哈佛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心理学教科书《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用一个章节回顾当时已知的大脑功能以及他捕捉到的关于大脑前额叶皮质区域的复杂状态。他把额叶比作“迷宫”,并指出:“比如,就目前所知,尚不清楚额叶前部是否有明确的功能……刺激或切除前额叶都没有产生任何异常。”
额叶之谜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不休争论。许多人认为它可能根本不具备重要的智力功能,或至多起辅助作用。1945年,传奇人物神经科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甚至描述了这样一位病人,该病人的额叶在锯木厂的一次事故中受损,在手术切除额叶组织后,病情似乎有所好转。根据赫布的说法,病人手术前性格冲动易怒、办事丢三落四,手术后竟变成了模范公民,唯一可能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是,他每隔几个月便要换一次工作。
可悲的是,当时人们对前额叶的功能所知甚少,为20世纪50年代广泛使用额叶切除术来治疗心理障碍埋下了隐患。毕竟,如果前额叶皮质是多余的,那么,与减轻精神病主要症状的潜在好处相比,切除额叶带来的微小损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额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不幸的是,仅在美国就进行了大约4万例额叶切除手术,术后人们身心受创、苦不堪言,之后此类手术才被禁止。
在诊所之外,流传着另外一个故事,该故事与最初提到的前额叶损伤病例大相径庭。1928年,一位43岁的妇女被转诊到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大约从20岁起,她的癫痫就会定期发作。她向医生坦白:“在料理家务方面,我总是笨手笨脚。”给她治病的医生中有著名的神经外科先驱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彭菲尔德研发的“蒙特利尔疗法”彻底地革新了癫痫的治疗方法——在手术过程中,对清醒患者的大脑进行电激,以定位癫痫病灶并予以切除,同时避免了对功能性皮质的影响。当时的手术情形远非寻常,病人是彭菲尔德唯一的妹妹。
在手术中,当外科医生打开她的头盖骨后,发现了一个位于右额叶的大肿瘤。肿瘤已经在右额叶大面积地扩散,为了切除肿瘤,医生不得不把几乎整个右额叶切掉,直到运动皮质前的大约一厘米处。患者在手术后康复出院。身为妻子兼抚养着六个孩子的母亲,她祈求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但不幸的是,最终她还是由于肿瘤复发去世,距离首次在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接受治疗仅过去两年之久。
尽管患者是自己的至亲使彭菲尔德备受折磨,他还是决定在医学文献中写下妹妹的病况,他认为妹妹的详细病况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人们在早期难以理解额叶损伤患者所处的困境,其中的一个障碍就是:患者缺乏基础参照,无法确切地评估自己在当下的状态。举个例子,患者在被转诊到医生那里时,疾病可能已发展到了中、晚期,肿瘤也许在体内已经生长了数年。因此,难以将病人此时的行为与他们大脑功能紊乱之前的行为相比较。然而,彭菲尔德对自己的妹妹了如指掌。他能描述他所看到的、发生在妹妹身上的变化并进行评论。他描绘了这样一位女性:虽然性情温和乐观、智力正常,却在她多年前能轻松完成的日常活动中显得那么笨拙、无措。
即便切除了大量额叶组织,彭菲尔德妹妹的诚恳、有礼还是给医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柯林·罗素博士(Dr. RussellCollins)给她做过检查后,致信彭菲尔德,提到下述交流情况:
她对我牺牲个人时间为她诊疗的善举表示感谢。她举止非常得体、彬彬有礼,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她非常担心自己失礼而给你带来困扰,也感恩我对她的帮助。当我提到虽然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是她的表现是我有幸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时,她非常礼貌地表达了感激之情。我不禁要问:额叶与更高级人际互动过程到底有多少关系?
她的智力功能,如记忆力、与罗素博士讨论正在阅读的书的能力,也给罗素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切听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在切除了如此大量额叶组织后,丧失了很多功能的病人。
然而,她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却全然不同。她在给彭菲尔德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泰勒医生(Dr. Taylor)问我思维活动是否有所改善,我说‘是的’,但每当我似乎觉得受到鼓舞时,我就会做一系列的蠢事。”她所感觉到的智力丧失根本不是明显的认知丧失或功能丧失,相反,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常因无法完成复杂的日常活动而感到沮丧,根本无力在生活中自处。
例如,有一次,她邀请彭菲尔德和其他四位客人共进晚餐。彭菲尔德描述了他到场时,从妹妹身上感受到的苦恼:
她兴高采烈地盼望着与客人共进晚餐,为此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来筹备。这种事对10年前的她来说轻而易举。而现在,约定的时间到了,她还在厨房忙活,所有的食物都还散落在厨房里,炉子上炖煮着一两样食物,但是沙拉还没备好,肉也还未烹调,长时间的孤军奋战让她茫然且不知所措。显然,她永远也无法把一切都立即备好。
她勉为其难地把所有的食物都尽可能地呈上桌,甚至连一些可能还在“咕噜咕噜”冒泡的都不放过。但是,如果行为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孤立无援的妹妹永远也做不成一顿丰盛的大餐。这不仅仅是掌勺一道菜,然后留置一旁再去着手烹调下一道菜的简单过程,任何有经验之士都知道这一点。相反,你得同时统筹多项准备工作,让一切井井有条:在烹调一道菜的间隙,你得腾出手来开始制作另一道菜,补齐烹调过程中分身乏术的短板,同时检查烹调进度,确保晚餐的各类菜品都约能在同一时间上桌,且温度适口。即便对经验丰富的业余厨师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对于像彭菲尔德妹妹这样没有认知控制能力的患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受损的认知控制系统会带来真真切切的、实质性的损失,完成任务变得充满挑战。对于彭菲尔德的妹妹来说,晚宴的烹制变得难以理解,就像一个失忆症患者难以形成新的记忆,或像一位失语症患者难以开口说话一样。然而,她并没有将这种经历描述为执行力尚缺,而是将其定义为智力受损,即一种自视“愚蠢”的懊恼。
有必要澄清的一点是,她所表达的智力下降并不意味着核心认知(core knowledge)的缺乏。通俗来说,核心认知包括我们储存在大脑里的事实、经验、信仰和对世界的理性认识。相反,认知控制问题可能出现在那些认知基础似乎完全正常甚至比正常人更好的患者当中。
这一悖论在另一个病例中得到了显著的证明。1986年,保罗·埃斯林格(Paul Eslinger)以及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报道了一名44岁的会计师。大约在达马西奥报道其病例的10年前,他曾接受过额叶肿瘤的切除手术。在手术后,他的大部分内侧和腹侧额叶被切除。在对其进行的多次临床测试中,他一直表现出超强的智力水平,甚至在手术10年后也是如此。在韦氏成人智力测验(WAIS)中,他的表现高居不下(位于97%~99%)。他谈吐自如,展示了渊博的学识。例如,他对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的新联邦主义政治哲学(当时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他甚至通过了旨在检测额叶功能障碍的传统神经心理学测试。
尽管患者在医生对他进行的所有测试中表现很出色,但他在诊所外的生活却是一团糟。在脑部受伤之前,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育有两子的父亲,他在当地的教会中表现得很是积极,并且已经晋升为一家建筑公司的审计,前途可谓无可限量。但肿瘤在不断地恶化,渐渐压迫到他的额叶,经手术切除后,他的生活状况开始急转直下。
患者在手术痊愈后重返了工作岗位,但由于屡次迟到,做事杂乱无章,最终失去了原有的工作,随后的几份工作也不尽如人意。他和一个不靠谱的合伙人做了一个风险性极大的商业投资,搭进去了毕生的积蓄。相恋17年的妻子忍无可忍,决意离他而去,并带走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他再婚、离婚,又再婚。在达马西奥报道他的病例时,他正与父母住在一起,并构想着一些疯狂的但达马西奥不能理解的赚钱大计。
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做事的效率同样低下。例如,他早上可能需要准备两个小时才能出门,而且他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洗头。晚上出行的计划一再破灭。有好几次他计划到选定的餐厅就餐,但最终都未能成行,或是即便他到了餐馆,也只能反复地看着菜单。他可以描述出一个更远大的目标,甚至描述出对未来的一个大致计划,例如去餐厅吃饭,但他无法付诸行动。真正捆扰他的,是如何组织和管理以实现短、中期目标。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僵局之中——幻想中有一个终点,但前往终点的多条路径和诸多选择让他不知所措,或者是他一味逃避,在起点处踯躅不前。
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何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很难确定额叶受损后人体会丧失什么功能。同上述患者和彭菲尔德的妹妹一样,额叶受损的患者谈吐流利、知识渊博、互动自如。进一步说,这些患者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诸多问题,也许在许多健全人身上是与生俱来的讨厌之处。在回顾额叶病例的研究时,行为神经学家弗兰克·本森(Frank Benson)汇编了一些神经科医生常用于描述额叶病例的术语。他的“额叶活动性”(Frontal Lobishness)表格(表1.1)列举了行为幼稚、自吹自擂或污言秽语等特征,这些也可能是聚会上那种令人生厌的夸夸其谈者所拥有的特征。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特征因额叶功能紊乱会持续且异常地表现出来,并往往反映了患者的性格变化。
如同难以区分性格特征一样,我们很难区分生活中哪些不顺之事或企业破产是由大脑损伤造成的,而哪些事情可能只是运气不好,或是性情古怪、行事草率等。做出不明智的商业决策,不守时,频繁地更换工作,或者多次结婚、离婚,这些都不是额叶功能紊乱的诊断标志。然而,上述生活中的种种不顺发生的原因以及额叶损伤后这些不顺出现的超高频率都表明,这些患者的一种或多种功能受到了损害,导致他们极易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
现代临床研究通过大量病例表明了额叶受损的患者的共同困境。平均而言,在这些研究中,额叶受损的患者一般在工作和学业上的表现逊于常人,他们无法管理好自己和家庭,且常深陷于财务危机或法律纠纷,许多患者因为生活无法自理只好入院治疗或由他人照料。
表1.1 本森的前额皮质损伤表现(额叶肥大)


改编自弗兰克·本森(D. F. Benson)《思维神经学》(The Neurology of Thinking)中的表11.1.(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尽管如此,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常常被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忽略,也没有可用来评估这些问题的方法。的确,目前仍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用于认知控制测试的黄金标准。患者遭遇的问题各有不同,一些研究发现,我们最广泛使用的现有测量方法仅能解释这些问题的18%~20%。
为什么这些测试结果难以测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原因有几个,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大多数测试过于简单,缺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计划和实施行动时需要面对的开放性和复杂性。1991年,神经心理学家蒂姆·沙利斯(Tim Shallice)和保罗·伯吉斯(Paul Burgess)进行的一项研究让这种错位现象备受关注。该研究将三名因创伤性脑损伤而导致额叶受损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一组头脑健全的人作为对照组。三名患者在智力和认知控制的标准化测试中都表现良好,然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都出现了认知控制方面的问题。例如,其中一名患者曾在治疗时借口要去取咖啡,然后就人间蒸发了,后来才在高尔夫球场里找到了他。
实验要求患者和对照组在伦敦周围自行完成一系列任务。他们首先获得了一笔钱作为预算来完成各种任务,比如买一根面包或者查看昨天的天气状况。这项研究不仅要研究患者的任务完成情况,还要分析他们完成任务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你我可能选择一家可以一次性地购买到两件商品的商店,而不是前往两个不同的商店分别购买这两件商品。研究人员假设患者在完成这种需要高效率的计划时会遇到困难。为了验证这种假设,他们设计出一套复杂的分析方案,不仅可以给完成的任务量打分,还可以为其完成任务的效率以及一路上违反多少规则打分。
然而,最终,研究人员可能甚至不需要他们那套花哨的分析方案就能看到结果。三位患者中的两位勉强完成了八项任务中的一半,而对照组几乎完成了全部任务。唯一一位设法完成所有任务的患者效率很低,一路上违反了好几条规则。比如,该患者虽然成功地找到了前一天的报纸来查看天气,却因为没有付钱被店员追赶。
也许病人只是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所以才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答案是否定的。沙利斯和伯吉斯将错误解读任务纳入分数的考量,在所犯的这些错误中,患者与对照组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相反,他们没能完成任务是由于做事效率低下、违反规则或未能实现目标。
总之,大脑认知控制系统受损会导致患者无法高效、利索地做事。如同我们在其他患者群体身上所看到的其他任意功能丧失一样,问题层出不穷,且颇具破坏性。令临床医生和科学家感到棘手的是,如何帮助人们在实验室之外的复杂现实世界中实现认知控制以完成目标。这是认知控制的真正用武之地,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背景,我们需要进行控制,以便持续性地观察到认知控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