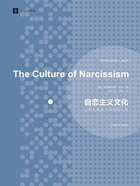
内心的空虚
尽管当代的自白作品可以说是层层设防,但是作者的痛苦还是常常在这些作品中略见一斑。也正是这种痛苦使他们去追求心理安宁。保尔·茨威格曾说他越来越“确信——甚至这都成了一种信仰——我的生活是围绕一个平淡而乏味的核心组成的,这种平淡与乏味使任何东西只要经我接触就变成毫无价值”,他确信“我几乎到30岁都没有从感情冬眠中苏醒过来”,确信“对自我空虚有摆脱不掉的疑心,我所有的谈话和急于迷住读者的努力都只是围绕和装饰了这种空虚,却不能够穿透它,甚至都无法接近它”。弗莱德里克·埃克斯雷的话与此如出一辙:“不管我是不是个作家,我已……培养出了作家的本能,即厌恶随大流。然而不幸的是,我恰恰不能很好地控制并准确地描绘出这种厌恶情绪。”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名流的崇拜以及名流头上那轮迷人、令人激动的光环,把美国人变成了狂慕者与电影迷。传播媒介培养并强化了自恋主义者对显赫名声的梦想,鼓励芸芸众生将自己视为与影星一般的特殊人物并憎恨随“大流”。这一切使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平凡的日常生活。埃克斯雷写道,法兰克·吉福德和纽约巨人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使我坚信一个人是可以出人头地的”。这个“对出人头地的可怕梦想”、这种“我能摆脱平淡而默默无闻的生活幻觉”,纠缠着、甚至在他看来毁灭了他自己。埃克斯雷把他自己或者小说叙述者——这两者的区别总是像往常一样不甚明显——描绘成一个厌倦一切的内心空虚者,一个难以满足的饥渴者,一个等待着去体验那只给少数幸运者保留着的丰富经历以填补内心空虚的人。“埃克斯雷”从许多方面看都只是个平庸之辈,但他却梦想着“只有我才配得上的辉煌的一生!就像米开朗琪罗画中的上帝把手伸向亚当一样,我也希望自己能跨越时代,把我肮脏的手指伸向后代!……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我所不欲的!我既要这,也要那……我要一切!”现代社会对商品以及舒适生活的大肆宣传使人们对其冲动的满足变得理所当然,并使人的本我不必为其形形色色的欲望感到内疚,或对这些无边无际的欲望加以掩饰。但是,正是这种宣传使失败和损失变得不可忍受。当新自恋主义者被告知他可以“既无名望又无自我地生活,他可以从未让他的同胞意识到他在这星球上占据着一块微小空间而生活并死去”时,他不仅会感到无比失望,而且他的自我意识也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埃克斯雷写道:“这一想法几乎使我绝望了,我每次想到它就不由得沮丧万分。”
芸芸众生内心空虚又默默无闻,就试图在明星们身上反射出的光辉中得到温暖。在《来自一个寒冷岛屿的日记》中,埃克斯雷沉溺于对爱德蒙·威尔逊的迷恋之中,并叙述了在威尔逊死后,他是怎样通过访问这位伟人还活着的亲友来设法接近他的偶像。这些记述与其说是与威尔逊有关,还不如说与他自己更有关系。埃克斯雷用传统的颂词一再赞颂威尔逊的文学成就——“20世纪一位伟人”、“50年如一日把自己彻底地奉献给了这门艺术”、“美国文坛……从未见过能与他匹敌的人”——在埃克斯雷心中,威尔逊显然代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即使在这位伟人去世以后,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会使他身后的崇拜者因此变得重要起来。埃克斯雷自己说,他的行动似乎表明“与威尔逊的接近能给我带来幸运”。
另一些自传作家虽没有埃克斯雷的自我意识,但也对他们是如何试图在想象中过着比他们自己更伟大的人物所过的生活作了相同的描述。苏珊·斯特恩就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她之所以为“气象员”派所吸引,是因为与马克·鲁德和伯纳丹·唐恩这样的新闻人物的接触使她感到她终于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唐恩在她看来像个“女皇”,一个“高级女牧师”,她的“光彩”及“高贵”使她与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协会的“二流”与“三流领袖”有着天壤之别。“她身上的一切品质我都想得到。我想像伯纳丹一样被人热爱和敬仰。”当对西雅图7人的审讯使斯特恩本人也成了新闻报道的名人时,她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一个“人物”了——“因为有那么多的人簇拥着我,向我提问,眼巴巴地望着我希望得到我的回答,或只是那么看着我,主动提出为我做事,想以此分得一些光芒。”她现在正处于“鼎盛”时期,她把自己想象得——并使得别人这么看——“浮华、粗俗、强硬、可笑、喜欢冲撞并具有戏剧性。”“不管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对我热爱之极。”她在美国左派最崇尚暴力的组织中的显赫声名,使她能够在大庭广众前实现她对名望的渴求背后的破坏性幻想。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复仇女神,一个女勇士。在她房间的墙壁上,她画了“一个8英尺高的裸体女人,一头金绿色的秀发在飞扬,一面燃烧着的美国国旗插在她的阴道中!”她说她在“服用毒品后的疯狂状态”中“画出了我在内心深处渴望成为的样子: 一个高大的金发女郎,浑身赤裸、全副武装,吞吐着烈火熊熊的美国”。
但是无论是毒品还是破坏的幻想——即使这些幻想是以“革命实践”为具体表现的——都不能平息滋生了这些幻想的内心饥渴。由于别人身上光芒的反射以及崇拜和被崇拜的需要而建立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最终是虚无缥缈的。斯特恩的友谊和恋爱往往以失望、憎恨与相互指责而告终。她抱怨自己对一切都已麻木不仁:“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冷漠,而表面上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尽管她的生活是围绕着政治旋转的,但在她的回忆录中政治从来就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而只是她自己内心愤怨与不安的投影,只是一场充满暴力与焦虑的梦。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许多作品,甚至那些直接产生于政治动乱的作品,在叙述政治时都有着这么一种不真实感。保尔·茨威格于五六十年代在巴黎生活了10年。他参加了抗议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活动,并说这场战争逐渐变成了“渗透他存在的每个领域的一种环境”。然而外部事件只是他叙述中的一个虚幻的部分。它们具有幻觉的性质,只是“恐惧和脆弱”的一个模糊的背景。在抗议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高潮时期,“他回想起他曾在一本关于精神分裂症者的书中看到的一种说法。那位病人带着预言家所有的辛辣口吻说: ‘地球旋转着,我对它毫无信心。’”茨威格说,后来当他只身走入撒哈拉大沙漠以考验自己抵抗严酷自然环境的能力、克服“内心的干涸”时,也曾被同样的感觉所压倒。“地球在旋转着,我对它毫无信心。”
在茨威格对自己生活所作的叙述中,朋友和情人只给了他短暂的所谓幸福。然而尽管他们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却不能止住他“内心生活的不停的空转”。有一个时期,他与一个名叫米歇尔的女孩同居。她“曾使出浑身解数想打破他内心的坚冰,却没有成功”。作者小心翼翼地写下了这个场面,本想抓住他们俩关系的本质。可与此同时茨威格那躲躲闪闪的叙述特点,旨在迷住读者、解除他们对作者的批评而采用的自嘲,以及这一切后面的可怕的虚假感都一一暴露了出来:
仿佛是为了嘲讽屋里的沉重气氛,被灰色灯光照耀着的巴黎圣母院这一庞然大物隔着那神奇的、低声哼响着的车流浮出了夜空。那女孩正坐在地板上,周围散落着一些画笔和一块暗色的木制调色板。男孩躺在床上散了架,或者说他自己觉得像散了架一样,这会儿他卡着嗓子戏剧般地低语着:“我不想做一个人。”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思,把他的焦虑升华到理智的水平,他重复了一句:“我不想做一个人。”他暗示着的原则问题显然不是那个愚钝的姑娘所能领会的,因为他发出了一声叹息并哭了起来。
这样相处了6年之后,“他们结婚了,可短短几周内又离了婚。”茨威格的流放结束了,而他想“以一个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的人所特有的敏捷来表现他的存在”的努力也随之告终了。
而内心的空虚却顽固不化。“我感受到内心的空虚,恐惧地感到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什么也不是。我的身份已经消失,内心深处一片空白、四顾无人。”最后不得不由那位被追求精神治疗的纽约人所推崇的宗教领袖施瓦米·摩克塔南达来教会茨威格使自己的“另一自我”安然入睡。“爸爸”——即父亲——使茨威格领悟到了“心理过程的徒劳无益”。在摩克塔南达的教诲下,茨威格体验了“如释重荷的狂喜”。正如杰里·鲁宾一样,他也把自己的痊愈,把他“康复与欢乐”的感觉归功于自己心理防卫的彻底摧毁。一旦“不再因为自己而不能自拔”,他就使自己“由心理忙碌而组成……由无法停步的思索所粘在一起、并由焦虑所推动的”那一部分得到了彻底的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