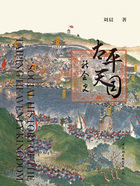
第三节 学术回顾
由于太平天国史研究长期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国内学界对太平天国对立面的关注不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局面略有改观,部分学术成果开始反思太平天国兴亡的外在因素,主要集中在湘、淮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研究,[89]对“民众”与太平天国对立层面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但正是前期研究的积累和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才为本书“太平天国民变”研究领域的推进奠定了基础,某些论断对“反抗反抗者”研究思路的完善有重要启迪。
一 直接提及统治区农民反抗的研究
“天国”民变研究目前尚无专文专著。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直接提及统治区“民变”的文章、著作也为数不多。既往研究仅是把它们附庸于某些太平天国政治、经济制度分析之后,作为制度消极影响的历史表现概述,言尤未详。
第一类,作为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局限的影响被提及。祁龙威关于太平天国后期土地问题的研究提到因“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被破坏和农民生活恶化,导致部分“变节”地区的农民发生抗粮抗租暴动。作为对这一消极影响的反思,祁先生认为“农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能否解决”。[90]龙盛运在部分地区探讨太平天国后期土地制度的实施问题时,提及部分地区农民的抗粮抗租斗争,他认为太平军“在具体行动中并没有积极支持农民反对地主、获得土地的要求,相反地……支持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样太平军便失去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支持,甚至使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91]杨纪枫认为太平天国以“收租局”形式保障封建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实施,从而激起农民反抗,他提出要敢于正视太平天国镇压农民抗租的事实,“以往,人们总拿‘个别将领’、‘革命队伍中的变节分子’等因素解释这一问题,总想替太平天国辩解。实际上愈解释愈不通,最终则跌入历史唯心主义之中”。[92]这些结论颇值深省。
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田赋政策“着佃交粮”,是太平天国的创举。关于“着佃交粮”的得失和影响,学界争论不一。郭毅生、赵德馨等认为“着佃交粮”在政治上有利于太平天国,因为它可以解决太平天国征收田赋与佃农抗租的矛盾,有助于动员广大农民支持太平天国事业,是区别于历代封建政权土地政策的重要特色。[93]王天奖的观点不同,他认为“着佃交粮”在政治上“失大于得”,主要理由是“太平天国治理苏南期间,各州县的农民反抗斗争颇为频繁,光常昭在两年的时间内,大小事件即不下数十次”,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没有满足他们免除封建剥削的正当愿望,反而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农民则在纳租交粮之外,还要负担繁重的杂捐和力役。这样就引起农民的失望、不满以至反抗”,“农民在这种‘着佃交粮’制度下承担各种‘随田’派征的租、粮和杂捐,在经济上是失大于得,以致起而反抗,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致使太平天国与农民的关系日趋紧张和复杂”。王先生的观察在当时具有前瞻性,有启发意义,而且这篇文章是目前提及太平天国统治区农民反抗行动篇幅最长的(约1500字)。[94]王明前也对“着佃交粮”持否定态度,他指出“着佃交粮”并未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未减轻佃农的经济负担。主要依据是“从佃农普遍高涨的抗租情绪看,他们是不太满意‘着佃交粮’的”。[95]
有学者注意到太平天国税收与农民反抗存在一定关联。曹国祉重点考察了太平天国的杂税,将其分为以田亩计征者八类、以户口计征者三类、以营业[96]和财产计征者两类,并就各地征收情况作了简要说明。文章结语部分,作者指出在苛捐杂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固然得不到什么好处,就是地主阶级亦无利可取,农民不得不铤而走险起来反对已蜕化的太平天国地方政府;和这一政府下所保护的地主阶级。从而农民们的抗粮抗租抗捐的事便不断地发生”。作者引征了《平贼纪略》所载无锡安镇东市稍四图庄顾某领导的抗租行动一则,其他未说明。[97]有学者对无锡佃农抗租事件产生怀疑,董蔡时认为“青布扎头为记”是无锡金玉山部枪匪的标志,顾某领导的抗租者亦以青布裹头,他们可能是金某的部下。[98]董蔡时在另一篇文章中就太平天国杂税的类型、影响与曹国祉商榷,他对太平天国杂税体系持肯定观点。[99]
第二类,作为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制度局限的影响被提及。吴志根的研究着重分析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实际运作及性质转化的表现和原因。他指出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性质变化的表现有从打击地主变为保护地主;乡官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镇压;乡官的享乐腐化与违法乱纪。这三个表现都会激起“农民反抗地主和乡官的斗争”。[100]王天奖考察了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分,指出“无论在太平天国的前期或后期,充任太平天国的乡官的大多数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地主阶级分子”。[101]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重申了这一观点,并阐述乡官局的实际作为;关于乡官基层政权为地主阶级掌握的危害,作者指出“特别是后期太平天国在许多州县实行‘着佃交粮’制,他们通过乡官局、收租局、租粮局而强派浮收,更给广大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以致激发了许多起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102]宓汝成就乡官体制的理想(源流)和实际做了探讨,他指出“某些乡官的劣迹对太平天国事业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增剧太平天国与民间的矛盾,以致日益失去民心”;作者还指出民间为反对乡官恶行,有暴动事件发生,太平天国政府径作干预,“使自己与广大民间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推其根源则“与最初建设乡官体制,在人选上只顾一时便益,而滥用非人,大有关系”。[103]张德顺认为乡官制是士绅与太平天国政治互动的中介,乡官则是士绅在太平天国主体的政治流向,但士绅与太平天国双方均存在互动弱化的消极因素,特别是太平天国欲取欲求,以暴力行径将“催粮压力经由乡官转嫁到农民”,导致百姓殴官毁局,地方政权陷入瘫痪,“太平军——乡官——农民原有的经济政治关系大为松弛”。[104]
第三类,作为纠正研究偏向的史实被提及。早在1957年,祁龙威据当时新发现的《自怡日记》等史料撰文质疑常熟《报恩牌坊碑》所记内容的真实性,指出常熟太平天国政府“支持地主,剥削农民”的诸种史实,列举了几起“随着社会经济破产而来的”农民暴动案例,并批评在太平天国研究工作中“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做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做‘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的偏向,即主观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造成的偏向。祁龙威应是较早观察到农民反抗太平天国历史现象的学者。[105]龙盛运对碑文所记内容的理解不同,就常熟农民暴动问题,作者指出“常熟农民暴动中有许多是农民根本拒绝交租而引起的”,“农民拒绝交租,并且集体行动,甚至武装对抗,正是这种矛盾的激化”,“其起因决不是由于太平军的搜刮,而是深刻揭示了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作者同时对太平天国研究工作偏向发表看法:“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倾向必须反对,因为它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正确地揭示规律,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是强调或者只看见缺点,也是不对的”,“有些不好的现象,也有它的两面性。如常熟的一些农民暴动,太平军没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甚至镇压它,这显然不好;但是看不到农民这种要求和行动,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大浪潮下所鼓舞起来的,也是不对的”。龙先生主张“对当时的缺点”,应“具体地、有原则地进行分析”,“实事求是看问题”。[106]祁龙威和龙盛运的研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旨趣均是矫正学术研究的极端化倾向;同时他们对农民反抗太平天国这类特殊历史现象的观察具有开拓性,反映了前辈学者对学术问题和历史现象敏锐的捕捉力。
上文的概述不可能囊括全部提及太平天国统治区农民抗争行动的研究,但文章类型不外乎以上三种,而且这类历史现象均是作为某一研究对象的附生品被简要提及,没有一篇论作专门进行系统分析。
二 宏观论述民众与太平天国关系的研究
太平天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可以说农民向背和农村治乱关系“天国”兴亡。在一些综合性研究(如萧一山《清代通史》,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太平天国兴亡史》等)中,关于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和太平天国历史地位的总结不可避免地涉及太平天国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先扬后抑”的评价之变,常常被研究者引征为评判太平天国功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曹志军、袁蓉认为马克思评价转变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息息相关,其根源是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与西方外交关系的变化,而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大多源于西方报道。[107]李颖则认为马克思是在不同的语义上评价太平天国的,对作为“农民起义”“大规模武力战争”和“小农社会理想试验”的太平天国存有不同的结论。[108]过去研究者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一般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记事》两篇文章为基础。[109]李颖强调应全面掌握相关经典文本,谨防以偏概全。这对选择评价太平天国历史地位的基点提供了新思路,像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110]如果研究者站在清政府和其他太平天国对立面的立场,它是“邪教”,是“反动”的;如果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则是“正统”“正义”“正宗”,是“革命”的;如选择普通百姓的立场,可能是“异端”“洋教”等,不同的基点得出不同的结论。
朱庆葆对太平天国政权兴亡与农民支持与否的关系作了概论。他认为,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至于太平天国为何会失去农民的支持,作者认为:“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111]方之光也探讨了农民问题与太平天国政权的兴衰,他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土地问题,“随着土地问题解决的失败和农民政权封建化的加速,太平天国也就不能重视农民的政治地位与作用,也就不可能在最广泛的范围里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作者虽然指出太平天国没有成功解决农民问题,但肯定它“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昭示着近代中国革命未来的选择道路,从而标志着近代中国革命的开端”。[112]
廖胜将考察重心转至社会基层,主张以社会史的视角自下而上的换位思考。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民众的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兴亡的关系,“按照心理学需求动因理论,民众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归属相爱需求无疑直接构成太平天国兴亡的最原始、最强有力的心理动因”。[113]结合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太平天国比较少见。
美国学者白凯(Kathryn Bernhardt)的博士学位论文《乡村社会与太平天国》重点考察了太平天国及太平天国前后江南农村的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45)》一书。书中有专目述及“民众对太平军的抵制与协助”,关于“抵制”,实际是在探讨民众参加团练的活动。[114]
前面提到美国学者梅尔清的新作实际也是希望通过对众多草野小民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建构战争亲历者对战争的切身感受,使后人品读和反思“What Remains”(被遗漏了什么)。作者把观察的重点置于“浩劫之后”,她发现战争的影响是多元的,不同群体的感受也是多元的,但这种创伤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身体和心理创伤,还包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影响。梅尔清的研究是视角后延的代表;她的结论虽然没有明确得出对太平天国的具体看法,但一切均已通过慈善家余治对社会道德的呼吁、张光烈的丧母之痛、被黥面者的耻辱印象和食人者的心理徘徊等个人情感流露出来,为本书从民众和社会层面研究太平天国提供了有益借鉴。[115]
国外学者对太平天国时期的民众和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等问题在相关论著中常有提及,各自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像美国学者濮友真(Eugene Powers Boardman)、[116]施友忠(Vincent Y.C.Shih)、[117]瓦格纳(Rudolf G.Wagner)、[118]史景迁[119]均是以宗教和意识形态为主线探究太平天国兴亡的历史轨迹,他们强调的疑难问题是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不是基督教,太平天国从基督教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的百姓是怎么看待和怎样对待这种宗教的,这种宗教又是怎样成功感召、动员以致丧失民众的。孔飞力则侧重于专门阐发团练、团民和太平军之间的关系。[120]裴士锋的研究从宏大的全球化视野考察太平天国,他关注的经济、市场、贸易、棉花、茶叶等要素,均是开启斯时社会生活影像的窗口。[121]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论述了整个19世纪中国的“叛乱”运动,着笔最多的则是太平天国,他认为太平天国没能控制农村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要么在不改变旧制度的前提下同化和取代现存权力机构,要么动员农民消灭旧士绅的地位而彻底颠覆现存政治制度,但它均未做到。[122]威瑟斯(John L.Withers)的《天京: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南京,1853—1864》是第一部从城市史角度系统研究太平天国城市的著作。[123]柯慎思(James H.Cole)的短篇小册《民众对抗太平军》是对浙江诸暨包村事件的个案叙述。[124]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一部分学者特别重视中国近代民众运动研究,以小岛晋治教授为代表,成立了“中国民众史研究会”,自1983年起编辑刊行《老百姓的世界——中国民众史札记》,侧重探讨和介绍近代中国一般民众问题和与之有关的资料。小岛晋治的《太平天国运动与现代中国》一书强调从民众文化、区域社会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分析太平天国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125]他的论文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收入“农民革命的思想”“太平天国史诸问题”和“近代农民运动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三个主题的论文,其中部分文章探讨太平天国时期抗粮抗租各种形式的农民斗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认为太平天国时期农民抗争风潮是以太平天国运动扩大发展为基础,肯定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性质。[126]小岛晋治教授较早从“太平天国与世界”的大历史视角关注当时日本人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日本人对太平天国感观,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太平军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太平军发展和衰亡的“民心得失”问题。[127]
菊池秀明从地域社会结构和客家问题探索太平天国起义的根源,他的研究重点在太平天国前夜南中国的客家民众、“移民社会”和“社会变动”。[128]菊池教授的新作《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天国初期史研究》是继钟文典先生大著后的又一部“太平天国开国史”,详细阐述了自太平军兴至定鼎南京期间转战地区的地域社会格局和民众反应。[129]他在另一本著作中认为初期迅猛进军的太平军“得到了底层人民的支持”,而在描述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的失败时认为“太平天国未能充分满足底层人民对它的期待”;作者也观察到“太平天国占领区还发生了多起农民抗租和少交地租的运动”,并指出特别是在1860年以后,“在太平军出入的江南地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130]
夏井春喜以日本各学术机构所藏苏州地主租栈文书为核心资料,根据租栈簿册、鱼鳞册记载的收租情况变动,对太平天国以降近代江南地主制经济和农村社会变迁进行考析,他在《中国近代江南的地主制研究》一书中着重展现太平天国前后江南农村的租佃关系、官民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太平天国政权与苏州农村社会的关系,太平天国政权与苏州土豪徐佩瑗的关系,认为太平天国占领江南与江南农民抗租风潮相辅相成,太平天国占领期间,低田租的客观存在又促生战后的减租政策,加剧了业佃对立。这是日本学界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宏观分析太平天国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研究。[131]
三 其他相关课题研究
一些具体课题与本项研究有关,如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革命性质”、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太平天国各项制度,士绅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团练,太平军军纪,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等。
(一)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革命性质”问题的实质是太平天国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反映了哪些利益诉求。国内学界关于这些问题的集中讨论主要有三个时段:
1.20世纪30—40年代
这一时期关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主要有民族革命、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三种说法。其中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运动、洪秀全等人是民族革命先驱的观点成为主流,萧一山、简又文力持此说。[132]郭廷以持综合革命说,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兼有政治、种族、宗教、经济和社会诸因素。[133]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134]李一尘、张霄鸣、李群杰等则认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135]李群杰还提出“市民革命”的概念,他指出,“只有说它是市民性的农民革命或农民性的市民革命,才得齐全”,“太平天国在历史上是介于中古和近代之间的运动。就其中古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后的农民革命;就其近代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早的市民革命”。[136]这个阶段的争论最终不了了之,未能达成共识。
2.20世纪50—6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成为大陆学界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讨论集中表现为单纯农民革命和兼具资产阶级革命两种观点的分歧。范文澜、胡绳、罗尔纲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性。[137]郭毅生则认为太平天国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的分化与市民等级的兴起密切相关,“由于市民等级是未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承担者,也由于分化的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性质,而这两种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主力军和核心力量”。[138]章开沅按社会内容和斗争手段的双重标准认为太平天国兼具资产积极革命性质和单纯的农民战争性质。[139]与前一阶段的研究不同,这一时期学者们的讨论广泛牵涉太平天国政治、经济制度等具体问题,如对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土地赋税制度、乡官制度的研究,重点是《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性质、“照旧交粮纳税”和“着佃交粮”政策的性质、乡官的阶级成分等问题。大陆学界这场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讨论成为该时期太平天国研究的焦点,争论最终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如太平天国是“单纯农民战争”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和空想性并存、后期太平天国承认旧有土地关系、乡官政权成分复杂等,并在1961年结集出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140]有力地推动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整体发展。另外,简又文的观点较新颖,他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力持宗教革命说,认为太平天国的组织、思想、推动力、各类政策均源于太平基督教,[141]但在60年代出版的《太平天国全史》中又倾向于综合革命说,即太平天国兼具宗教、民族、政治革命。[142]
3.20世纪80—90年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太平天国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得以重新审视。太平天国研究关注的重点从“革命性质”转向“政权性质”的讨论,“文化大革命”期间简单化、脸谱化、教条化的研究倾向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大致有三种观点:(1)农民政权。这是对传统的农民革命性质说的延续,董蔡时的研究是典型。[143](2)封建政权。此立论建立在对太平天国政体、国体和土地政策的考释之上,认为传统的生产关系没有被变更,地主阶级没有被打倒,沈嘉荣、孙祚民持此观点。[144](3)过渡政权。主要有后期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和两重性政权两种意见。王天奖关于太平天国土地、赋税制度和乡官制度的系列研究重在论述政权封建化。[145]李锦全的观点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对立统一的两重性,因此太平天国政权也带有革命性和封建性两重性质。[146]但是该阶段关于政权性质问题的讨论仅仅持续两三年的时间便趋于沉寂,众说纷纭,未达成共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太平天国研究陷入低谷,关于太平天国社会经济史、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乡官制度的研究仍然续有进展,主要是对既往成果的总结、增补。经济研究以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为代表,系据旧著《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增订而成,探讨了“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及性质”“‘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施”“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政策”“‘着佃交粮’制度的实施和性质”“田赋税收政策”“商业政策与货币”等具体问题,基本上肯定太平天国对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意义。[147]典章制度研究的代表是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系据1956年、1963年两个版本的修订本,系统地讨论了太平天国的经济理想和具体措施、乡官制度、赋税制度、供给制度、城市组织和生活制度,对与“民众”主题有关的太平天国政略作了概述。[148]梁义群《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对太平天国的“政权”——政权雏形、战地草创政权、天京政权、地方政权、国体政体、后期政权,进行了全面探讨,表述贡献,总结教训。[149]可见这一时期宏观的概念之争已被搁置。在新时期,受太平天国史研究整体寥落的大环境和史学思想多元化的影响,过去各类学术观点的对立渐趋融合,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已基本避谈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革命性质之类的问题。
百余年的太平天国研究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各时段研究思想解放的先声,然尚有不少问题存争议、待深化。通过上述三个时期研究状况的概述,可见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主要拘泥于宏观的概念之争,有略简单化的倾向,而太平天国政权是否代表农民的利益,是否维护农民的利益,应该将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放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跟进具体的实证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和“民生”问题有助于从一个新角度搁置既往争议,而获得对上述问题更为明晰的诠释。
(二)“士绅”与“民众”
太平天国时期的士绅阶层是当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也是敌对双方争取和倚赖的重要对象。张德顺系统地阐述士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就太平天国据守江南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分化背景和流向、士与太平天国政治文化互动的积极层面和消极层面、两种政体下士人群体的素质和角色功能进行分析,得出“人才政策实践中的见首不见尾现象,是天国无以善终的症结之一”,并认为走出农民运动怪圈的近代民主革命道路是一条“农民”与“知识阶层”结盟的道路。[150]
杨国安考察了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地方民众的政治抉择,指出两湖民众的“从贼”与“反贼”行为更多地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太平军与清军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是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形成的重要纽带之一。最后作者认为,地方精英在广大乡村地区以“卫道”相号召,建立遍布各地州县的团练组织,其最大功用就是阻隔太平军与农民的联系,使太平军在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彻底失败。[151]这项研究实际是在讨论太平天国时期两湖地区地方社会(包括士绅和普通百姓两个群体)的社会分化现象,该文的方法和思路可以借鉴研究太平天国时期全区域全时段的民众分化。
方英重点考察了太平天国时期安徽的士绅群体,指出这一时期安徽士绅阶层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中,在地域政治方面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的分化。[152]太平天国主战场士绅阶层政治分化的诸种面貌和影响流向的因素大致相同,主要原因无外乎敌对双方的文化政策;社会分化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基本可概括为中央政治权力下移、基层社会结构变动和地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等。
贾熟村对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太平天国时期地主阶级的中央政权、地主阶级的地方势力、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曾国藩集团、地主阶级的洋务派。作者逐一考察各集团的代表人物和重要成员,认为太平天国促进了地主阶级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促进了地主阶级的新陈代谢,并指出地主阶级以宗族体系为核心在社会剧变中表现出五类不同的应变姿态,也就是社会分化的类型;关于清政府为何摇而不坠,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在争取有利社会分化力量的斗争中渐处弱势,最终使地主阶级各派大联合,实现剿平“粤匪”的“同治中兴”。[153]张德顺和梁义群的研究都注意到对清朝统治存在离心倾向的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在倒向太平天国后所扮演的角色;梁义群重点分析乡官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对出任乡官的群体进行简单区分。[154]
国外学者关于民众运动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也可为本书提供借鉴。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利用《大清历朝实录》对1796—1911年间社会运动的种类、地理分布、领导者身份、目标、政府应对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探讨政治与社会秩序、社会运动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关联。杨庆堃的定量分析虽然在研究对象类型上有所扩大,却提供了民变研究的一般途径。[155]王国斌(R.Bin Wong)对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和西欧民众的粮食暴动、抗税活动等社会抗争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造成抗粮、抗税暴动的根源在中国和欧洲不同,但它们均与国家形成、政治和经济变化有关;作者进一步以文化和思想作用分析叛乱与革命的源流。[156]陈兴国(Joseph Hing-Kwok Chan)的博士学位论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探讨中华帝制末期民众暴动和抗议的形成模型,指出民众集体行动对动摇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157]亨利·兰斯伯格(Henry A.Landsberger)关注的是长时段乡村农民运动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乡村抗议的目的、方式和思想均进行概括性分析。[158]此外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中国农民运动(1840—1949)》一书以“农民”为核心分析近代中国各阶段农民运动的特点,指出太平天国并未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革命性影响,不足以构成“农民革命”。该书由英国学者柯文南(C.A.Curwen)译为英文。[159]
(三)“团练”
“民团”是民众与太平军对立的一类形式。学界关于团练的研究较多。[160]
郑亦芳、曹国祉、黄细嘉、夏林根对团练制度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论。[161]团练研究往往会与士绅、国家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牛贯杰从晚清团练组织的发展分析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指出团练势力的崛起标志基层社会自身系统发展趋于成熟,导致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关系错位。[162]吴擎华、柯莉娜通过对皖北苗沛霖团练的观察,探讨19世纪中期皖北基层社会结构的嬗变。[163]贺跃夫考察晚清县级以下基层行政官署的设置及职能,认为县级衙门并非皇权的终点,像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不少地区位于县级政权和村落社会之间的重要机构,此结论与近期有学者对“皇权不下县”传统观点的质疑相近;而晚清次县级官署官员数量下降或基层政权的缺失反映了皇权与绅权在互存互利的同时,又互相竞争和牵制的复杂关系;太平天国时期团练兴起,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机构,使士绅权力在乡村社会膨胀。[164]朱淑君认为咸同时期团练话题之兴反映了士绅阶层积极参政的心态,构成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的独特面貌,而团练实践成为后来地方势力扩张的重要资源。[165]
根据上述总结或可发现,太平天国时期团练的主要研究一般是将重点放在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地方基层组织、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把团练置于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分析,以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各社会要素间的关系动态,早先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已进行过尝试。[166]上述研究所得结论基本与孔飞力的观察相近,即“团练”是地方军事化和绅权扩大的表现,最终导致地方社会结构重组、传统名流解体。[167]本书关于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的研究旨趣之一也是希望建构“叛乱”“革命”或“内战”与地方基层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
太平天国时期各地方兴办团练的情况,是团练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杨国安的著作介绍了晚清两湖团练组织的兴起、组织结构、经费来源和功用,以鄂州绅士王家璧为例,说明士绅与团练的关系。[168]郑大发也对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团练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169]此外还有郑小春关于徽州团练、[170]吴竞、万心刚关于无锡团练、[171]朱谐汉关于江西团练、[172]宋桂英关于山东团练的研究。[173]
对具体团练事件的研究,学界着笔最多的是苗沛霖团练。日本学者并木赖寿论述了苗沛霖团练的形成、发展和覆灭历史,并提出苗沛霖团练是“清朝中央对地方行政严重失控、广大农村社会秩序遭到破坏,部分地主实力派趁机实行武装割据的一个最具有典型的事例”,“苗练”的武装割据是它有别于大多数团练的特色。这也是从社会史视角解读政治事件的尝试。[174]
“枪船”是团练的一种类型。曹国祉分析了江浙太湖地区枪船的性质,指出枪船是一股反动土匪武装,社会危害性极大。[175]吴竞论证了苏南、浙北枪船产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枪船势力最终消亡的过程,对1862年夏太平军剿捕枪船的范围、效果、策略进行了评估。[176]贾熟村对太平天国时期枪船的一般情况和历史脉络作了概述。[177]日本学者针谷美和子关于枪船的三篇专论对太平天国时期太湖地区枪船集团的性质、从发展到衰落再到复活的过程、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对太平天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颇为翔实的考述。[178]日本学者小林幸夫通过对周庄乡绅陶煦的政治、社会形象,以及周庄费玉成枪船集团与周庄地方精英复杂关系的研究,阐释费氏集团兴起的原动力和团练在太平天国统治体系中的作用。[179]
近年来,团练研究趋于停滞。崔岷对“团练”与“官府”对立关系的探讨拓展了该项研究,他从团练“抗官”着手,分析团练与官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指出咸同之际团练之乱的后果是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的进一步变动,士绅与国家关系明显疏离,并为未来多端冲突埋下伏笔。关于团练和官府的冲突,傅衣凌先生曾做过引论。[180]
(四)“军纪”
太平军和清军的军纪优劣,直接影响民心向背,关系战争问责。李惠民探讨了太平天国时期的“食人”现象,指出北方战场食人的根源在于饥饿,也有传统迷信、宗教因素的文化背景影响。[181]“食人”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反人性恶俗,太平天国时期不仅在太平军中存在“尽杀妇孺以充食”的现象,清军士兵也有食用太平军俘虏心脏的情况,更多的是存在于杀食同类以求生存的饥民难民群体中。[182]李惠民还考察了北方战场的平民伤害问题,他认为北伐战争殃及百姓的原因复杂,除自杀、清兵和土匪伤害、间接伤亡外,太平军伤害平民的现象不能讳言,所谓“致撄其怒而惹此大劫”,[183]不能作为为太平军屠城行为辩护的理由。[184]侯竹青、陈志刚观察到太平军中的幼童现象,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中幼童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军事环境恶化,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以及太平军对广大城乡社会的有效控制。[185]“食人”“民伤”和“幼童”问题,为了解战争期间反人性的恶俗和太平军军纪提供了新颖视角。
李惠民总体分析太平北伐军的宗教、军事、群众纪律,认为“良好的军纪是处理群众关系的润滑剂”,但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军纪实态与战争后果存在差异。关于太平军的宗教纪律,李惠民认为宗教军纪的作用弊大于利。[186]太平军的宗教纪律,是太平军军纪的重要思想基础。宗教热情和虔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军事行为,但也存在弊端,如信仰的约束不能恒定维持,宗教具有“盲动力”“麻痹力”“迷惑力”等。董丛林希望建立军纪教育和拜上帝思想的关系,他认为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在拜上帝思想的影响下始终带有“非人性”的蒙昧落后成分。[187]还有学者专门对某地域太平军军纪进行研究。王兴福评价浙江太平军军纪基本良好,而清军纪律败坏,但在后期太平军军纪有所松懈,特别是新招抚的天地会、枪船、游民和清朝溃兵。至于社会经济破坏,作者认为内战双方均有责任,不能全部归咎于太平军。[188]
关于太平军军纪的总体研究,简又文、张一文等先生早有论述。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开辟专章讨论太平军与清军军纪,区别时期、地域和各支部队,整合诸家史料,兼顾西人记载;至其结论,观点鲜明,对太平军以“仁义之师”相称,对清军军纪则以“暴行实录”名之。[189]张一文在《太平天国军事史》中专门对太平军的军事纪律做了考察。张著对太平军军纪的执行情况总结如下:(1)太平军纪律众多、全面,执行严格、彻底;(2)太平军的纪律前期好于后期;(3)即使到了后期,太平军由于成分变化,军纪有所败坏,但在陈玉成、李秀成等主力部队中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军纪。[190]
(五)其他
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问题也是探究民众与太平天国关系的一个分项。学界研究较多的是太平天国的女营、女馆制度,李文海、夏春涛、郑春奎均有专论。[191]廖胜和王晓南对太平天国妇女问题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廖胜的《妇女与太平天国社会》一书叙述了洪秀全的妇女思想、太平天国妇女的精神风貌、妇女在太平天国各领域的生活和地位,并通过对“寡妇再嫁”“妇女自由”“妇女教育”“婢女”“缠足”“娼妓”“服饰”等问题的考察论断太平天国在主观上没有任何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主旨。[192]王晓南对太平天国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禁止缠足、寡妇再嫁等问题的民俗背景和文化成因进行分析,同样认为这些形态不构成太平天国妇女解放的依据。[193]王晓南和廖胜合作的另一篇文章考察了太平军的“掳妇”现象。“掳人”是在太平军行军过程中较常见的军纪败坏行为,其中掳掠妇女的现象尤为严重。作者认为太平军通过各种手段强制“掳妇”,造成妇女恐慌和敌对心态,乃至自杀身亡,这是太平天国占领区妇女大量死难的直接原因。[194]王晓南又对太平天国占领区妇女死难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作者以同治《苏州府志》旌表“烈女”为研究范本,对方志所载死于咸同战事的妇女数量、死难方式和地点进行初步估计,认为妇女死难原因有直接死于战争暴力、强制“掳妇”、恐慌心态、吴越地区妇女浓烈的“名节”观等。[195]
像“刺面”问题也关涉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宫明指出“刺面”主要是对逃离太平军者的惩罚,也作为惩罚犯有其他错误者的一种方式;也有对部分“新兄弟”先行刺面的例子,是预防逃跑的措施;被刺面者有相当多的数量,说明确有群众被迫加入太平军,这一行为反映了部分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对立立场,在政治和思想上对太平天国产生了消极影响。[196]
综上所述,关于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目前还缺少系统研究,既有研究虽已提及民众抗争现象,但论作数量较少且仅作为论据附证于太平天国的某些政治、经济问题,而且未有以“民变”视之的先例。“民变”现象涉及太平天国与民众的关系评介,学界对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研究或为零散课题,或为浅说概述,或受时代局限,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民变”问题恰可直观了解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之要领,又可统筹相关各具体问题;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与“反抗反抗者”的视角本身即是突破既往太平天国史研究范式和主流论断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