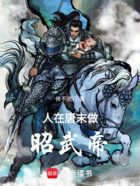
第11章 须陀洹
“大父,我们来了。”
刘伯阳扣响房门后,便在屋外等待,直到屋中传出一声进后,方才推门而入。
“过来一起看看火奴儿的大作。”
或许是元日的原因,老道今日的精神还不错,话语之中显得中气十足,眼神也略清了一些。
而听到祖父的话,刘伯阳这才注意到一旁摆着六个箱子,其中一个已经打开,所以可以看出其中装着的是书籍。
“火奴儿也会写书?”
这不是刘伯阳看不起刘克之,毕竟刘克之看过多少,学过多少,会用多少,他都一清二楚,他知道这个弟弟学识不错,博闻强记,但写书,并不是靠这些就能做到的。
“天工开物?这是什么书?”
看着封面上的四个方正大字,刘伯阳翻开一看,便知道此书正是刘克之所写。
因为刘克之写文章有一个习惯,开篇先写题眼,然后围绕着题眼分为一二三阶段以方法或者思考的形式写下来,最后还要写一篇总结。
这种习惯与当世主流迥异,他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也是这样,反正他只在刘克之身上看过。
“原来是一本工书。”
刘伯阳翻到的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如何炼铁,后面还附有一副图画,画着一个十分奇怪的巨大炉子。
“不止,还是一本农书。”
一旁的刘仲卿也拿起一本书翻看起来,上面记载的是如何种植水稻等农作物。
“不止,火奴儿的这六个箱子里,天工开物只占了两个箱子,其它的四个箱子中,两个箱子装的是两本书,名为大唐风土记和万国地理录,还有两个箱子装的,是一堆兵书和医书。”
老道的表情变得严肃,但刘伯阳兄弟二人却从老道的语气中听出了骄傲。
两人打开箱子查看一番,随后满脸惊骇的看向老道。
“大父,火奴儿从哪里得的这些书,兵书和医书也就罢了,这地理录中的地图,居然如此精细!他是哪里得的?他可是连长安都没出过。”
二人并没有怀疑书中地图的真假,因为他们年轻时也曾游历天下,玄都观中也藏有一副简略的大唐地图,但那些,都没有这书中地图详细。
因为这地图已经详细的绘画了大唐的每一个县城,其中的主要大城,他们都去过,自然知道这地图记录的分毫不差。
至于大唐之外,他们也没有去过,但从大唐的地图来看,恐怕做不得假。
老道合上手中书籍,语气中带着一些回忆,第一次对后辈诉说起刘克之的往事。
“火奴儿小的时候便告诉我,他晚上做梦时,会遇到一个老道人,带他游历天下,从而看到了许多新奇事物,他请我买纸给他,记录下来,那时他年方六岁,如今十年过去,他已无法入梦,只有这六箱书籍,证明他梦中所见并非虚假。”
此事兄弟二人还是第一次知道,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不信,随后看着手中的书,却又不得不信。
刘仲卿慢慢的翻看着书籍,口中呢喃出声:
“我以前听对面大兴善寺的一个秃驴说过,罗汉果位中的须陀洹,虽然尘缘已断,但是生死未了,还需再入轮回,方能解脱。而须陀洹需要还清宿缘,因而能够觉醒宿慧,想起前世的记忆,展现出超凡的智慧。”
“火奴儿的情况应与须陀洹相差不大,那老道人说不定就是他的前世。”
闻言,刘伯阳满头黑线的看着自己的这个亲弟弟,见他恍然出神,忍不住开口呵斥起来。
“胡说八道,我看你是被那秃驴蛊惑了,你也是经年的修行人,怎会去相信这些,火奴儿不过是神游天界,获得祖师传授而已。”
刘仲卿回过神来,听着大哥的训斥,不敢反驳,但他不以为意的撇了撇嘴,言不由衷的回了一句。
“大哥说的对。”
“你!”
一听刘仲卿的语气,又看到他的神色,刘伯阳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撸了撸袖子便要再次开口。
“好了,我让你们来是为了看书,不是为了吵架的!”
老道一句话,便让刘伯阳冷静下来,想起了正事。
“大父,火奴儿为何要将这些书籍送来?”
“他想去投军,所以让阿贵将书送来,让我替他保管。”
“投军!”
刘伯阳顿时炸了,他知道有人想要谋夺刘克之家财,只是自己没有本事,无法抗衡那人,又知道刘克之脾气刚烈,不会轻易屈服,但家人皆在,会让他束手束脚。
所以便给弟弟带话,让他放手施为,大不了全家一起逃亡。
可他没想到,刘克之居然想去投军!
下意识的,刘伯阳回头看向刘仲卿,见他心虚的低头,便知道此事只有自己不知道,也不废话,当即撸起袖子,便要动手。
“你这家伙!叔叔就火奴儿一个儿子,你怎不阻止他,而且还瞒我!”
“好了!”
见大孙那醋钵大小的拳头将要打在二孙身上,老道眼中混浊顿时一清,合上书籍,起身一个箭步便来到二人身旁,伸手便抓住了刘伯阳的手腕,行动之迅速,眼力之精准,身手之灵活,完全不像是一个已经年逾八十的老人。
“大父!”
见是祖父抓住自己的手,刘伯阳连忙收力,怕伤到老人家。
“男儿汉,又怎能一世待在家中,火奴儿既能神游太虚,自有祖师护佑,不会出事!”
一边说着,老道松开了手,他的眼睛又重新恢复了混浊。
“可是!”
“没有可是。”
老道直接打断了刘伯阳的话,又语气严厉的吩咐二人。
“火奴儿的这些书无一不是传家之宝,这长安已不可久留,你们即刻收拾行李,趁着这几日天气好,启程前往蜀中!”
兄弟二人对视一眼之后,知道此事的严重性,刘克之的那堆书,在他们看来大多都不重要,唯有那些地图,既是真正传家之宝,也是灭门的祸根。
“是!”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两人连忙出门,吩咐家人收拾行李。
话分两头。
唐,乾符六年元日,辰时六刻,布政坊外。
一辆车架自顺义门辘辘驶出,旁边跟着一火十人的队伍,个个身披铁甲,腰胯横刀,手持长矛。
而在景风门外百步,一群腰胯横刀,手持棍棒的汉子早已等待多时,见到车驾到来,连忙迎了上去。
领头的是一个身高五尺,肥硕如球的胖子,只见他走到车架前,神色恭敬的躬身一礼。
“义父,您来了。”
“嗯,出发吧。”
车架中传出的声音与平常人并无不同,而听到车中人开口后,那胖子连忙转身指挥起来。
“老七,带着兄弟们将义父的车架围起来,注意警戒!”
“好的,大哥。”
那群人中一个胖子连忙高声回答,随后指挥着众人将车架围了起来。
若是刘克之在这里,一眼就可认出,这老七便是在永安坊找他麻烦的胖子,而指挥他的那个“球状物”,就是董六。
“嗯。”
见到车架被严密的围起来,十分安全之后,董六转身笨拙的爬上一匹马,一挥手。
“出发!”
车架应声而动,转头向南,沿着布政坊和皇城中间的大街行走数百步后,又拐弯向西,走布政坊和延寿坊大街,目的地直指西市。
而在西市与延寿坊交界的街道上,刘克之二人已经等候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