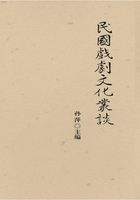
近代戏曲文学中的喜剧佳构——且说京剧《连升店》[1]
钮骠
京剧中的丑角戏(亦称“小花脸戏”)和丑行演员,在京剧演出史中都曾占有重要地位,有所谓“无丑不成班”之说。按例丑行演员都格外受到尊重,他被特许享有一种其他行当所没有的自由,就是可以在舞台上利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借题发挥,去完成“执艺以谏”、“随戏寓讽”的任务。其承继了远自秦汉徘优以来的唐参军戏、宋代杂剧、金元院本中那种讽刺性演出的传统,每每起到抨击时弊、警世讥俗的功用,深为各个观众层所共同喜爱。《连升店》(亦称《连升三级》)就是京剧传统剧目中体现着这种特色的一个保留节目。它是一出以白口、表做见长的丑角正工戏;又是一出与小生搭档的“对儿戏”。表演上要求二人配合默契,衬托严谨,做到相得益彰,互为辉映。因此它成了习练文丑与穷生表演技艺所不可不学、不能不会的一出“底子戏”。这也是这出戏得以薪传不断、流播不衰的原因之一。
《连升店》的编写年代和它的产生
这出戏的编写年代,与京剧中大量剧目的情况相同,已不太容易考证得出精确的时日,但大致可以断定它是产生于清代中叶的作品,在京剧形成的初期就已经有了。据京剧界前辈萧长华先生说,这出戏最早演出于清道光年间,当时春台班的丑行伶工朱三喜曾演过,剧中有讲解《四书》文句的内容。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杨懋建(掌生)所著的《梦华琐簿》中也有“乡会试场后,各园及堂会,必演《王名芳连升三级》,花面演说题解,以为笑乐”的记载,同萧说正相吻合。
有的书中记述:“昆腔、高腔、河北梆子均有此剧目。”(见陶君起著《京剧剧目初探》)所憾俱已久成绝响。既无剧本传世,更无早于朱三喜之前有其他剧种演员演过此剧的记载。那么,这几个剧种与京剧究竟谁先有的这个剧目呢?窃以为,即使昆腔中有过这出戏,它也不属于哪部传奇中的一折,戏中唱的又是[吹腔],也非昆曲。更何况从剧本的语言风格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来看,无不充满了“京味儿”,不大可能是最先产生于江南的昆剧中,它应当是京师本地的产物。虽在北方的昆弋安庆班的演出剧目中,查有《连升三级》一剧(见周明泰编《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说高腔有这出戏,可能就是指此,但演出的时日,已是宣统年间了。在河北梆子的传统剧目中也确有此剧(见马龙文、毛达志著《河北梆子简史》),但不明出于何时,若从河北梆子在京师盛行的年代考察,最早也超不过同光年间。梆子班演出这出戏,倒大有可能是从皮簧班移植过去的,抑或是“两下锅”时期才开始有的。其他剧种,另如滩簧演员范少山演过此剧的记载就更晚了,己是民国七年(1918),而且表演中操的是京话(见张聊公著《听歌想影录》)。因此,说《连升店》的剧本编写于清代道光年间,首先出现于北京的京剧舞台上,看来是切合史实的。
按清代沿袭明制,仍以科举取士,每逢会试发榜后,召新进士入宫,于保和殿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拔取状元。就在这天,为了祝贺“状元及第”,例行团拜之举,仪式上要请状元观剧,谓之“状元戏”。为取“连升三级”这句话的吉利,照例必演此剧。是日,民间戏园也都家家上演这出。剧中王明芳考店家的题目,就是本科会试的考题,于是店家穿凿题义、作滑稽诊解,诙谐百出,以博观者一笑,谓之“讲题”。近代的许多笔记、史料中确有不少关于这出戏的记述,除前面所引的《梦华琐簿》外,再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戏剧类》中也记确:
由此可见,《连升店》是一出应时当令的小戏。从剧中的另外几个方面也可以表明,它是以当时清代生活为题材的。如崔老爷原来的扮相是戴帽头儿(瓜皮帽)、梳小辫、穿外褂子、官靴,完全是清装打扮(这与《八蜡庙》中金大力扮清装,以示故事发生的时代为同一用意);剧中所涉及的官职、官署,如翰林院、庶吉士、提学道等也都是清制中所有的。清代中叶以来,昆班的上演剧目中有所谓的“时剧”,含新出或时行之意,如《芦林》、《思凡》、《罗梦》、《借靴》、《拾金》等,为此,说《连升店》是京班中的“时剧”,亦无不可。
至于这出戏的作者,颇有可能是一位曾经亲身受过店家这类人物冷眼、侮慢的落第文人所编写的,为了一泄对这种不良社会气习深恶痛绝的情绪,夸张而又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状况,于嬉笑怒骂之中予以嘲讽。当然,这样一出小戏,传演了一百几十年之久,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包含一定的思想力量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外,在艺术上也具备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充溢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这主要是经历了诸如刘赶三、罗寿山、萧长华、赵仙舫这些丑角大家们赓续不断地加工锤炼,踵事增华,才日臻完善而成了受人喜爱的佳剧的。正如明代曲家王骥德所说的:“古戏科诨皆优人穿插、传授为之,本子上无甚佳者”(见《曲律》)。他认为科诨多半是表演者的创作,《连升店》也正是这样。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又经过表演者与作家共同合作,进行了一番拂拭、清理,就更焕发了它的熠熠光彩。
《连升店》的戏里与戏外
京剧中的“小花脸戏”、或扩而大之说“三小(小丑、小旦、小生)戏”,大致可分为四类:玩笑戏(包括闹剧)、诙谐戏(亦可称趣剧)、歌舞戏(亦可称身段戏)和淫荡戏(俗称“粉戏”,此类戏已为时代所淘汰,现不见于舞台)。《连升店》属于诙谐戏。这类戏的内容多具讽刺性、揭露性,格调高、寓意深,讲究余味,引人深思,故此也是丑角戏中最难演的。《连升店》的店家在剧中既是被嘲弄者,同时他又往往从戏中站出来嘲弄别人。有“戏内哏”,是剧作家和表演者对剧中人施以的嘲讽;还有“戏外哏”,则是表演者随戏寓讽,借滑稽的形态,诙谐的语词,对时下违反人民意志、不洽舆情的流弊或统治者,予以的针砭和讥刺。几代搬演此剧的演员,舞台上都做到了这点,如:
上述诸例中这些有的放矢的插科打诨,无疑都起到了为人民之喉舌的作用。
“戏内哏”所嘲讽的对象,就是剧中的主要人物店家了。剧作者与表演者通过描摹店家前倨后恭的两副迥然不同的面孔,揭示了社会生活中一种庸俗卑劣的人际关系,把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恶浊风习具体化、形象化了。店家这个集鄙俗、虚伪、贪婪于一身的市侩形象,又是在揭露“店大欺客”与“客大欺店”的不良社会现象中塑造起来的。
戏的前半出,表现为“店大欺客”。在店家眼里,衣履穿着就是贫富贵贱的标志。衣冠楚楚者,自然是富者、贵者,来到他这店里,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不招“财神爷”生气;衣衫褴褛者,必然是贫者、贱者,连要盏灯也得凭造化。王明芳在他眼里,就是要饭的花子、寻宿儿的乞丐。因而也就不配做举子,不配住他的店。实在打发不走这块“穷磨”了,才把他安置在半间草房里。如此一来,却增长了他不可一世的气焰,因为这回他对穷人施了恩惠,故此王明芳稍露一点不满,他便拿“请出”、“别处去”来要挟,屡屡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王明芳与他走近一点,他嫌口臭,对他说两句客气话,他厌烦“穷人礼多”;甚至把王明芳当作贼看,王要住厢房,他说:“半夜人家丢点什么,我还负那责任去!”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轻蔑、侮弄,使王明芳自叹:“今科不中啊,下科我是再也不来了!”店家立即呵斥道:“我这儿没请你来!”店家始终贯穿着的都是一个“欺”字,尽管目不识丁,胸无点墨,却敢大言不惭地开讲、训人,这目空一切、信口开河的行径,也是基于一个“欺”字。这种被铜臭气熏透了灵魂的市侩的思想逻辑就是:“没有钱便没有一切”,当然也就没有学问、没有见识,甚至没有人格。
王明芳得中后,意味着他一脚跨进了富人圈儿里。于是,店家的态度立即随着王明芳身份的改变而改变,一副冷面孔,登时换上了一副热面孔。在店家的心目中,谁得中谁就摇身一变而成为财神爷,就要去攀附。由此,阿谀谄媚、溜须拍马、垫钱、借衣和把王的旧鞋放在祖宗板上供起来等等,就都接踵而来;甚至于厚着脸皮和王明芳论起“咱爷儿俩”来,及至王换上了新衣服,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言辞来恭维了,索性恬不知耻地说出:“简直的是我爸爸么!”灌米汤、套拉拢到了令人作呕、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谓“客大欺店”,这“欺”字实非出自“客”,而是受欺者心理状态上的自甘情愿,故作多情,这一切的终极目的,无非是为了有利可图。自愿垫钱、殷勤借衣是先下本钱,以从中牟取超出几倍的利益。到了最后,干脆赤裸裸地说出来:“这衙门里所有进钱的道儿,都赏给我一个人儿,那才好哪!”一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卑鄙嘴脸暴露得无遮无掩。“客大欺店”实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写照。当然,在批判这种人情世态中的恶习的同时,也流露出赞颂“荣华富贵”的封建思想,无形之中在告诉观众:穷书生唯有高魁得中,踏上仕途,才能改变受人揶揄的处境。“有功名才有富贵”——这也是这出戏不容否认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在店家身上反映出的社会风气,是与这出戏产生的时代以及社会状况密切关联着的。清代后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日呈繁荣,加上商税轻微等原因,城市商业得到发展,贫富分化日渐悬殊,这就形成了《连升店》中店家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市侩哲学的社会基础。剧作者与表演者,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和感受,把店家这种遇贫穷而作骄态、见富贵而生谄容的可憎可厌的形象,穷形尽相地暴露在舞台上,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让人们于笑声中否定它、鄙夷它,做到了喜剧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能够收到发人深省和作为“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门”(李笠翁语)的社会效果,即使今天演来,仍不失其启迪作用,故此它在京剧的讽刺性喜剧中当列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连升店》的写作特色与表演特色
《连升店》的作者与表演者,为了充分发挥喜剧滑稽、诙谐、风趣的表演特色和它的娱乐作用与启迪作用,收到寓教于笑,令人醒脾解颐的效果,在喜剧手法的运用上,呈以下特色:
一、章法简洁,段落分明,不蔓不枝,轻快顺畅。
全剧演来四刻多钟,通过主要人物店家的一系列自我表演,不造作,不牵强,水到渠成地暴露了他可鄙的心理和可笑的丑态。无曲折的情节,无离奇的悬念,始终在轻松、自然中发展,具“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意趣,笑料跌宕起伏而出,无故意造作的痕迹,使笑声贯串全剧,充满了视听之娱。
全剧从氛围和节奏上,分为两大块,以王明芳得中前后为分野。前段写王明芳的微弱与寒酸,店家的傲慢与轻狂;后段则写王明芳的转弱为强和店家的由强变弱。通过对比,刻画人物性格,描摹人情世态。在第一场里,从开场至王明芳去赴殿试下场、店家念下场对儿:“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尿壶”止,对人物的刻画实已基本完成,常有演出至此即告结束的。后几场戏,虽属余波,但却能加重渲染,使观众对人物、情节得观全貌,印象完整,还是以演全为上。
在节奏的推进上,由于前段重在勾勒店家的趾高气扬,故意摆谱儿,较为从容、款式;后段在于描绘店家的逢迎阿谀、跑跑颠颠,较为紧促、闹忙。全剧自始至终无拖沓之弊。
第一场中的几个段落是利用“更声”来划分的,很为巧妙。先后两段[吹腔],每段仅仅两句,起到了时间过渡的作用:起初更后,开唱头段[吹腔],唱止,店家上,响二更,店家讲题后,下,响三更,开唱二段[吹腔],唱止,店家再上,响四更;店家让王明芳睡觉后,下,响五更。借人物的上下场间,便将每个各有中心内容的段落,转折得十分自然,没有花费什么笔墨,却把时间交代得清清楚楚。这四句唱,安排得何其妥切!充分发挥了戏曲在处理时空上手法简洁的优长。
二、运用夸张手法,矢出人物性格。
夸张手法在寓讽刺于笑乐中的一类诙谐戏里,几乎是普遍使用的。对所描摹的现象或性格作突出和夸大,是为了更鲜明地揭示现象或性格的实质,以取得否定和鄙夷的效果。然而,运用得成败与否,则在于分寸的掌握是否得当。如果夸张到不合理的地步,就不会令人相信而接受,做到“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语)才行。《连升店》在运用这一手法上,既是大胆的,又是适度的,恰到好处,合乎情理,做到了夸张与真实的统一,既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又把生活现象夸大了。如店家让伙计们把王明芳换下来的鞋,放在祖宗板上供奉起来和当王换上新衣裳后,他竟装模作样地哭嚎起来,编了一套令人肉麻的阿谀之词:“当初我们老掌柜的在世,总想穿这么件衣裳,我好容易给他做得了,没穿着,他就故去啦。今儿个您一穿上,我猛这么一瞧,简直的是我爸爸么!”这种人说出这种话是毫不奇怪的,确有刻骨传神之妙,把人物的丑恶心灵,全盘亮出来了,着实可笑和可鄙。
崔老爷已然白发皓首,却刚刚学念《百家姓》,这样的人竟想考取进士,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当他误听了得中的消息后,高兴得竟连下巴颏都乐掉了,于是又拜祖先,又谢皇恩,折腾了一通,结果是闹了个绝大的误会,一场虚空。但并未甘心,后来终于花钱捐了个锣夫当当,也算过过身在官场的瘾。这一连串的情节都是以夸张手法描述的。其实,崔老爷与锣夫并不一定是一回事,而一经把这两个人物捏在一起,不但增强了喜剧性,也加深了讽刺性,嘲讽了社会生活中一些人觊觎功名富贵的心理和行为。而这喜剧性的背后,又何尝不蕴蓄着一定的悲剧性呢?言其深刻,就在这里。
可以说,《连升店》全剧的构筑、情节的铺展、人物的雕镂,无不饱含着夸张的意趣。
三、笑料的安排做到前后呼应,出之自然。
全剧中的许多“哏”都是前有伏笔,后有应笔,及至出口,瓜熟蒂落,绝无生硬勉强之嫌。如“好”与“妙”,“臭”与“香”,“人参汤”与“豆腐浆”,开讲与不识字,等等。凡王明芳得中前,受店家呲嗒、揶揄的言词,都没有过而即逝,全成了留下来的扣子,到后来一一还将回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店家弄得露丑出乖,尴尬万状,达到了贬斥的目的。
四、语言机巧、隽永,谑而不俗,做到性格化。
京剧丑角戏中,由于品类不同,在语言风格上也各有所异。玩笑戏的说白,重在生活情趣,以“逗”见长;诙谐戏的说白则忌低俗,重理趣,以“说”取胜。李渔曾说:“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连升店》的念白,妙在“俗”与“不俗”之间,能使雅俗共赏。“讲题”一场,充分体现了这点。另如王明芳看过报单之后,在笑声中失手碰了店家的下巴时,店家竟说道:“我下巴颏儿没留神,碰了您的手了。”这样的语言活脱勾画出一个圆滑讨好、甘愿低三下四,为了达到企图而宁可把一切坏事揽在自己身上的小丑嘴脸。前面问王明芳的姓氏时,明芳说姓王,他不相信,竟说:“您瞧,他这浑身上下,可哪一点儿配姓王呢?”就这一句话便把个小人心理,描绘得入木三分。
全剧的语言做到了干净、简练、流利、顺畅,富于生活气息,彰显人物性格。确乎是经过几代名家锤炼过的精品。
《连升店》的表演特色,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全剧的表演以话白为主,重念功。念法不同于一般的玩笑戏那样近于生活口语,它是经过加工的舞台语言,属于半京韵白,富有音乐性、韵律性和鲜明的节奏感。讲求各种语气的变换,于抑扬顿挫、亢坠疾徐的变化中,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复杂变化,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展露在舞台上。
通场的念白在传神达意中,要求有“味儿”。“味儿”即是一种艺术感染力量,舍此则失去戏曲魅力,让人听起来,既不是话剧,也不是相声。
二、店家与王明芳在表演的配搭、交流、衬托上,冷与热、急与缓、收与放的交替对应,互为默契,于“相称”中出戏,忌浮浅,戒俗厌,收到含蓄而不温、舒放而不火的艺术效果,给人留下余味。
笑声终止后的艺术力量比笑声更有价值。萧长华、姜妙香二位前辈的表演,达到了这种境界,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范本。
《连升店》中“讲题”一节,历来的演出,凡使用“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一段的,只有店家歪讲,却从无对这两句文词的正确解释。听者只知道是店家在这里胡说八道,却未必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解释。为了弥补这一缺陷,1985年我与润德(萧老的次孙)、郑岩二弟应北京电视台之邀,摄制此剧的戏曲电视片时,在店家讲说完了之后,王明芳加了这样一段念白:
对这两句《四书》文句略作解释。播映后得到了几位前辈的首肯,认为这样较之前圆满了。王明芳既说破了店家的信口雌黄,也使观众明白了这两句的词义。
另外,为了使听众耳熟易懂,我们还将念白中提到的“李三娘”改为“王宝钏”,相应地将“正在磨房那儿推磨哪,一瞧她丈夫不第而归……”改为“苦守寒窑,等了十八年,一瞧她丈夫不第而归……”;“代战公主”也改为了人们更为熟悉的“穆桂英”,原“追赶平贵还朝”,改作“追赶宗保回山”。这些改动虽然不大,不至于有伤大体,但我们还是审慎行事的,所幸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
1988年8月于宣南半步桥东百安寄庐
[1] 本文发表于《戏曲艺术》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