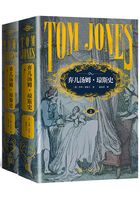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三章
奥维资先生刚一到家就发生的一件怪事。玳波萝·维勒钦阿姨在这件事里的体面行为,兼及她对私生子的严斥痛责。
在前一章里,我对读者表明,说奥维资先生继承了一份很大的产业;有一副善良的心肠,却没有家室的累赘。这样一来,一定会有许多人下结论,说他这个人,忠诚立身,正直处世,从不欠人一钱,除了自己的财物,其他概无所取;使一家上下,都丰衣足食;对于邻居,在饭桌上热烈真诚地款待;对于贫苦的人,慈善为怀,这也就是说,对于那般宁愿乞讨而不愿工作的人,给他们一点儿饭桌上的残渣剩炙。他死的时候巨富无比,同时修盖了一座医院 。
。
一点儿不错,这些事情之中有好些他都做了。但是如果他没再做别的事,那我就只好让他自己在医院大门的上方,用光滑的易切石,刻上自己的善行义举就完了。但是我这部史书所要写的,比起这些来,是更为不同寻常的事迹,否则,我写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书,就是大大地浪费了时光,而你,我的明智朋友,把某些令人开心的作者故意逗人发笑、叫作是《英国历史》 的章节纵游涉猎一下,也同样可以益人意知,怡人性情。
的章节纵游涉猎一下,也同样可以益人意知,怡人性情。
奥维资先生因为办一件极特别的事,离开家而在伦敦待了整整一个季度。不过究竟是什么事,我却不知道。但是据他为这件事而离家外出这样久,就可以断言,事情一定很重要,因为多年以来,他每次离家,都没超过一个月。他这次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了,他和他妹妹匆匆吃过晚饭以后,就因为旅途劳顿而回到自己的寝室去了。在那儿,他跪了好几分钟的工夫 ——这是他的定例,不论因为什么,都不能打破——就打算上床就寝;这时候,他一揭开毯子和被子
——这是他的定例,不论因为什么,都不能打破——就打算上床就寝;这时候,他一揭开毯子和被子 ,就吓了一大跳,因为千没想到,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婴孩,用粗麻布裹着,在他的上下双重单子里正睡得沉稳香甜。他站在那儿,一时让这种光景惊得口呆目瞪;但是他心里既然永远是慈爱占上风,一会儿就对眼前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儿起了怜悯之心。他于是打铃儿,吩咐叫一个年事垂老的女仆马上就起床,到他屋里来。同时,婴孩之容和酣睡之态所永远表现的那种红红白白的鲜明颜色,生出一片天真烂漫,所以他就聚精会神地细看起来;因此那位庄重老成的妇人进来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竟没顾到,自己上身原来只穿了一件衬衫。实在说起来,那位庄重老成的妇人很给了她主人充裕的工夫来穿衣服;因为虽然仆人叫她起来,那样急如星火,而且即使她明知道,她主人猝然中风,或者发了别的急病,马上要一命呜呼,而她为了尊重主人和顾全体面,却也在镜子前面整发拢鬓,待了有好几分钟之久。
,就吓了一大跳,因为千没想到,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婴孩,用粗麻布裹着,在他的上下双重单子里正睡得沉稳香甜。他站在那儿,一时让这种光景惊得口呆目瞪;但是他心里既然永远是慈爱占上风,一会儿就对眼前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儿起了怜悯之心。他于是打铃儿,吩咐叫一个年事垂老的女仆马上就起床,到他屋里来。同时,婴孩之容和酣睡之态所永远表现的那种红红白白的鲜明颜色,生出一片天真烂漫,所以他就聚精会神地细看起来;因此那位庄重老成的妇人进来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竟没顾到,自己上身原来只穿了一件衬衫。实在说起来,那位庄重老成的妇人很给了她主人充裕的工夫来穿衣服;因为虽然仆人叫她起来,那样急如星火,而且即使她明知道,她主人猝然中风,或者发了别的急病,马上要一命呜呼,而她为了尊重主人和顾全体面,却也在镜子前面整发拢鬓,待了有好几分钟之久。
一个人,对自己的仪容是否体面顾全得那样严格,遇到别人稍一不顾体面而就失惊打怪,本不为奇。因此,她刚一开开门,看到她主人上身只穿着一件衬衫站在床边,手里还拿着蜡烛,她马上大惊后退,本来也许还要晕厥倒下;幸而她主人一下想起来,他原来没穿上衣,立即告诉她,叫她先在门外等一下,等他把上衣披好再进来,才让玳波萝·维勒钦阿姨那双见不得脏东西的眼睛,不再失惊打怪。因为她虽然已经都五十二岁了,却起咒赌誓地说,她从来没见过不穿上衣的男人。好嘲弄的智士,或喜浪谑的哲人,也许觉得她头一次吃惊,是令人可笑的;但是更稳重沉着的读者,如果想到半夜三更,叫人硬从床上提溜起来,再加上她看到她主人那番光景,一定会认为她这种举动完全事有必然,应该盛加赞赏;除非他想到,玳波萝阿姨这种举动,无非出于审慎谨饬而已,而审慎谨饬,我们应该认为,对于一生之中,到了玳波萝阿姨那样年纪的老处女,必定追随陪伴,不离左右,如果这样一想,也就不觉得她有什么可以盛加称赞的了。
玳波萝阿姨重新回到主人屋里,听到发现这个小小婴儿的经过,她那时的惊讶,比她主人刚才还要更甚;她忍不住不但大惊失色,而且还大惊失声,嘴里喊道,“哎呀,心善的老爷啊,这可怎么办哪?”奥维资先生答道,那天夜里,这个婴儿就归她照管啦,到了明天,他就吩咐人给他雇一个奶妈。“不错,老爷,”她说,“我还盼望,老爷您发拘票 ,把这孩子的妈那个小娼妇抓来,因为她一定就住在这方近左右。我得看到她关进布莱得维勒
,把这孩子的妈那个小娼妇抓来,因为她一定就住在这方近左右。我得看到她关进布莱得维勒 ,拴在大车后面叫鞭子抽
,拴在大车后面叫鞭子抽 ,才可心称愿。不错,这种坏透了的烂污货,您不管怎么严厉处治她,都不为过。就看她这大的胆子,愣把罪名扣到老爷您头上,我就敢说,这绝不是她头一个孩子。”“把罪名扣到我头上,玳波萝!”奥维资先生回答说,“我就看不出来,她有这样的打算。我认为,她采取这种办法,只是为的能给孩子找一个有吃有穿的地方就是了。我还是一点儿不错地认为,她没办出更坏的事来,觉得高兴哪。”“这样该死的臭婊子,把罪名栽在忠厚老实人头上,
,才可心称愿。不错,这种坏透了的烂污货,您不管怎么严厉处治她,都不为过。就看她这大的胆子,愣把罪名扣到老爷您头上,我就敢说,这绝不是她头一个孩子。”“把罪名扣到我头上,玳波萝!”奥维资先生回答说,“我就看不出来,她有这样的打算。我认为,她采取这种办法,只是为的能给孩子找一个有吃有穿的地方就是了。我还是一点儿不错地认为,她没办出更坏的事来,觉得高兴哪。”“这样该死的臭婊子,把罪名栽在忠厚老实人头上, 还有比这个再坏的吗,我还真没听说过;老爷您自然应当知道您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全世界别的人可都挑毛拣刺儿,好嚼舌根哪。有好些忠厚老实人,碰上倒霉,叫人家拿着当成和他毫不相干那种孩子的爸爸,还不有的是吗?再说,这样的孩子,区上有义务养活,
还有比这个再坏的吗,我还真没听说过;老爷您自然应当知道您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全世界别的人可都挑毛拣刺儿,好嚼舌根哪。有好些忠厚老实人,碰上倒霉,叫人家拿着当成和他毫不相干那种孩子的爸爸,还不有的是吗?再说,这样的孩子,区上有义务养活, 您为什么非自己收养不可?论到我自己,要是这个孩子真是正经八百的人家的,那自然另有一说;不过这种不是正道儿上来的小杂种儿,那我自己连碰一下,都觉得恶心得慌,我简直不能把他当作是和我一样的人看待。嗬!您闻闻他这个臭劲儿!他的味儿都不像个正经八百的人家的。您恕我多嘴,要叫我出主意的话,我就要叫人把他装在篮子里,送出去,放在教堂管事人
您为什么非自己收养不可?论到我自己,要是这个孩子真是正经八百的人家的,那自然另有一说;不过这种不是正道儿上来的小杂种儿,那我自己连碰一下,都觉得恶心得慌,我简直不能把他当作是和我一样的人看待。嗬!您闻闻他这个臭劲儿!他的味儿都不像个正经八百的人家的。您恕我多嘴,要叫我出主意的话,我就要叫人把他装在篮子里,送出去,放在教堂管事人 的门外面。今儿夜里天气很好,只小小地刮点儿风,下点儿雨,那不要紧;所以要是这孩子裹得严严的,放在一个暖和的篮子里,那等到明儿早晨有人看到他的时候,有对半儿他死不了。即便他死了,咱们把他好好地照管了一番,对他也算尽到了责任了。其实,这样的孩子,还不如在任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死了,那比他们长大了跟他们的妈学还好一些;因为这种孩子,您绝不能指望他们长大了不跟他们的妈学。”
的门外面。今儿夜里天气很好,只小小地刮点儿风,下点儿雨,那不要紧;所以要是这孩子裹得严严的,放在一个暖和的篮子里,那等到明儿早晨有人看到他的时候,有对半儿他死不了。即便他死了,咱们把他好好地照管了一番,对他也算尽到了责任了。其实,这样的孩子,还不如在任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死了,那比他们长大了跟他们的妈学还好一些;因为这种孩子,您绝不能指望他们长大了不跟他们的妈学。”
这番话里,很有些太鞭辟入里的地方,如果奥维资先生当时十分用心听,本来也许要生气的;但是正在那时候,他把一个指头伸到那婴儿的小手儿里,小手儿轻轻一挤,好像求他帮助似的,这一来,一下就把玳波萝阿姨那番确实滔滔不绝、恰当不移的贬抑之词,战而胜之,即便那番话比她说的力量再大十倍,也都无济于事。他现在斩钉截铁地吩咐玳波萝阿姨,叫她把孩子带到她自己的床上,再叫起一个女仆来,叫她给孩子预备奶糊以及别的东西,等着孩子醒了的时候用。他还吩咐,明天一早,就把婴儿应用的小衣服,一概预备好;又吩咐,他明天刚一起来,就把孩子送到他跟前。
维勒钦阿姨很会察言观色,见机而作,她对她主人又极恭顺驯服(她在她主人手下,当的是一份最美的差事);所以她良心上的顾忌,在他严厉的命令之下屈服,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她对这孩子出生非法有任何厌恶之意,就把孩子抱起,嘴里还说着,这孩子是个甜美可爱的小娃娃,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奥维资于是进入一枕黑甜之乡,这种黑甜之乡,是如饥如渴、一心向善之人,一旦所欲得遂,心餍意足,所极易于享受到的境界;既然这种黑甜乡,比起另外其他的丰筵盛席 所能导入其中的,都可能更甜美酣畅,因此如果我知道有任何地方,风清气爽,能使读者起饮和饱德、履仁行义之欲,因而可以向他推荐,那我就应更加惨淡经营,使这种酣适的黑甜乡,展现于读者之前。
所能导入其中的,都可能更甜美酣畅,因此如果我知道有任何地方,风清气爽,能使读者起饮和饱德、履仁行义之欲,因而可以向他推荐,那我就应更加惨淡经营,使这种酣适的黑甜乡,展现于读者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