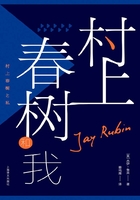
第4章 将日本文学介绍给世界的村上春树
过誉的言辞
1991年秋,英国一家大型出版社企鹅出版社的编辑西蒙·维尔德先生的一封信翩然而至。自从我1991年成为村上译者以来,翻译的都是与村上相关的内容,但因这封信,我开启了围绕芥川龙之介的冒险。
鲁宾先生:
重要事情请允许我后面再提,首先我想对鲁宾先生《奇鸟行状录》的英译表达我诚挚的敬意。受益于先生的丰功伟绩,我得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
我在企鹅出版社担任“现代·经典·系列”的主编。关于这个系列,我的本意是希望收录各领域中印象深刻的作品并能引以为傲,可是关于日本文学数量太少,除了三岛和川端的作品,尚为一片荒芜。特别是缺少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在英国无法以任何形式得到)。
我以前读过很早之前艾利坦斯·普莱斯(Eridanos Press)翻译的英译短篇集,里面收录了《地狱变》、《齿轮》、《一个傻瓜的一生》、《寄老友手记》,读完着实吃了一惊。我想,芥川的感受性和村上春树有着极为近似的地方。
倘若能以崭新的翻译将芥川的作品推出去,应该也会给西方世界强烈的震撼。先生意下如何呢?您会认为芥川的作品存在终究无法译成有影响力的英文的壁垒吗?
我的梦想是希望请鲁宾先生重新挑选芥川作品译成英文,再附上村上春树先生的序之后重新出版。我的这一设想或许会被您嘲笑为异想天开。百忙之中打扰不胜抱歉,希望这个提案能有幸得到您的审阅。
最后,再次祝贺《奇鸟行状录》取得的伟大翻译功绩。
西蒙·维尔德
1999年9月17日
一目了然,这封信中过誉的言辞是要表达企鹅出版社希望策划带有村上春树序文的新版英译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集。这个主意固然不坏,而且还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况且我被人赞誉,心情也不赖。于是我当即给维尔德先生写了肯定的回信,可是我认为,请一向声明对日本文学不感兴趣的村上参加这样一个项目,可能性接近为零。
所以我同时也对维尔德先生写道:“如果村上先生决定参与西方世界的芥川再发现,那是多么讽刺啊!若说原因,村上没有获得的少数文学奖项之一便是芥川奖,而且还要让他反过头对没有得到的东西表示骄傲。”
我通过传真给村上转发了维尔德先生的信。我想反正没有村上的序,企鹅出版社大概也不想出版这本书,便又回到正在着手的两项工作中。那就是《神的孩子全跳舞》的英译与《HARUKI·MURAKAMI与语言的音乐》的执笔。
一口应承的回复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村上很快给了回复,并一口应承。结果村上不仅在英语圈,而且在日本国内的芥川再发现上做出巨大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个讽刺。
《神的孩子全跳舞》的英译与《HARUKI·MURAKAMI与语言的音乐》在2002年完成,所以我真正得以认真投入芥川龙之介之中是在2003年夏天以后了。自那以后,除去大学的工作,我就向芥川一边倒了。
我并非只读已盖棺定论的代表作,而是读芥川的全部小说,仔细吟味,为英语圈构建全新芥川像的愿望汩汩涌起。既然想象力丰富如芥川,那么以现代眼光重读,肯定会发现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名作,我带着这样的自信决定通读作品。
然而问题关键在于值得翻译的作品为数过多,《地狱变》、《齿轮》这样不可撼动的代表作自不必说,我还希望务必将几乎不为人知的《尾形了斋备忘录》、《阿吟》、《忠义》、《掉脑袋的故事》、《葱》、《马脚》、《大导寺信辅的半生》、《文章》、《孩子的病》收入。出版后的短篇集18篇作品中,之前未能译成英文的有9篇之多。
从准备阶段到发行阶段的4年是我极为充实的体验。加上年谱、参考书目、村上的序、译者前言和注释总共被限制在230页之内,所以分给关键的小说部分的页数就没那么多了。
可是随着阅读推进,接连出现我希望一定要收入的作品,而且比原计划要长的村上序文着实有趣,编辑也希望全文登载,所以2006年出版的这本书遂膨胀为268页了(村上的序占了其中的19页)。
这篇序完全表现出村上严谨的性格,所以我知道他写的时候是当真认可芥川作为日本文学代表作家的地位的。他向西方读者详细解说了芥川龙之介对于典型的日本读者和作家村上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读过之后,就会明了写这篇序时,村上花了多少时间再次阅读、再次思考芥川的作品。
序的开头写着这样一段视野开阔的话: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国民作家”中的一位。如果要从明治维新以后的所谓日本近代文学作家中投票选出10位“国民作家”,芥川龙之介首先毫无疑问要占据其中一席。除他之外,这份名单或许还会有夏目漱石、森鸥外、岛崎藤村、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这些名字列入吧。虽然我并不确信,但或许他们后面应该是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吧。夏目漱石毋庸置疑应位居第一。顺利的话,芥川可能会溜进前五名。这样就有九位了,还剩一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了。[10]
村上将芥川和其他日本作家及一众西洋作家进行比较,论述了芥川文体的杰出和芥川小说流传后世的价值。村上还谈及大正时期民主主义历史背景下芥川对西洋文化的态度,阐述了日本作家在东西洋之间所处位置的微妙,然后在最后写道:
芥川给现代日本作家——我自然也算其中一个——是否留下什么教训呢?自然有。作为伟大的先达,某种程度上也作为有志的反面教师,教训之一便是即便逃入技巧或人工虚构的世界中,迟早也会撞到坚固的壁垒。(中略)另一应当称作教训之处与西欧和日本文化的重合方式相关。(中略)这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而言,也不能完全等闲视之。因为纵令远离芥川生活的时代,纵令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置身于西欧文化与日本文化相互争诘的漩涡中。或者使用比较时髦的说法,或许应该说我们依然置身于全球化与家国化相互争诘的漩涡中。(中略)我们生于叫做“日本”的文化环境中,继承了固有的语言和历史,在那里生活,固然不可能完全西欧化或者全球化,但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必须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这既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沉痛教训,也是不可扭曲的原则。[11]
村上的这篇序自然是写给用英语阅读的读者看的,但对日本人而言也具有深度的洞察力,加之我编纂的这套企鹅出版社版短篇集与素来的芥川集不同,所以新潮社将这本Rashōmon and Seventeen Other Stories(《〈罗生门〉与其他十七则故事》)几乎原封不动囫囵个儿地反向引进,早在2007年就以《芥川龙之介短篇集》为题目出版了。这本书也得到引领芥川研究的关口安义与宫坂觉两位教授的认可,使我作为美国的日本文学学者得到一种意料之外的满足感。[12]
再度一口应承的回复
自那以后,村上积极协助我们向世界介绍日本文学。我1977年在华盛顿大学出版部出版了《三四郎》的译本,企鹅出版社策划再次由我执笔重译,他们对我说还是希望附上村上的序文。因芥川作品的翻译一帆风顺,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与村上进行了联系。就这样,我再次收到一口应承的回复。
2009年出版的企鹅版《三四郎》共235页,村上的序占了14页。题为“(大约)甘美的青春气息”的这篇文章是村上众多随笔中最优美的一篇。作为作家,作为怀念自己青春时光的个人,作为对漱石的伟大有着切身体会的日本人,也作为综观世界文学的读者,村上春树以饱含情感的文体叙写了《三四郎》的意义。
学生时代,村上对漱石和其他日本作家几乎不感兴趣。他说,在无钱买书的新婚时期,不得已借来妻子的漱石全集,这才第一次认真阅读,留下的印象却是“相当不赖”。
《三四郎》的特别之处在于与漱石自身22岁时的回忆纠葛缠绕,所以村上的序“(大约)甘美的青春气息”是一篇洋溢着怀旧而温暖的情调的文章。村上作品中传达这类情调的作品为数不少,特别突出的当属《挪威的森林》。
《三四郎》在漱石作品中所占的位置与《挪威的森林》在村上作品中所占位置大致相同,村上这样论述道:
对漱石而言,《三四郎》是唯一一部作为长篇的“青春小说”,他毕生只写过一部这样的小说,对他而言,应该一次足矣。然而这是一部无论如何都要写上一次的作品。在这种意义上,《三四郎》在漱石作品群中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部。任何一个作家都有那样一篇小说。与之比较也许有点厚颜无耻,但对我而言,《挪威的森林》这篇小说也是如此。我现在既不怎么愿意回首重读,也不认为自己还能再次写出那一类型的小说。然而通过完成那篇小说,我有种前进了一大步的感触,同时还有一种感触是,因为那篇作品的存在,我的其他作品得到实实在在的佐证。我如此设想(就擅自论断吧):这对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感触,漱石对《三四郎》大概也怀着相同的感触吧。[13]
与村上论《坑夫》
接下来村上积极协助将日本古典文学介绍给世界的另一些作品中就有漱石的《坑夫》。2002年在《海边的卡夫卡》中被提及之前,《坑夫》是一部在日本也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品。它是漱石小说中反响最差的一篇。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第一回开始就评价极差,《海边的卡夫卡》中对世间事情无所不知的大岛这一人物也说:“它的内容不怎么像漱石的风格,文体也相当粗糙,照一般说来,它似乎是漱石作品中评价最为糟糕的一篇了,可是……”[14]然而,村上在2015年9月出版的由我重译的《坑夫》的前言中说,在漱石的全部小说当中,《坑夫》是他最喜欢的作品。[15]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卡夫卡君如此说:“读完之后莫名感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这篇小说到底要说什么。可是怎么说呢?正是这‘不知道要说什么’的部分不可思议地留在了我的心里。”[16]
在重译本的序中,关于这部小说的读者所说的“读后的空白感”,村上做了稍为详细的说明:
“那里面有种与读优质后现代小说时同一类型的、与沙沙的干渴极为近似的感觉。也许可以称作由意义欠如产生的意义吧?”[17]
也许因为读者不怎么喜欢这种“读后的空白感”,所以《坑夫》的读者很少,然而我认识这部小说的两位热心读者,一位自然是村上,另一人便是我。
老实说,我第一次翻译《坑夫》是在1988年。后来在1993年之后的两年里,在我与村上同住在剑桥市的时候,我记得我俩谈论过《坑夫》。
那时候村上自然已读过《坑夫》,却记不怎么真切了。在我的拼命劝说下,他马上又读了一遍,说最喜欢的是主人公历尽种种艰辛却依然不改初心。那之后我们再没提起过《坑夫》,2002年我读《海边的卡夫卡》时却遇到了这样的句子:“主人公从那些体验中得到了怎样的教训啦,生活方式因而改变啦,深入思考人生啦,对社会的存在方式产生疑问啦,并没有专门写这些。也没有他作为个人成长起来这一类反应。”[18]尽管都是些琐事,但我能从中多少体会一点自己影响到村上文学的满足感。
若说到《坑夫》的重译如何被提上出版日程,这也要归功于村上的影响。有位名叫斯科特·帕克的英国编辑是村上的超级粉丝,他甚至将自己儿子的中间名字取为“Haruki”。在他读过《海边的卡夫卡》的英译本之后,涌起对漱石《坑夫》的兴趣,便又读了我从前的英译本,希望面向英语圈中的村上粉丝推出附带村上序的新版翻译。《坑夫》重译本遂决定由这家名叫“土豚社”(Aardvark Bureau)的颇具个性的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现在我正着手编集企鹅出版社的《近代·现代日本短篇小说集》。计划于2017年出版的这本书中,村上将如何向西方读者介绍同时代的文学呢?我热切期待着。